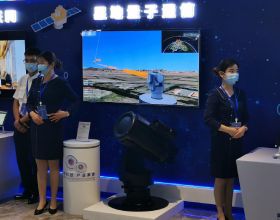以“辨體明性”為話語起點和理論指歸,以體用相兼、本末相洽為認知方式和批評路徑,是中國傳統文體批評獨具的特色,極其鮮明而突出,謂之為中國古代文體批評固有的一個傳統,絕非過言。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辨體明性”文體批評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乃至形塑了一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使其同時也成為中國傳統文學批評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古人品詩衡文,往往首先確認文體,此乃所謂“體制為先”者是也;確認文體,離不開對文之“體”與“性”的識別,能“辨”之“明”之方為能事者也,此乃所謂“以體論文”者是也。因此,談議文章利病得失、篇章品次優劣,當具“辨體明性”之功力,如此則能事足矣,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尤其是文體批評的“辨體明性”傳統便因此形成。中國傳統文體觀念和文體批評理論與方法的發展演變、豐富多樣正由此育化而來。“辨體明性”是中國式思辨理性與詩性智慧的和合統一、圓融相處,為華夏文化和華夏文脈偉岸大樹上佳美的一枝一葉,對其進行創造性闡釋和創新性轉化,應該成為我們研究中國傳統文體批評思想與方法的重心之一。
“辨體明性”作為傳統文體批評固有的一個特點,其批評指向與功能在於辨析文章之形制與風格特徵,即所謂體性是也。傳統文學批評善於從文體與風格的相依互顯中察體氣觀文象,古人以此為詩文評之本分也。“辨體明性”中,“體”主要指文的體式、體制、體貌,“性”主要指與作者關聯的個性風格,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本末相兼、體用相洽,涉及文體制式、文體分類、文類辨析、文體流變、風格特徵、批評方法論等諸多方面。透過對“辨體明性”的體認,我們可知傳統文體批評主要在體裁、語言形式和風格構成、辨體和類分或曰體式、體性、體類這三個層面上進行。
從文體的組織構成來看,我們可以將體裁和語言形式形成的綜合性狀態稱之為“體制”。所謂“體制”,主要包含三層含義:一是指文章的間架結構,二是指文章的體式特徵,三是指文章的內部構造。這三者屬於文章的形式因素,古人在作文、評文時對它們特別予以經營或評判。東漢以來文體漸趨豐備,演進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非但文體愈豐而臻於繁茂,文體批評意識也開始逐漸走向自覺,其時的文評論作和集文編纂中所體現的文體批評意識足可證明之,而“辨體明性”的文體批評特點和傳統亦由此而奠定基礎。總之,參照從唐代直至清末的“辨體明性”文體批評發展演變軌跡,可以說以品第文章的體制結構和體氣風神為主旨的“辨體明性”批評,確實是通體滲透著中華文化特點、文學精神和審美意識的一個傳統。
理論的研究和總結往往是在實踐之後,文體的命名和分類同樣如此。先是由於現實的需要而產生了某種適應現實需要的文章體式,其後這種體式在差不多同樣用途的書寫場合得以使用。大家都按照這種體式為某種特定事情和場合來書寫所需要的文章,從而這種具有特定體式特徵的文體便固定下來了,使用該種體式的書寫者就需要遵循這種文體的規約,即“文成體立”。因此,中國傳統文體大多是在因用而成體的情況下形成的,而對於文體批評來講,則是立體在先、辨體其後。劉勰的《文心雕龍》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多種總集和選本編纂,均對“辨體明性”文體批評奠定了基礎,並形成了較為系統的文體觀念意識。以“辨體明性”為核心的辨體批評,自此而蓬勃興起,在唐宋及以後的各個朝代全面展開,枝葉繁茂碩果累累。“辨體明性”成為傳統文體批評的具有方法論意義的基本正規化。
《文心雕龍》之後,唐代詩歌也在延續辨體的傳統,但大量的是對“詩格”的研究,屬於詩歌作法一類的實用研究。中唐以後,詩體批評崇尚意境,宋代則又注重韻味,雖然對詩歌體性的關注有所遮蔽,但仍有一些品評家比較重視詩體的“辨體明性”批評。如江西詩派就十分注重詩歌的體式與做法。到了明代,由於復古思潮的興起,“辨體明性”理論和批評實踐取得了長足發展,出現了大量的辨體批評著作。如《文章辨體》《文體明辨》《詩源辨體》等,就直接冠以辨體之名;《藝苑卮言》《詩藪》《唐音癸籤》等雖未以此冠名,但都以辨體明性為主要內容。這一時期亦多有“體制為先”的言論,體現出強烈的“辨體明性”批評意識。
任何文體一旦形成,就有自身獨具的體式,就會形成特有的體性方面的特點,併為後來的書寫者所遵循。時間長了便會引發突破該種文體規範的書寫,是為“變體”“破體”甚至於“失體”,如果“挑戰”成功,則往往會產生一種具有新的體性特點的文體種類。因此,我們看到,傳統文體批評中,對於諸如“正體”“變體”“得體”“破體”“失體”等問題的討論相當多,形成了一個話語鏈條,此便從觀念到方法兩個方面豐富了“辨體明性”批評的內涵。
“辨體明性”批評具體可分為三種方式:一是“觀瀾索源”,即在探本溯源過程中對文體演變軌跡進行還原性考索,歷時性、動態性特點突出,重在溯流別。如摯虞的《文章流別論》以及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眾多文體的闡述,均屬是也。二是“擘肌分理”,即對所論文體的體式結構、體制規範、風格特徵等進行闡發,力求透過微觀考察,以靜態、共時的分析揭示文體的體制形式和內在機制與肌理,重在明體性。如陸機在《文賦》中專對文之體貌、體氣、體脈進行揭示性描述,而不涉及文體發展流變歷史的追溯,便是如此。三是前兩種的融合,即沿波討源與辨析體制結合在一起進行“辨體明性”批評,務求達到博觀圓照,在動態考察與靜態審辨交替進行中辨明一種文體發生和發展演變的歷史軌跡,以及其外在形式和內在肌理之特點和規定性。如《文心雕龍》透過“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批評方法,對諸種文體進行綜合考察,便足以證之,而劉勰的這一方法在後世的文體批評中幾成“辨體明性”批評的正規化。
在這種傳統的影響下,後世批評家都把“辨體明性”作為文體批評的核心問題,體現在文體的形態辨別、觀念建構、類別界分、理論闡述、批評實踐等方面。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批評著作,有一些就是專門為某種文學體裁而設,比如說詩論、詩格研究的著作就是其中的代表。與此相應,文學史上每出現一種新的文學體裁,文學批評史上都很快會出現研究其體式、體制特徵的批評著作。比如,詞作為有宋一代之所勝,就有諸如李清照的《詞論》、張炎的《詞源》等著作出現,對其體制及風格進行“辨體明性”批評。又比如曲,在元代出現之後,曲論家也對此進行“辨體明性”批評,王驥德的《曲律》、李漁的《閒情偶寄》等就是這樣的成果。其中,李清照的“詞別是一家”的理論,王驥德“詞之異於詩也,曲之異於詞也,道迥不相侔也”的說法,都比較直接地指出了詞、曲與詩歌在體制、風格上的特點,具有為該文體立格、辨體的理論意義,是為“辨體明性”也。
“辨體明性”是隨著文體發展、種類繁多之後文體批評作出的必然反映,體現了文學創作和文學品評對“辨體明性”批評的需要。我們應該將“辨體明性”視為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傳統文學闡釋學的基本方法論之一。“辨體明性”以文章體裁為批評物件,論及文體正變與各體源流、藝術風貌、創作得失及風格特徵等諸多方面,展現了開闊的批評視野和理論維度。從批評理論的角度講,“辨體明性”既是一個命題,也是一種方法論。古人在批評實踐中創造和使用了一系列範疇、概念、術語,足以形成一個概念群或曰概念家族。這些概念術語的能指與所指各有側重,各自雖然有自己的義界,但是真正要為它們作出邏輯嚴謹、理論清晰的定義,卻頗為不易。因為,它們之間存在著相互交叉黏連的情況,而且它們多不是邏輯抽繹的產物,而是“象喻”的產物,要對它們作出內涵與外延都精確而明晰的定義是非常困難的。季羨林先生對中國古代文論概念名詞“一看就明白,一思考就糊塗”的評語,用於此真是再合適不過了。但同時,正因為這些概念術語存在著高度感悟性、“象喻”化和語境化的特點,古人運用它們進行“辨體明性”之文體批評時,卻可以更好地達到體貼入微的批評效應,並且使傳統詩文評中的“辨體明性”批評成為一種充分展現中華文化詩性智慧的批評詮釋過程。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黨聖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