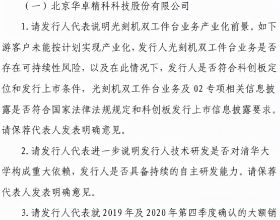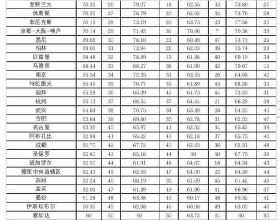二程自家體貼出“天理”二字,乃理學之奠基者。朱子繼承和發展了二程思想,集理學之大成。朱子思想為“理學”,毋庸置疑。然而,一些學者則將朱子理學與陽明心學並稱為“心學”,有混淆朱子理學與陽明心學的傾向。迴歸經典,重新系統闡釋朱子哲學、心理學、政治、倫理、教育、文學、美學、經學、史學、經濟、法律、科技等思想,筆者以為,朱子思想始於“理”,成於“理”,歸於“理”,一“理”以貫之;“理”具有本體性、參與性、歸宿性,是貫通朱子思想體系的主線。不能因其“心論”豐富,誤以為是“心學”。
“理”之本體性:“生”的功能
哲學方面,理與氣的關係紛繁複雜。理生氣、理本氣末、理先氣後、理主氣從、理寓於氣,究其根本是“理生氣”。朱子利用“理一分殊”說明“理”與老子的“道”類似,提升“理”至形而上的地位。“理”生成、孕育、滋養萬物,此後,萬物體現著“理”,最終復歸於“理”。每一人、物都稟賦了完整的理,以理作為存在的根據,其所各具之“理”是本體之理的體現,即“理一”。人、物雖各有一“理”,但所稟之氣駁雜,“理”在他們那裡或偏或全,形成人之理與物之理的“分殊”。相對“理一分殊”,朱子提出“心與理一”,“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這是就心的認知功能而言,心可以體認理,而這個體認過程需要下內、外和橫向、縱向等一系列功夫。據此,朱子的“心與理一”“心包萬理”與心學的“心即理”有本質區別。
同樣,“心,主宰之謂也”,也不能說明朱子思想是心學。從“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可以看出,朱子雖承認心的“主宰”功能,強調心的主觀能動性(認識的能動性),但認為心與其他萬物一樣,也由理生成。心之所以能“主宰”,是其主宰者“理”賦予的。心與理的關係,不是心主宰天理,而是心因天理而為主宰。終極主宰者是“理”,不是“心”。“心統性情”則體現了心理調節能力。“心”的能動性再大,沒有“生”的功能,就不能稱為本體。陳來指出,“朱熹這種以‘心’為意識的立場,與心學要求設定純粹主體、設定意識現象之後的心之主體的立場是不同的”,“朱子之‘心’也就不具有本體的意義”。“理”才是本體。
因此,心“與理一”“包萬理”“宰萬物”“統性情”都不足以證明朱子思想是心學;更不能為了便於與心學比較而稱朱子思想為“心學”;同時稱朱子思想為“理學”和“心學”顯然自相矛盾。可見,朱子思想是理學,且一“理”以貫之。
“理”之參與性:“分”的功能
“參與性”看似淡化了“本體性”,卻恰恰凸顯了“理”作為主宰者的強勁控制力。“理”是本體,亦參與朱子思想各方面,體現了“分”的功能。
心理學方面,理掛搭於心,性是心之體,情是心之用,心有調節七情的能力。政治方面,“正君心”是大根本,以“理”正君主之心,是“心與理一”在政治層面的體現。倫理方面,“性即理”,理善,性本善,“性”與“理”一致。教育方面,“變化氣質”是教育的路徑,可以祛除氣對理的遮蔽,其理論根據是“性”“理”一致。文學方面,“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道本文末,即理本文末。美學方面,“善惡皆是理”,善惡都有理的基因。經學方面,“借經以通乎理”,“理”寓於“經”中,讀“經”可參悟“理”,明白聖賢的微言大義。史學方面,“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理支配著歷史,滲透於人類關係、活動之中。經濟方面,“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貧賤、富貴因理而得之,因理而安之。法律方面,“道字、理字、法字、禮字,實理字”,法即理,法理一體。科技方面,“天地統是一個大陰陽”,理生氣後,憑藉氣實現宇宙系統迴圈,生生不息。
“理”之歸宿性:“一”的功能
“歸宿性”表現在心理學、政治學、倫理學、教育學等思想方面趨向、復歸於理,即“與理一”。體現了“一”的功能,“分”與“一”的辯證關係。“分”與“一”的關係,表明“心與理一”不同於“心即理”,釐清了理學與心學的邊界。
心理學方面,痛下心之功夫,調整心的狀態,未發與已發、動與靜、感與寂對立統一,“虛”“靈”“神明”,七情發作得恰到好處,善性不變,“心與理一”。政治方面,“心與理一”落到實處是“仁民愛物”,善待民,保護民,愛民如子。倫理方面,“聖賢氣象”是“心”“性”“情”與“理”一致的終極表現,是“心”與“理”一,是現實與超越、感性與理性的統一。教育方面,教與學形成的合力都是為了下學而上達,進入“心與理一”的理想境界。文學方面,聖賢文章是對心中之“理”的自然流露,文章的創作過程也與“理”一致。美學方面,順理為善、美,逆理為惡、醜,可以抑惡揚善,復歸於善(理)。經學方面,讀經、解經的過程,是一個趨近“理”的過程。史學方面,從史中發掘理,以此理治世界,經世致用,創造出符合“理”之發展路徑的歷史。經濟方面,君民一體,民富則君富,民貧則君貧;以“理”治天下則富,反之則貧。法律方面,理與法都是維護政治秩序的手段,兩者相輔相成。科技方面,瞭解宇宙間的運動、變化規律,掌握其本質“理”,順理而為,收穫豐碩。
思想體系特徵:一“理”以貫之
在朱子的思想體系結構圖式中,“理”既是出發點,也是目的地,出發點與目的地之間紛繁複雜,綜羅百代,博大精深,卻始終由“理”這個主線貫穿始終。
一是始於“理”,“理”具有至上性。“理”猶“道”,是本體,生成一切,包括氣、心、性、情等。無論是在哲學,還是心理學、政治學等思想方面,“理”的至上地位不可動搖。
二是成於“理”,“理”需要“掛搭”之處。“理”之至上性,導致其不易言說的特點,給人一種神秘而虛懸的感覺。為了便於理解“理”,只有下沉到更加具體的心理學、政治學等領域,才能使“理”逐漸變得有形有體,更加豐滿、真實。“理”是如影隨形的參與者,在朱子學中,我們都能見到“理”的影子;沒有“理”,也就沒有構建其他思想的筋骨。
三是歸於“理”。“理”是最後的歸宿。“理”是形而上的,是“道”;相對於“理”來說,氣、心、性、情等範疇是形而下的,是“器”,它們最終上達的理想境界是“理”。
總之,朱子思想一“理”以貫之,它是理學而非心學。朱子理學、陽明心學及其他學派共同構成了宋明新儒學,形成了中華五千年文明中一個獨特的精神高地。
(本文系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專案、國家社科基金孵化專案“‘以水喻性’的嬗變與宋明理學心性論的發展”(AHSKF2018D68)、2020年度安徽省社會科學創新發展研究課題“朱子《明道論性說》對明道心性論的反思與挽救”(AHSKCX2020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曉莊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