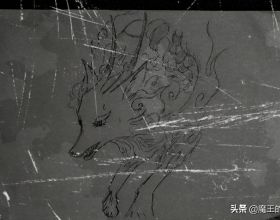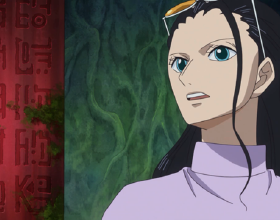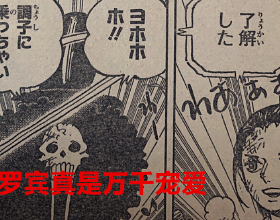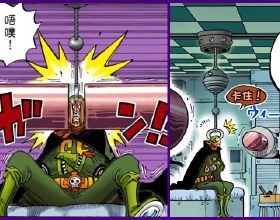【文化的江山】
李冬君/文
南宋人的空間感的確縮小了,潛意識裡的“殘山剩水”,因南北對峙以及主戰與主和兩陣的殘酷之爭,沉澱為時代的隱痛,如薄暮晚煙在山水畫裡彌散。
作為時代最敏感的部位,藝術的表現往往領先。南宋初年,在宋高宗親自領導下,李唐、蕭照、馬和之等人參與的歷史題材創作,無不被時代主題所激勵,君臣勵志收復失地,同仇敵愾要把殘山剩水補全。而山水畫作為主流畫壇的主流,雖然比起人物花鳥等其它名目更偏向於藝術,但它仍無法超越於它所處的時代命運,“殘山剩水”也是它的時代印記。儘管也總有人憤憤於歷來對“殘山剩水”基於時代情懷的政治解釋,但那是南宋山水畫的胎記。一般來說,出身的底色,會如影隨形。所以,你可以從藝術風格的創新來讚賞它,也可以從藝術的立場來辨析它的精神底色。畫有畫風,也有畫格;風格,風是形式,格是精神正規化,是一種持守。兩種評價都無法否認,南宋山水畫浮游著一種頹廢的傷感,暗示了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非分之想”。
殘山剩水無態度
北宋人應運而生,他們懂得如何誕生宏大並在宏大中保持獨處。如張載“橫渠四句”,恐怕是繼孟子之後飈出的儒生最具抱負的口號;而蘇東坡卻在流放生涯中自塑個體人格之美,併成為後世典範;王安石在變法中將他的人格理想奉獻給他的國家主義之後,如一顆悲壯的流星劃過十一世紀;范寬在《溪山行旅圖》中再造高山仰止的全景式山水,米芾則以“逸筆草草”開創了大寫意的山水款式,具有里程碑風範。如此等等,這種恢弘的、文藝復興式的人文風景,在南宋轉而內斂了。
陸游、楊萬里、朱熹、陸九淵、辛棄疾、陳亮以至於文天祥,在他們的詩詞裡,大好河山都在北方,南宋的秀山麗水,攏不住他們的“全景”意志,他們的主戰共識,會時時提醒迫不及待要安頓下來的南宋人,在臨安中不安,在偏安中難安。
南宋畫界,像蘇、米、李公麟等西園十六士那種士林已不再,馬遠和夏圭作為宮廷畫師,與北宋畫家的精神格調完全不同了。他們既沒有承繼北宋士林,也不屬於南宋士林圈。因此,他們既不過分渲染儒家的入世人格,也沒有鋪張老莊的出塵,他們似乎只要一種“臨安”,過著隸屬於皇家工匠化的藝術家生活。
生命無限堆砌,在這個地球上,誰的人生不是一種臨安狀態?如果“臨安”還居然能留下一點痕跡,人類便沾沾自喜,自以為永恆了。
精英們會製造時代精神,也反映時代精神。因此,不斷有人批判南宋山水畫中的“殘山剩水”,是一種偏安臨安的安逸態度,儘管這態度時時帶點傷感的風月調。據說惟蒙元滅宋後始謂之“偏安”,“偏安”還有點中原中心論意識,但南宋人卻在安居中向海外開通了海上絲綢之路,他們不是“直把杭州作汴州”,而是放眼泉州已經是世界三大港口之一了,直到被蒙元滅亡後,南宋人才如夢初醒,來自海上的大多是貿易,而來自北方的鐵騎,則已經由搶掠上升到直接登堂入室坐天下了。南宋亡得固然酷烈,但日本人所謂“崖山之後無中國”這一提法,不僅會令人誤解,也會引起歧義。“無中國”,是指不光趙家王朝亡了,還有文化中國也亡了,創造文化中國的人種也滅亡了。事實是,至此南宋以前的文化中國,不僅在不及百年的蒙元時代、不僅在日本得以傳承和發展,即便明清王朝嬗替,而文化中國猶在。
蒙元治下的南宋人又重啟了耗費上千年的興亡反芻,“殘山剩水”的院畫體便成為他們咀嚼的“邊角”料。也許是遺老遺少們遺恨難釋懷,正如一首詩所吟:“前朝公子頭如雪,猶說當年緩緩歸”,“殘山剩水年年在,舞榭歌樓處處非”。從此,便帶偏了南宋山水畫格的鑑賞路徑,偏離了藝術判斷的軌跡,諸如“截景山水”或“邊角山水”的空間關係,留白的暗示與讓渡、幽邈與聚焦的聯想等等,這些藝術的新表現都被拿到興亡的鏡片下顯影。
明朝人接著說:“是殘山剩水,宋僻安之物也。”若談山河殘破,首推杜甫“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經典,而在殘破的廢墟上建國,則數宋高宗趙構踐履非凡;就在藝評家們為剩水殘山的畫格嘉譽時,辛棄疾已經開始在詞裡拿捏這種風月調了。
宋高宗南逃之際,殘酷帶給他如影隨形的晦暗,並未改變他堅持北宋文人政治的信念,抗戰期間南宋的頭條,就是君臣勵志於“藝以載道”、“禮樂教化”、“耕讀民生”的國策,在公元十二世紀初,同樣彰顯了一種廢墟里的國民尊嚴、以及精神不可缺席的態度。這態度表達了一代新王朝落定杭州的理性,也是一個新王朝存在下去的理由。怎奈殘山剩水天生麗質,誘使金人咬定青山不放鬆。主戰與主和的激烈對峙,如雲遮月給這種戰時的風月帶來陰晴圓缺般的搖擺。明知起點是風月、終點便是第二個“宣和年”,辛棄疾也只能作一聲無奈的長嘆,將嘆息落在朝廷的“無態度”上。
所謂“殘山剩水無態度,被疏梅,料理成風月”,這是“詞中之龍”辛棄疾的扼腕名句。這位“醉裡挑燈看劍”的偉大詞家,僅15個字,便將南宋朝廷的政治畫風料理分明,他借用“馬一角”和“夏半邊”的山水畫格,譏刺朝廷不思北伐、躺平殘山剩水,還要把這種政治風格打理成疏梅折枝、吟風弄月般的一派風雅。
歷史的折射常常是模稜兩可的,可以贊宋高宗在廢墟上的精神建設,也可以同情辛棄疾北伐無望的長嘆,關鍵從哪種立場進入。
歸正人的態度控
辛棄疾與馬遠同年生於1140年,他們出生的第二年,南宋便“紹興議和”了,宋高宗終於結束流亡,“臨安”杭州了。
辛棄疾出生於淪陷區金人治下的山東濟南,而馬遠則生於剛剛榮勳為南宋首都的杭州。夏圭與馬遠同鄉並譽,位列宋畫南四家。在南宋人眼裡,李唐、劉松年、夏圭、馬遠最懂山水,而馬、夏兩人的山水畫風,竟如一對孿生兄弟,一個棲息於“全景山水”的某一處最佳角落,一個擷取全景山水的半邊憑依,沉浸在有節制的山水情懷中。天生一副對子,“馬一角”和“夏半邊”,格調對稱,溫暖的陰影,也能與南宋人民居於半壁江山的心理陰影重合,而且天衣無縫。
藝術與時代的關係,還有如此貼切的嗎?只能說他們高度概括了時代的心理特徵,帶給時代強烈的暗示,誘請人們住進“殘山剩水”,躺平臥遊。
1161年,辛棄疾在北方起義抗金,手刃叛徒南歸,被宋高宗任命為江陰籤判。此後,卻因他是“歸正人”,再加上主戰派,在朝廷上總是被排擠,幾起幾落,直到1204年出知鎮江府時才受賜金帶。作為64歲的南宋宿勳,身披宋寧宗賜予的榮譽勳章,想必龍性難馴的“歸正人”對這份遲到的榮譽早已倦怠,具有諷刺趣味的是,此時的賞賜變成了對倦怠的加冕,而對辛棄疾來說,它本來就是個純裝飾品。
不過,“歸正人”的提出,是南宋走向衰亡的敗筆。1178年南宋淳熙五年,宋孝宗趙昚頗為器重的丞相史浩,第一次提出“歸正人”的概念,朱熹解釋為:“歸正人元是中原人,後陷於蕃而復歸中原,蓋自邪而轉於正也。”一看便知,這是針對從北方淪陷區來投奔南宋的人的統稱,而且是帶有懷疑和歧視性的圈定。
史浩在十幾年前曾識破了北來間諜劉蘊古,並與高宗時名臣張浚有過辯論,他說:“中原絕無豪傑,若有,何不起而亡金?”史浩出此奇葩言論時,正逢辛棄疾在北方首義後投奔南宋之際,那時辛不僅僅是熱血青年,還是手刃叛徒的英雄豪傑,以史浩的純儒見識,他也不會側目一個年輕北人是什麼北方豪傑。即便十幾年後,史浩仍未因辛棄疾在南宋的貢獻而改變對北人南投的看法,反而更加警惕,將北人南投定義為“歸正人”。
史浩、朱熹都是江南原住民,朱熹是南宋理學大家,官也做到了皇帝侍講,就因為北人食了“金粟”,南投便是“改邪歸正”?朱熹出此言論,真讓人懷疑思想家是怎樣一副心肝,迫同胞於兩難。史浩,堂堂一朝宰相,不會不知一個擁一國之力的朝廷,為什麼不“亡金”而南逃?卻去譴責北方無豪傑?北方難道不是堯舜禹湯文武所立之地?北方不是周公仲尼所化之民?北方不是大宋天子南逃時帶不走的遺愛子民?
在“家天下”的秩序裡,家僕式的慣性思維,向來訓練有素。一切正義,皆圍繞以家長為核心確立的既定秩序。這種思維培養不出政治家的視野、心胸、風度以及智慧,只會培養以家長為圓心的半徑心胸和半徑眼界。不管他們對朝廷有多麼忠孝;不管他們多麼擅長宮闈智慧,他們本人的心態以及倫理習慣都是家僕式的;他們大多熟練家僕式的狡詐,但那並非政治家的智慧,而對北人南投的懷疑和歧視,才是王權治下的正常邏輯。
在“歸正人”正當化兩年後,辛棄疾開始在江西上饒修築帶湖莊園以明志。明什麼志?當然是歸隱之志。他不能像岳飛那樣還未踏上“賀蘭山闕”,便出師未捷身先死,他要把帶湖莊園修得既有桃花源的歸隱氣質,又要有園林式的雅浪,表明他已經沒有岳飛那種武將雄心了,他要向文人轉型,像陶淵明那樣掛冠歸去,歸正人不管北人南人,總之,他不要岳飛那樣的結局。褪去英雄本色,辛棄疾以歸隱的方式,逃離家天下的權力半徑,也是傳統體制和傳統文化給士人留下的一個可以迴歸自我、還原自由的唯一路徑。
一個人若在內心打開了審美之眼,他便無法對醜寬容或熟視無睹。那份執著的能量,只能依據它所隱藏的痛苦來掂度。整整八年,辛棄疾在帶湖莊園熬製他欲作北方人傑而不得的痛苦。1188年,老友陳亮來拜訪帶湖莊園,二人相攜再遊鉛山鵝湖,自稱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鵝湖之會。陳亮索詞,辛稼軒欣然命筆,豪抒北志難伸之二十多年的積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可發千里一笑”:
把酒長亭說,看淵明、風流酷似,臥龍諸葛。何處飛來林間鵲,蹙踏松梢微雪。要破帽多添華髮。剩水殘山無態度,被疏梅,料理成風月。兩三雁,也蕭瑟。……(《賀新郎·把酒長亭說》)
蕭瑟之處,風景別幽,總有二三知己把酒,辛棄疾與有榮焉。終宋南北三百多年,榮與蘇詞舉世並譽;幸與陳亮莫逆顧盼,豪傑氣概冠宇。尤其,辛、陳皆有臥龍之志、經營天下之才,卻又不得不審美淵明的生活方式。先覺者必定孤獨,當“兩三雁”被體制疏離而又不妥協時,為了避免宮鬥,辛只有選擇歸隱。歸隱,這種帶有遠觀的審美生活方式,也許可以稱它為士林精神的一個終極。
另一終極,當然是修齊治平。孟子早就說過:達者兼善天下,窮者獨善其身。這句話居然印證了一種機緣,巧合了孔孟和老莊兩極,而且深蘊知識分子心靈,源遠流長於士林的精神指標和古老的理想主義。儒家入仕,老莊出塵,均根植於辛棄疾的精神體內,無論住在帶湖山莊改號為“稼軒”,還是在瓢泉莊園誓種“五柳”,他都是在跟自己歃血為盟,明歸隱之志,以歸隱自囚。
辛棄疾與馬遠同朝為官,想必對馬夏並不陌生。1188年辛、陳第二次鵝湖之會時,辛、馬都已經48歲了。馬氏家族五世院畫待詔,先祖叔侄皆畫,畫格家風薪火相傳,作為宮廷畫師在北南宋主流畫壇獨領風騷,佳話藝評流行南宋。夏圭雖沒有顯赫家世,純粹以畫鵲起,與馬遠大部分時間一樣,同仕光宗、寧宗兩朝,受賜待詔、袛侯。
辛棄疾為“歸正人”,雖被壓制到從四品龍圖閣待制,那也是朝官,待制可不是沒有品級的待詔、袛侯。袛侯與待詔意思差不多,為恭候靜候之意,名副其實的話,都是皇家的家臣,與上朝議事、知府地方的大臣們地位不可同日而語,而且家臣進不了正史,宋史會為辛棄疾專門立傳,但不會為馬夏立傳,所以馬夏的事蹟是模糊的,而辛棄疾是有年譜的。一個是家臣,一個是朝臣,圈子不同,各執其事,各個完成自己的風範。但身為人臣誰又不是臣子呢?誰又能逃離家天下臣子的藩籬?誰又不想拼命隸屬於體制這個大圈子呢?本質上,朝臣與家臣不都是為臣的命嗎?好處是各執其事,才有辛棄疾借宮廷畫師的畫風譏刺小朝廷在殘山剩水裡品味。
山水無常有態度
從藝術的角度看,殘山剩水是有態度的。
讀南宋“小團扇”,畫面上的小人物,姿態幽默,比大人君子正襟危坐有趣多了,方悟其精妙在於放下。放下“全景式”大山的理想與完美,也放下踽踽于山根小路上朝聖的謙卑。畫家們更喜歡坐在松下撫弦撩風,握手水面吹來的琴聲,嘆息無常帶給個體命運的凌亂,內心卻更加篤定人間煙火的一角,感懷時有半邊山水足夠一人寥落。
北宋那種撐滿畫面的神聖高山,煙消雲散了。即便是半邊山、一角水,也總會隱約在煙巒之間,謙卑的命運感,留給無常一個渺遠的空,是讓看畫的人看空嗎?南宋的山水畫,似乎更重視一種不確定的印象表達。以馬、夏為例,在山水的一角或半邊的後面,即將到來是什麼?誰也不知道。無常的守望和不確定的鄉愁,在殘山剩水間靜候,在無常結構的時間裡等待,等待著留白……,留白中汩汩著無盡的傷感美學,打動了歷代畫壇,稱譽之為“殘山剩水”或“真山真水”。
隨意擷取目之所及的山水邊角料,敷衍身在其中的氣氛,寫生“人與山川相映發”,當然是“真山真水”,不過,作為山水畫風格的“真山真水”,主要還是針對北宋“全景山水”提出的。“全景山水”是剪裁自然,而且是黃金剪裁,將山川最理想的截面拼接到一個畫面上來,它不是真實的,卻是理想的。
而經此南渡之變,無常感使南宋人轉而珍惜身邊實景、珍惜小而精美之物,珍惜有時間感的、可供掌控、近在眼前的美物。黃金剪裁、金玉拼接,不都被命運肢解了嗎?什麼是順應自然?就是眼前景是什麼就畫什麼,真山真水並不都是完美的,自然的美多半是殘缺的美。南宋的這種殘缺美,在日本發展為不對稱的美學正規化,日本人謂之“傾”。
既然放下“大全景式”,“小團扇”更適於表現山水一角或半邊山水,流行為專門的繪畫形制,南宋的畫家們很喜歡在小團扇上作畫,表達小的意志,表達小的極致,連李唐晚年也開始了小團扇畫畫殘山剩水。正如董其昌在《容臺集》中所說:“宋以前人都不作小幅,小幅自南宋以後始盛。”
從審美意識來說,相對於范寬的《溪山行旅圖》,南宋人不擅長應對宏大主題了。以腳度量道路的南宋人,不管是人腳、驢腳、牛腳還是馬腳,他們不再努力去識別形而上的大山的真面目,而是輕手輕腳地走在山中小路上,也不再像北宋人那樣用理念建構全景山水的宏大敘事,而是溫情點染甚至飄過留白,畫面上因無奈而趨於寧靜,那種幾乎能聽到的一種頹廢的寂靜,浮泛著一股惆悵的魅力。南宋人抒懷太吝嗇了,只在一角半邊裡揮灑,卻一再強化柔弱的意蘊,文質彬彬中將憂鬱化為詩意。如果說北宋山水畫如謝靈運的山水詩,那麼南宋山水畫則如陶翁的田園詩。山水詩是有格有律的格律詩,而田園詩是老農詩,依四時變化即可。
從藝術的角度,畫家關注人生,也關注現實,是必不可少的美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為現實營造一種氛圍,應該是繼批判之後更具有建設性的知行合一,當南宋人走進他們營造的審美氛圍裡,人們可以不用歌頌,只要傾訴,而歌頌會疏遠,傾訴會拉近。
有人說“殘山剩水”隱喻南宋偏安是後人的附會,從繪畫藝術的角度理解,應為一種繪畫風格的轉變,甚至是一種對北宋山水畫的批判或叛逆。的確,藝術的本質就是不斷超越、不斷尋找表達自我感受的符號語言以及與之呼應的獨特形式。
如上述,畫面所傳達的情緒與時代的傷感情調吻合得天衣無縫,這又何嘗奇怪呢?畫家是一群最敏銳的時代氣息吮吸者,他們身份卑微卻又在時代主流中潛泳,不管他們自覺抑或不自覺,時代痛苦或歡欣的影子總會隱約在他們作品中,何況表現時代氣質,也是藝術的本分。因此,隱喻也好,風格也罷,都是作品本身自帶的張力,對於畫家來說,每一筆都只表達那一筆瞬間的領悟,每一筆都在為情緒謀求出路。魯迅說它們“萎靡柔媚”,踩著了南宋時尚的點兒,大概就是一種“安”的狀態吧。
南宋人的空間感縮小了嗎?如果僅從具體的個體對於生活空間的感受來說,在開封和在臨安沒什麼大小之分,是時代的窘境形成普世的心理逼仄,精神空間的折損在剝蝕歲月裡填補痛點,連楊柳岸都要曉風殘月,而彌補疼痛的良藥便是神遊在這殘山剩水間。
現實中,飽滿與虛無交織,豐盈與無常博弈,藝術家興奮了,他們解構了北宋山水畫的造山等級,不再高山仰止,可望不可即,而是就在飽滿與豐盈的世俗邊上營造一個幽邈的空無,在物慾的邊上給出一個精神鄉愁的棲息地,而且觸手可得,隨時追隨神思消失在眼前的迷霧裡。但思想家憂鬱了,朱熹喊出了“存天理,滅人慾”,陸九淵回到自我“發明本心”,畫家則僅畫一個山水的邊角,便過濾了無常的焦慮,即便在一把小團扇下,亦可臥可遊。這個世界的有趣現象很多,比如畫家與理學家,風馬牛不相及的各自表達,就像一條河的兩岸。
北宋山水畫在新生代面前反而古意濃郁了,端莊嚴謹、對稱完美,卻被新生代的無常山水撞了一下腰;那種期待永恆的全景山水被南宋帶有時間感的“邊角”山水,又傾了一下腳。大山的主題主角消失了,只有邊角配角,留給時間一個殘缺的美。深蘊於哲學意味的“傾格”,作為美學樣式,始於南宋,流變於日本戰國時代。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