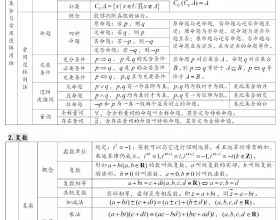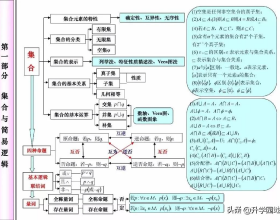當外面的羅馬帝國正在分崩離析時,一個新的、非常奇怪的機構正在其中建立--尚未統一的基督教會。因此,從教會的鐘樓上看羅馬的違憲崩潰,他們在這段時間裡到底是如何在國家中共存的,以及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樣的問題。
由於從君士坦丁大帝開始的幾乎所有皇帝的積極國家支援,教會真正進入了國家,並與羅馬人的單一偉大文明和一個無懈可擊的皇帝的理念相融合。為此,猶太人的選民觀念(現在是神聖羅馬國的基督徒)被扭曲了,國王成了地球上的第一權威,因為他一般是上帝的門徒。皇帝召開大公會議,確認教條,如果他自己不是異教徒,就積極反對異端,如果只是因為一個宗教分裂的國家是一條單行道。皇帝的權威可以歸納為:教會在國家中,所以君主是我們的法官。
當然,無論給皇帝加了多少個 "聖人 "的字首,他們還是會被成群結隊地拆掉,尤其是在西方。就這樣,沒有持久的力量,半個羅馬帝國歸於野蠻人,這對教會有什麼區別呢?對教會來說,不僅普世的國家已經崩潰,而且信徒們也開始受到異端野蠻人的壓迫,這是很痛苦和尷尬的事情。在這方面,向西方爭取恢復帝國的運動成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們的神聖職責:第一,這是我們的,不是討論的;第二,正統的基督徒被冒犯了! 只是在查士丁尼時期,因為帝國終於有了休息和恢復的機會,而西部的野蠻人則繼續相互爭鬥,或者像汪達爾人那樣被塵土所覆蓋。
而在帝國重建的同時,在西方,在羅馬,只剩下一個完整的穩定的代表陷入困境的基督徒的島嶼--羅馬牧首。在一個皇帝先是像手套一樣被更換,然後又被完全剔除的時代,羅馬教皇看起來是一個完全足夠的、令人滿意的實體。想想看,對異教徒阿提拉來說,不是皇帝在談論撤退,而是羅馬教主在談論釋放囚犯。但是,當教皇在入侵的哥特人面前捍衛東正教的權利時,卻與君士坦丁堡因芝諾這樣半信半疑的皇帝發生了摩擦。衝突甚至更進一步:作為一個原則問題,羅馬不喜歡皇帝對第一個基督教大教堂的喜歡程度低於其他。
最終,當拜占庭人最後一次失去羅馬城時,大教皇回到了現在著名的與野蠻人半獨立共存的道路上。只有查理曼大帝被信任為上帝在地球上的傳教士2.0,如果他能尊重教會的適度領土要求。而事實已經證明,教會似乎在國家中,然後根本就沒有國家,也就是說,一般來說,羅馬教會就是國家本身,不需要諮詢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