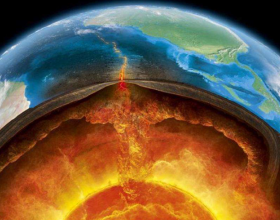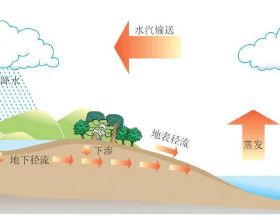陳介祺(1813-1884),字壽卿,號簠齋,晚號海濱病史,濰縣(今濰坊市)人。
2013 陳介祺200週年紀念郵戳
清代,金石學大興於天下,此勢直至清末仍未衰竭。相反,在此時卻出現了許多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如阮元、吳大澂、翁同和、端方、王懿榮等等。這其中,陳介祺無疑是佼佼者,他與曾獲有大盂鼎的江蘇學者潘祖蔭被譽為“南潘北陳”。
陳介祺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考中進士,在此後整整十年的時間裡,一直在翰林院供職,這是個閒職,對從小就喜歡文物的他來說,是個難得的機會。他曾向當時著名的金石學家、書法家阮元請教,也曾與何紹基、吳式芬、李方赤等金石學者來往密切,常在一起談金石、話收藏,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提高了鑑賞水平。另一方面,他身處京城,頗有近水樓臺先得月之勢,許多豪門大宅,物藏豐富,為他提供了方便。京華的琉璃廠,是他經常去的地方,在這裡他見到來自全國各地的文物。多年來,陳介祺在這條冷闢的收藏路上艱難地行走著,幾乎傾注了全部身心。經過多年不懈的求索,他的收藏已頗具規模,僅三代,秦漢古印一項就蒐集了近萬方。這些古印,有許多都在京城所得,後來他編成了《籃齋印集》。道光三十年(1850年),他在濰縣建成了“萬印樓”,將所得古印藏於其中。此樓至今仍在,並已對外開放。
西周毛公鼎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在陳介祺的收藏生涯中,日益豐富的藏品常使其喜出望外,但最令他欣喜若狂還是得到毛公鼎的那些日子裡。該鼎於清道光末年在陝西岐山出土,內壁有周宣王時的金文(大篆) 479字,是至今我國出土的銅器中字數最多的一件器物,有著極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被人們稱其為海內吉金之冠。它也是陳介祺藏品中最珍貴的一件。據說,得到此鼎後,陳介祺親自將其護送回濰縣,陳家收藏毛公鼎半個多世紀。毛公鼎對陳介祺來說,應是他收藏上的一個里程碑,欣喜之餘,他幾番考證了鼎上的金石文字,並椎拓成片,分贈海內親友。
咸豐四年(1854年),陳介祺的母親病故。他以母喪之機返鄉,從此再也沒有踏入官場一步,開始了長達30年的研究,著述工作。
據不完全統計,他藏有商、周古鐘1件,為此,他把“萬印樓”改為“十鐘山房”。他還藏有“商周銅器253件,秦漢器物80餘件,以及秦漢刻石、古錢、陶、瓷、磚瓦、碑碣、造像、古籍、書畫等精品萬件以上”。擁有如此豐富的文物,他並沒有躺在上面睡大覺,也沒有“玩物喪志”。他每得一物一器,必究其淵源,或拓片存檔,或記錄在案,兢兢業業,一絲不苟。他對金石學家王懿榮談起自己的治學體會時說:“學問之事,全在分析,而不籠統,籠統只是不分析,分析得出十條路,方知此一條是,九條不及,而知之愈真,行之彌篤,此皆分析之力也。”他的一張漢磚拓片,不足一平尺的紙上,密密麻麻寫下了近200字。他嚴謹的治學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蟬翼拓
陳介祺作為清末的一位收藏大家,在當時已名震朝野,但他卻能放下架子,不恥下問,熱情向農民兄弟交朋友,向他們學習,這在封建社會里是少見的。當時還沒有照像術, 搞金石研究的人常需要“推拓”,只有椎拓才能如實地把物件複製下來,如此,推拓便成了一種十分重要的方法。陳介祺與拓工劉某,經過反覆研究,創出了一種名叫“蟬翼拓”的方法。用這種方法,拓片不僅立體感強,字口清晰,而且墨色均勻,如“淡淡籠月”。也許正因為有了這種方法,陳介祺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拓片,從這上面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發現和創造,同時,也常常會讓我們想起這位為祖國文物事業奮鬥了一生的老人。
陳介祺一生著作等身,據統計約30種以上。已正式出版就有十餘種。陳介祺書法造詣頗深,篆書極有個性。名為篆書,實際上是以楷法寫篆,中間還參以隸意。特別是其結體偏長,筆畫粗細差別較大,有人評其“ 取北朝後期書體雜揉之法”,因此,情趣盎然,韻味無窮。”(作者徐開揚,號靜逸翁,系中國收藏家協會會員)
陳介祺篆書
(靜逸翁談收藏[三]藏家趣事之三:毛公鼎收藏者陳介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