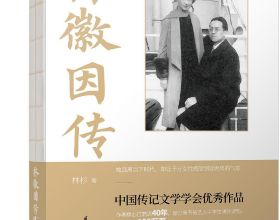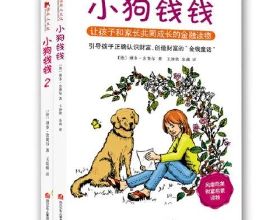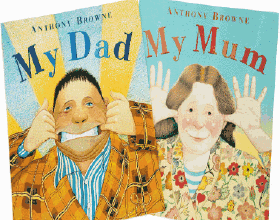每位走進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副院長、肝膽外科主任醫師蔡建強門診室的患者,腳步都輕而急切,尤其初診患者,往往人還沒到,手中拎著的或厚或薄的CT片、病歷資料已迫不及待先遞過去,甚至手有些發抖,說話也有點亂,心中的緊張、惶恐、希望交織在一起,怎麼也掩飾不住。

我國是肝癌高發國,始建於1958年的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是國家標誌性腫瘤專科醫院,目前日均門診量4000人,十分之一屬於肝膽腫瘤。來自全國各地的患者,很多把這裡作為生命最後一絲希望。
蔡建強深知這一點,他總是先關照他們坐好,邊輕聲詢問,邊抽出CT片對著燈箱一張一張細細檢視,不多言語間,病情大概知曉,患者情緒也穩定下來。他再對下一步檢查、治療如實給出初步意見。
他不拒絕任何一位患者,要求自己和團隊竭盡全力留住他們,在提高生存質量前提下,延長患者生存期。“竭盡全力”在蔡建強的詞典裡不是程度副詞,而是動詞。
當住院醫時,他每天守在病人身邊18個小時,從清晨到深夜,積累豐富臨床處置經驗;在日本作訪問學者一年間,他觀摩600多臺手術,最終破例以訪問學者身份成為主刀醫生;他守床22天搶救一名結腸癌手術後罕見過敏症患者成功,曾震驚世界同行。
這名被全世界專家判“死刑”的患者,至今健康地生活;他建立消化道腫瘤多學科會診(MDT)體系,歷時13年打造出一支讓患者信賴的國家隊,不僅幫助患者對抗疾病,而且讓他們始終保有生命的尊嚴。
身為副院長,蔡建強在幾任醫院領導努力基礎上,和現任班子一起想辦法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等問題,成立國家癌症中心、完善腫瘤登記制度,力爭讓更多人對腫瘤防治加深瞭解。
作為主任醫師,蔡建強出門診、做手術、搞科研、帶團隊、教學生、抓培訓……要做的事實在太多。即便已經擔任院領導,蔡建強每週還出半天門診,主刀至少三臺腹部腫瘤複雜手術,進行一次大查房。
他幾乎沒有屬於自己的時間,每週雷打不動地運動,也是為了更好地投入工作。只要對患者有益的事,蔡建強都去爭取。他說:“高超的醫術、高尚的品格、對醫療質量的把控和追求,是永恆的”。
對醫療質量的把控和追求永恆
有一組資料概括我國肝膽惡性腫瘤發病狀況:2015年,我國肝癌發病率為28.71/10萬人,位居我國腫瘤發病率第四位,死亡率則排第二。患病人數佔全世界肝癌發病總人數47%。此前,這個數字是55%。
蔡建強說,隨著近年來我國肝癌發病人數整體下降,這個佔比有望進一步下降,到2030年發病率降至40%左右,而五年生存率將提升12至15個百分點,“五年生存率是肝癌治療一個重要指標,每提高一個百分點,都要下很大功夫”。
蔡建強已經為此奮鬥35年。1985年自白求恩醫科大學醫療系畢業後,蔡建強被分配到北京,同屬協和系統三家醫院:阜外心血管病醫院、整形外科醫院和腫瘤醫院,他選擇最後者。
“越來越多人患有腫瘤,而且腫瘤更難醫治,我相信自己可以在這方面幫助更多人。”彼時,位於北京龍潭湖畔的腫瘤醫院外科只有胸部外科和腹部外科,蔡建強再次選擇後者,因為腹部臟器比較多,能做的事更多。
工作後,蔡建強師從我國著名腹部腫瘤外科專家、腫瘤醫院腹部外科主任醫師餘宏迢教授。
餘宏迢從事腫瘤外科工作40餘年,臨床診療經驗豐富,擅長診治腹部及乳腺腫瘤,肝、膽、胰腺癌手術水平高。“當時腫瘤醫院技術力量就很雄厚,餘宏迢教授那一輩建立了一整套外科治療腫瘤的基礎”,至今,“餘派”手術要領仍為蔡建強腹部腫瘤手術技術基礎。
在臨床中,青年醫生蔡建強發現有很多東西要學習,要提升。那時,中國醫療也逐步和國際接軌。
在這一背景下,蔡建強1994年赴德國杜塞爾多夫海因裡希·海涅大學血管外科中心參觀學習。當時他已有10年臨床經驗,但按照海涅大學規定,他在學習期間不能接觸病人,更不能動手做手術,只能觀摩。
他還記得第一次看心臟移植手術,“各種複雜管道系統井然有序地呈現在面前,整個過程就像看天書一樣”。蔡建強被驚到,“真是天壤之別”。每次觀摩,他都拿著本子努力把自己看到的都記下來、弄明白,每一筆都帶著使命感。
回國後,蔡建強在科室前輩支援下,與同事提升確保手術安全技能,使腫瘤醫院腹部外科腫瘤治療更專業化,技術逐漸成熟,手術死亡率降低,手術治療腹部腫瘤技術逐漸成熟。蔡建強也逐漸確立自己對肝臟和消化道腫瘤方面的研究方向。
五年後,蔡建強又赴日本,在以醫學和藥學立足的熊本大學醫學部作一年訪問學者,與平岡武久教授等幾位日本著名外科專家交流共事。
“日本是胃癌與肝癌高發國家,病人比較多,醫生手術技術也比較成熟,在亞洲治療消化道和肝臟腫瘤方面比較領先。”
那時,國內腹腔鏡手術剛起步,日本則很普遍。蔡建強珍惜近距離觀看手術的機會,“每天早出晚歸,泡在醫院裡”,一年時間完整觀摩600多臺手術。9個月後,蔡建強破例以訪問學者身份主刀手術。
訪學歸來,蔡建強立刻帶領團隊在腫瘤醫院開展系統性肝切除研究等工作。
2003年,蔡建強團隊提出的“應用解剖分離方法進行肝段聯合切除治療肝臟腫瘤”,透過衛生部成果鑑定。
他們對2001年9月至2003年12月收治的53例肝臟腫瘤患者採用解剖分離方法進行肝段聯合切除,術後無1例發生嚴重併發症或死亡,並將原來40%左右的併發症發生率降到7.54%。後來,這一手術方法被多家醫院採用。
透過分層解剖和去漿膜外組織行消化道吻合方式,大大降低胃腸手術後發生吻合口漏的情況,從而對消化道腫瘤手術建立起安全體系。
以往,全胃切除是死亡率很高的手術,截至2007年科室功能細化前,蔡建強團隊所做的全胃切除有300例左右,無一例死亡。結直腸手術死亡率也是0。以追趕者的狀態,蔡建強和同事們努力著,“現在差距已經不大了”。
2016年,12歲的小佳被當地醫院診斷為肝癌(後經腫瘤醫院診斷為巨大肝臟腺瘤)。父母帶她輾轉省內多家醫院求醫,結論都讓人絕望。幾經輾轉,小佳來到腫瘤醫院腹部外科,蔡建強記得第一次在門診見到小姑娘的情形,“很憔悴,臉色蠟黃,是典型黃疸表現,一看就知道病情不輕”。
CT片顯示,小佳的巨大腺瘤位於左肝,15釐米大小,幾乎佔據整個肝葉。由於腫瘤過大,壓迫肝內膽道,已引起較重黃疸。蔡建強立即讓小佳住院,進行保肝、營養等對症治療的同時,決定是否進行手術切除。
腹部CT、核磁檢查……一沓沓檢查化驗資料擺在面前,蔡建強表情凝重,絲毫不敢疏忽。“手術意味著要切除掉病灶和病灶周圍的正常肝組織,這對病人肝功能是一種巨大打擊。許多巨大腫瘤的患者,尤其是兒童,很有可能因為術後肝功能衰竭而危及生命,因此術前評估對於肝臟腫瘤治療至關重要。”
多年臨床外科經歷,他深知,這麼小的患者進行如此大的手術,充滿風險和挑戰。而且小佳的腫瘤貼近重要血管,“稍有不慎就會引起致命出血,這也可能是之前醫院認為難以手術的原因”。但,手術是患兒小佳唯一的生存機會。蔡建強下定決心:“做!”
入院第四天,小佳在全麻下接受左肝不規則切除術。按照當時醫療條件,手術中有一絲一毫差池,鮮活的小生命就會驟然逝去,蔡建強說:“打著12分精神做手術。”從早上8點到下午3點,整整六個小時,蔡建強用肝臟不規則切除術,採用解剖性分離方式,切除肝臟腫瘤病灶及病灶周圍2釐米正常組織,最大限度保護肝臟,並將術中出血降為平常的1/10,暫時留住了孩子。
“肝臟不規則切除術需要術者非常熟悉肝臟解剖,對腫瘤病灶有精確評估,才能夠順利地進行切除。又因為小佳是個孩子,每個動作、每次暴露病灶都更加精確和小心,也許一不留神就會導致整個手術失敗,現在想想都還有些後怕。”蔡建強的學生、腫瘤醫院肝膽外科主任醫師畢新宇當時任助手,對那次手術記憶猶新。
手術成功,包紮時,連小佳背後的腹帶,蔡建強也逐一輕輕撫得平平整整。在腹部外科醫護人員精心呵護下,小佳闖過肝臟腫瘤手術後正常的肝功能異常關,順利康復。
14年過去,如今小佳健康美麗,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和同齡女孩一樣喜歡追劇。她時常問候蔡建強,還有那些守護過她的醫護人員。
在一封信中,她曾寫道:“蔡主任,請允許我親切地叫您一聲‘爸爸’,是您用精湛的醫術、慈愛的仁心挽救了我,挽救了我的家庭,是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赫捷院長上任近10年來,我們醫院醫療質量、水平,醫護人員培養都不斷提升,在第三方評價中,我們連續十年排名第一,一直在引領腫瘤治療方向。”
2012年,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國家癌症中心成立,引導全國腫瘤早診早治、做好全國腫瘤登記工作的職責越發明確。三年後,我國第一次正式公佈腫瘤發病率、死亡率及各地區發病數字,空白逐漸被填補。
蔡建強親歷變化:“我國腫瘤防治工作到了最好時期,國際上也得到認可,腫瘤登記、城市腫瘤防治等方面文章,陸續在久負盛名的同行評審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期刊》和全球影響因子最高雜誌《臨床腫瘤雜誌》上發表,這在以前沒有過。”
從醫35年來,蔡建強記得自己收治的所有患者
為晚期腹部腫瘤治療開啟新路徑
在人類與惡性腫瘤鬥爭史上,多學科會診(Multi-DisciplinaryTreatment,簡稱MDT)診療模式建立是一個里程碑。“MDT就是醫院多學科骨幹醫生在固定時間、地點,對個體病例進行討論,團隊協作為患者設計最佳診療方案,並定期進行反饋評估,從而使患者獲得最佳療效。”
2007年,在前輩倡導多學科合作治療基礎上,蔡建強建立腫瘤醫院消化道腫瘤MDT。這一年,據世界衛生組織年度健康報告,全球每年有62萬人死於肝癌。這一年,肝癌靶向藥物問世,原發性肝癌臨床治療向前邁進一大步。但肝癌發現時中晚期比例還很高,能夠接受手術的肝癌患者只有15%-20%,蔡建強和團隊於是先將MDT救治重心放在中晚期肝癌上。同時,結直腸癌肝轉移比例高,也是治療失敗主要原因,患者和家屬往往容易失去信心。
為了讓更多患者得到治療機會,MDT團隊向醫院申請增設結直腸癌肝轉移專病門診。經過13年發展,複雜消化道腫瘤患者病歷幾乎都打破科室界限,納入MDT系統,“開啟電腦,一目瞭然,無法隱瞞”。
腫瘤醫院素有使用綜合手段進行腫瘤治療、尤其惡性腫瘤治療的傳統。“老院長吳桓興一直倡導,但此前會診只有外科、化療科、放療科,一個科室一個科室看,判斷先做什麼治療,不同科的醫生有時對治療方式說法不一,容易引起醫患矛盾。並且,手術是過去治療第一選擇,如果外科會診認為已經無法手術,也就沒有其他更多辦法”,蔡建強打破正規化,把診斷科、病理科納入進來,由五大學科組成MDT核心力量。
在蔡建強看來,MDT是一種理念。介入治療科副主任醫師韓玥說,蔡建強經常提醒大家,“腫瘤治療不是單打獨鬥,手術只在腫瘤治療某個階段是主要方式,腫瘤治療需要多學科通力合作”。
起步不易。蔡建強聯合其他科六七位志同道合的醫生,從聯合查房開始,默默開啟MDT模式。目標從開始就定得很高——每個人都一定要為打造一支值得患者信賴的、多學科診治的國家隊而不懈努力。蔡建強說,這是對MDT團隊每個成員的要求。
慶幸的是,MDT從一開始就得到內科腫瘤學專家孫燕院士、腹部腫瘤放療首席專家餘子豪教授、胸部腫瘤放療首席專家殷蔚伯教授等多位老專家支援,“孫燕院士當時70多歲了,還來參加我們MDT會診”,前輩支援,蔡建強念念不忘。
在腫瘤醫院,MDT治療要求是規範化、微創化、個體化。蔡建強認為,規範就是“多學科長時間高層次積累的經驗”,並無太多創新可言,更多是經驗運用。面對中晚期惡性腫瘤,醫生和患者往往面臨同樣艱難抉擇。
兩條甚至更多的方案擺在首診病人面前,但沒有一條路可回頭,判斷失誤、治療不規範……一旦走錯也許就是深淵。多學科支援下,晚期消化道腫瘤治療另一條路徑逐漸清晰。
“微創”是如今腫瘤治療高頻詞之一。
當下,腹腔鏡、介入、消融等微創手術在肝癌治療中所佔比例越來越高。“過去什麼都是開刀手術,現在有些病例用微創技術完全可以達到開刀手術效果,而且損傷小得多”。
蔡建強說。他有些擔憂業內外對“微創”的誤讀,微創並不是單指微創技術,也不是看手術傷口大小。微創治療有很嚴格適應症,只適合一部分患者,而不是全部。“微創是一種理念,貫穿治療全過程,病人從疾病診療開始到結束,所有治療手段都要達到最優,以最小損傷換取最佳治療。多做一個檢查、多吃一片藥、多花一分錢,都不是微創,都是重創”。
MDT團隊第一條理念是以病人為中心。2005年,某高校退休教師胡老師被診斷為直腸癌,幾年間三次出現肝轉移,總共住院21次,經歷三次手術。
之前她去過很多醫院,找很多專家諮詢,意見差別很大。在腫瘤醫院,胡老師成為納入MDT系統的患者。她很快接受肝臟轉移瘤切除手術,隨後在MDT團隊大密度隨訪中,踏上康復之路。
放療科主任醫師金晶說,腫瘤標記物升高會提示腫瘤復發的可能。根據不同情況,門診會給胡老師開B超、CT或者核磁檢查,確保檢出病變可能性。
治療前,診斷科透過讀片判斷轉移瘤的部位、數目、大小,為團隊專家治療提供建議。經過系統治療後,治療效果也需要透過診斷科讀片結果來進行判斷。影像診斷科主任醫師蔣力明說。
病理診斷是診斷腫瘤金標準,透過切片可以準確判斷腫瘤性質,為後續治療提供指南。這部分工作由病理科主任醫師應建明完成。
內科主任醫師周愛萍告訴記者,肝臟轉移瘤如果過多或過大,可以用內科手段來減少或縮小,以達到外科手術要求。“胡老師的轉移瘤是單發的,而且不是太大,所以她比較幸運,能直接透過手術切除。”畢新宇說。
病房門外,更多“治療”同步進行著。胡老師這位一輩子要強的高階知識分子,性格倔強,很長時間不能接受自己患病的狀態,跟家人、親友、同事關係也頗為緊張,蔡建強反反覆覆給她做思想工作,“包括如何處理與家人、同事之間的關係,我們都跟她一起想辦法。花了很多功夫。
後來她心態越來越好,理解親人苦心,慢慢懂得感恩,感受到他人關愛,反過來還能開導別人。這在治療初期都不可能,但這對她身體恢復太重要了”。
蔡建強說,個體化對MDT團隊而言,強調針對病人因人施治,把病人想盡辦法穩定在能夠提升他免疫機能的範圍內,達到MDT團隊設定的治療效果。“治療手段、方案、技術,以及病人心理要達到一定平衡,治療結果才會好。”
15年過去,胡老師如今已恢復正常生活,“我和團隊醫生建立了深厚情誼。之前我沒想到,蔡院長他們幾十人一起討論我的病,他們不僅對我有再生之恩,還是我心靈的老師。”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前,年過七旬的胡老師幾乎每月都到腫瘤醫院作一次抗癌志願者,以自己作為案例,勸導其他患者正視疾病、樹立信心、樂觀平和地生活。
2018年1月,國家衛生計生委釋出“進一步改善醫療服務行動計劃(2018-2020)”,對MDT協作組描述為:以病人為中心,推廣多學科診療模式。鼓勵有條件的醫療機構將多學科專業技術人員納入多學科診療團隊。
蔡建強第一時間把訊息發到工作群,畢新宇很快回復3個大拇指標識,“我們堅持這麼多年的MDT,終於有了國家層面的支援”。
MDT模式對團隊整體水平要求很高,要求各科彼此尊重、能夠合作。從現實層面上,在一些醫院推行也面臨困境。蔡建強無需面對這些困擾。
“腫瘤醫院科室沒有經濟指標考量,赫捷院長對績效要求一共四條:第一,科室核心競爭力,在國內業內所處位置;第二,團隊建設,擁有怎樣的師資力量,有哪些拿得出手的成果;第三,為醫院作多大貢獻,看科室獲獎率、醫護人員學術造詣、學術文章影響等;第四,跟去年同期比,經濟效益是否下滑,如果下滑太快,那一定治病效果不好。”蔡建強說,這些都非一日之功,治療水平高不高、患者多不多,平時就一目瞭然。
蔡建強說,MDT執行前10年,“為了挽救更多患者,沒有收過錢,甚至其他醫院500元會診費都沒有,會診都免費。”而病人一旦進入MDT體系,就會被終身隨診,得到持續而最優的診療方案。“13年了,病例庫裡還有十幾例MDT成立之初的病人,在不斷隨診。”
13年間,MDT逐漸形成數十位多學科骨幹協同作戰的醫療團隊,積累越來越多寶貴臨床經驗,年輕醫生在實戰中飛快成長,團隊現已擁有15個國家級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稱號、20餘個副主任委員稱號。
“當年支援我們的前輩們,現在都年過九旬,有的已經不在。我們這些當時還年輕的教授、副教授,科室主任、副主任,十幾年間迅速成長起來。MDT專家團隊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但理念從沒改變過。”
每週四,腫瘤醫院病理科、影像科、內科、放療科和外科醫生都有一次會診,透過討論為患者決定最為適合的治療方案。
大家經常會診前就在微信群裡開始討論,由於工作原因實在不能到場的會請假,認認真真說明原因。
“怎麼做才能讓患者得到最佳治療效果、最低損傷和最小刺激?”“如何在最好的集體免疫機能下進行治療?”“這一結論來自哪裡?”“國際最新文獻顯示,這樣的治療會大大提高患者生存期。”“樣本量是多少?病情是否和討論中的病人一樣?是否要考慮個體差異和腫瘤生物學行為?”類似對話,幾乎每次討論都會發生。
蔡建強說,“MDT團隊沒有職務高低之分,每個人都平等討論,由秘書彙總意見後,大家總結、分工。秘書由團隊成員輪流擔任,平等得很。”
MDT剛建立時,參加會診的人很少。現在,消化道腫瘤MDT討論不僅吸引許多本院醫生自發參加,不少外院醫生也習慣每週四下午到腫瘤醫院旁聽。
記得收治的所有患者,理解那些痛
少年時,蔡建強曾是一名求醫者。
1962年生於吉林,蔡建強兒時隨下放的父母在長白山農村生活。“這裡距離家鄉吉林市並不算遙遠,城鄉生活卻有天壤之別。雖然年紀很小,但已經能意識到周圍環境的巨大變化,而且因為政治上的因素,我們一家人生活比較困難。”
沒有隨性玩耍的童年,甚至沒有睡過一個懶覺,6歲的蔡建強學著擀餃子皮、劈柴,播種、收割、燒飯也慢慢不在話下。勞作在他胳膊上、手上留下道道傷疤,至今可見。
生活艱苦,農活繁重,蔡建強母親又體弱,不久患上關節炎、腎炎和嚴重的偏頭痛。“以當時處境,我媽媽找大夫看病很不容易。從那個時候起,我就有一個決心:將來要做一名大夫,治好媽媽的病。”
偏頭痛犯起來,整個人都受不了,家裡輾轉找到一位會針灸的女大夫幫著治療,可往來交通不便,蔡建強母親又很要強,不願意總麻煩人。
蔡建強又想自己學針灸,給母親治病。15歲的少年一邊學,一邊在自己身上試驗,大概一個多月後開始給母親針灸。“沒想到效果還挺好,大約半年左右,她的偏頭疼居然完全好了。”
作為患者的痛苦和無助、逆境中父母的堅強隱忍、醫者技藝和仁心對患者的幫助與撫慰……都成為蔡建強日後行醫處世的厚重底色。他理解那些痛。
從醫35年來,蔡建強做過5000多例腹部腫瘤手術,醫院統計顯示,沒出現一例嚴重術後併發症。查房時,為了查體不讓病人受涼,他習慣性地將雙手放在兩側腋下保持溫度。他記得自己收治的所有患者。
2004年,浙江溫州肝癌患者葉女士在腫瘤醫院接受手術,蔡建強主刀。現在葉女士已年過七旬,身體很好。今年,葉女士的愛人柯先生又在體檢中查到肝臟腫瘤,兒子毫不猶豫帶他來到北京,好不容易掛上了蔡建強的門診號,見到蔡建強一邊報喜一邊報憂。看過患者CT片和之前醫院寫的病歷,蔡建強對老先生說:“這兩天再做個核磁檢查,全面評估一下身體狀況,如果符合條件就做消融手術,很快就可以出院回家了。您和您愛人當年情況不一樣,她必須開刀。”
患者兒子忍不住驚叫:“16年了,您還記得我媽媽的病情!”
很多疑難患者是報著最後一絲希望找到蔡建強的,他也總是不遺餘力。當他成為肝膽外科主任醫師,尤其擔任腫瘤醫院副院長,逐漸成為業界知名專家時,曾有人勸他“為自己的聲譽留一條退路”,但蔡建強從不,“我行醫原則就是隻要對患者有益的事,我都會做也願意做”。
不僅如此,有些病人想要放棄時,他還要儘量鼓勵他們堅持一下,“生命寶貴,人總有可以活下去的理由”。
在腫瘤醫院工作35年間,除了醫術精益求精、不斷創新,蔡建強更強調醫德傳承。
1986年,進入腫瘤醫院第二年的蔡建強,到同屬中國醫學科學院的北京協和醫院輪轉一年,每天騎著腳踏車從東南二環龍潭湖跑到長安街北的協和醫院。
在協和,他上過病理生理學家陸士新院士的課,跟著分子腫瘤學專家吳旻院士、我國醫學放射物理學術帶頭人胡逸民查房,與中國消化病學奠基人張孝騫等名家會診討論……耳濡目染中,蔡建強感受到醫者的榮譽感、責任感,還有治病救人的幸福感。
“病人治療成功、做一臺完美的手術,幸福感自然而然由心而生。這些年來我在臨床中不斷用這樣的思路要求自己、約束自己,培養自己的工作作風。”
學術之外,老一輩協和人對待患者的溫厚誠懇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烙印。“患者在醫院裡問路,醫護人員不但停下來認真傾聽指路,有時還會直接護送到目的地,一路上耐心安撫,勸慰患者不要著急。”在急匆匆的當下,這樣的畫面已不多見。
蔡建強任住院醫時,導師餘宏迢要求他每天守床18個小時。早上不到7點進病房,夜裡十一二點回去,一邊在患者旁邊觀察術後反應,寫病歷,一邊等處理急診的機會。
“餘教授說,處理急診能力是對自己快速反應、判斷推理能力的最好鍛鍊,處理急診節奏之快,沒時間讓你出問題。”急診並非時時都有,患者病情也不會分分鐘起變化,大多數時間守床顯得枯燥漫長,但蔡建強不這麼想,“我整理病歷和資料,寫了很多手術記錄,畫了很多圖,積累了大量經驗,為以後做準備”。
做了三十多年臨床醫生,蔡建強至今特別看重那張病床。“臨床”還是“離床”,是他判斷一名臨床醫生合格與否的重要標準之一。“臨床,不在患者病床邊你怎麼知道情況?如何增加跟病人之間的溫度?”
他經常把學生或科裡年輕醫生從電腦旁邊叫起來,按到病人床前“守著”。曾有一位病人手術後,蔡建強要求一名醫生守床9個晝夜,每隔一小時發簡訊彙報一次病情。
“對病人關懷,不單純是人文層面,還有很多技術引數、醫療指標,當然還有醫療道德”。有些來自長期臨床實踐的絕活,蔡建強的學生們歎為觀止。
結直腸腫瘤患者手術後,會出現腸粘連,有時腸管轉彎處折得太緊,腸內容物在腸道中不能順利透過和執行,就會發生粘連性腸梗阻,嚴重者要進行二次手術。
一次,一位患者術後腸梗阻,大家都解決不了,面臨二次手術。蔡建強趕來,用聽診器聽了腸鳴音後,讓患者平躺在床上,用雙手給患者揉肚子,揉一會兒,再用聽診器聽聽,換個手法繼續揉,再聽,再揉……如此反覆,進行了一個多小時,患者腸梗阻完全緩解,蔡建強滿頭大汗。
“一般醫生都沒蔡院長的手法和耐心”,畢新宇坦言,“有時醫生揉十幾分鍾覺得枯燥,就把方法教給患者家屬讓他們繼續,但蔡院長一定親自揉,而且一邊揉一邊思考,不斷變換手法和位置,最終患者免於二次開刀受苦。這樣的病例在科裡可不少”。
有一名學生,因為患者病情需要而加班守床。幾天後,這個學生到醫院教育處諮詢加班補助事宜。蔡建強得知後大發雷霆,把學生叫過來只問兩句話:“書還要不要繼續讀?一點奉獻精神都沒有,醫德去哪了?”把利益作為醫者出發點,這是蔡建強絕不能容忍的,“作為醫生一點奉獻精神沒有,書還讀得有什麼意義”?蔡建強眉頭緊鎖,不停地搖頭。
他要求學生重溫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8月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對廣大衛生與健康工作精神概括的16字——“敬佑生命、救死扶傷、甘於奉獻、大愛無疆”,寫出對其中每一個詞的思想認識,作出書面檢查。
從1999年讀研究生算起,畢新宇已經跟蔡建強21年。縱然現在自己也已成為特需門診專家,逢蔡建強每週大查房時,畢新宇還是緊張不已。“他對治療總是精益求精,在臨床工作中總能發現我們沒發現的細節,而這個出其不意的細節,又總擊中要害。
比如有一個很小很小的細節,一位術後病人發燒,其實是腹腔有一處感染,我們也做了檢查,但查了半天也沒找到問題,後來蔡院長來查房,一下看到,說‘腹膜有問題,需要做個穿刺’。穿刺後果然解決了問題。”
講起蔡院長查房,畢新宇就忍不住緊張,手不停推眼鏡。“蔡院長每次查房,都是我們最緊張的時候。是真緊張。”
平日,蔡建強對同事、學生好得全心全意,大家有事都先想到他。逢年過節,他會感謝每位醫生家屬對醫院工作的支援。可如果有人在工作中出一點點對患者不利的問題,他就忍不住發怒。
畢新宇經歷過,只因為一個對整臺手術並無影響的不規範操作,他被蔡建強訓斥:“你有沒有想過這對患者有多大損害?!這不允許!”畢新宇回憶,那是發自內心的憤怒。
“不該逝去的生命就必須留住”
北京順義結腸癌患者劉平夫婦,十幾年間每隔一個多月就特意坐車進城,到腫瘤醫院蔡建強辦公室坐坐。直到幾年前,老兩口都年過七旬,蔡建強勸他們不論如何不要再辛苦奔波,這才勉強作罷。
2005年結腸癌手術以來,劉平的生命源於蔡建強22個晝夜的不間斷搶救。
當時,罹患結腸癌的劉平,在腫瘤醫院經多學科會診確定沒有其他部位轉移後,由外科先行手術。手術很順利,但術後第7天病人仍未排氣排便,這不正常。再次會診後,蔡建強為患者緊急實施造瘻手術。
術中,發現腸管牢牢黏在一起。歷時8小時的造瘻手術依然沒有讓腸梗阻緩解,又經過一次手術,這才發現元兇竟是患者腸管對手術手套上的滑石粉過敏。“這樣的病例很罕見,全國只發現6例,死亡率很高。”蔡建強說。
患者劉平有親友在國外,影像學資料透過網路發過去,得到的回覆是一片惋惜聲。滑石粉過敏導致腸粘連,當時國際上也不超過10例,沒有救治成功的記錄。
蔡建強不信,帶著幾位醫生守在病人旁邊。搶救室的燈24小時亮著,生命體徵監測儀不間斷地滴滴響著,不管白天黑夜,蔡建強每隔十幾分鍾、二十幾分鍾就進行一次操作,不斷刺激腸道,灌腸、貼劑、穴位按摩……其間進行三次手術,用盡辦法避免腸道麻痺,消化道功能衰竭。
第22天,劉平生命體徵平穩。
隨後放化療取得預期效果。之後,外科又領銜完成兩次手術,經多學科協作,劉平終於從死亡線上逃脫。
詩人約翰·多恩說:“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減少。”蔡建強有一個死命令:病人情況是否已經徹底無解?如果不是,那就絕對不能放棄。不管用什麼方法、手段,一定要搶救。
醫護人員要全面深入認知疾病,加強會診、不懂就問、彙集多方意見,在統一思想指導下,把握各個環節,全面付出。
“類似情況很多,有的不是我處理的,但我們科只要遇到這個問題,都拼到底。很多病人真是我們從死神手裡搶回來的。”
蔡建強極為看重醫學人文精神,又反對空談醫者仁心。“過去總說人文是我們自己能接受的善良,但我認為,所謂醫者仁心,是涵蓋整個醫療過程中的醫療準則,是一種實踐;是要把醫者該做的事做好,把責任、技術和溫度結合在一起。在醫療執行過程中準確執行醫療思想,想盡辦法幫助患者提升戰勝疾病的能力和心態。”
畢新宇牢牢記著蔡建強的一句話:“都說醫生是天使,你要記得天使是長著一對翅膀的,一隻代表醫德,一隻代表醫術,少一個都不是天使。”
患者小健是19歲的大一新生。2015年,他患有母系傳播的乙肝病毒導致的肝癌,且病情已到晚期,右肝巨大腫物13釐米。
當小健的病例出現在MDT系統裡時,蔡建強知道,“會診室內外的人,從他身上看到的東西不一樣。我們討論的是當下和未來,是如何留住生命;屋外親人想到的是過往,是孩子叫出第一聲爸媽,他掉下第一顆乳牙……”所有美好的回憶因為當下的痛苦而倍加沉重,也讓拼命挽留這份美好的努力格外值得期待。
討論後,MDT團隊醫生決定先為小健實施右半肝切除術。但他們也擔心,畢竟是晚期,即使手術順利,病人也會因可能的腫瘤復發轉移到多臟器而生機渺茫。
歷時4個多小時手術後,大家鬆一口氣。畢新宇還記得,“雖然有轉移風險,但完整切除了腫瘤,同時清掃了區域淋巴結,加上預防轉移復發的治療手段,相信他會有較長時間的生存”。
然而,小健術後三個月,他母親也被查出患有肝癌,面對術後巨大的後續治療費用缺口,一家陷入經濟深淵。
治療組減免了他們一些費用,仍是杯水車薪。在這種情況下,MDT全體成員發出“為年輕的生命募捐”倡議,不到一週募捐7萬多元。
最後一次複查,小健給團隊醫生帶來一張自己在校園拍的照片,白襯衫、淡藍色牛仔褲,那麼蓬勃。蔡建強記得,小健說他已無遺憾,只是無法回報。
與病人一起度過艱難時刻,甚至最後時刻,醫生難免動情。但不論怎樣,總有些事情醫生、患者及家屬必須直面。蔡建強從不迴避病程,不論多沉重,他都會如實告知患者或家屬。
蔡建強所在的肝膽外科,患者百分之七八十從外地來,他理解患者和家屬的不容易。“我們看到這些病人也很沉重,但再沉重,也要把病情程度講清楚,絕不誘導,也不過度。
治療有時是積極的,有時是放緩的,有時是放棄的……醫療盡頭,我們要經常給緩和醫療患者指導和安撫,儘可能在提高生存質量前提下,讓患者病情發展再慢一些,痛苦再小一些,精神狀況再強一些,對生活感受再深一些,給生命以最後尊嚴。”
安靜時,蔡建強時常想起他送走的患者。他們有的平靜離開,有的經過激烈搶救;有的走時安詳,有的則帶著諸多遺憾……奮力拉回他們的經過和他們最後時刻的樣子,都一一清晰地印刻在他心裡。
蔡建強把死亡分為三種——自然死亡、科學死亡和醫療死亡。自然死亡是生老病死,科學死亡是用盡醫學技術和治療手段仍舊無力迴天。醫療死亡則往往出於醫生認知或醫術侷限而導致,這是蔡建強無法接受的,也是極力要求醫護人員提高技藝去避免的。
他不講客觀理由,只要求不該逝去的生命就必須留住,這總是督促著他奮力前行。“每個外科醫生心中一定有一座墓園,這座墓園是需要時常祭掃的,這樣才能源源不斷有加強責任心、精進醫術、提升治療水平的動力。”(本文刊於《中華兒女》雜誌2020年第14期)
來源:光明日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