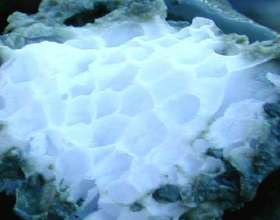過去幾年裡,丁一舟與賴敏的故事被媒體不約而同地包裝為一種“感動中國”式愛情敘事:
「一個叫賴敏的年輕女孩,身患絕症,身體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衰弱下去,戀愛多年的男友離開了她。此時,小學同桌丁一舟挺身而出,兩人重逢相愛,當賴敏的生命進入倒計時,他們帶著輪椅、寵物和全身僅剩的200元環遊全國。」
他們的故事被不斷報道、拍攝為影視劇、紀錄片,倆人甚至登上央視《朗讀者》舞臺。故事裡的“丁一舟”,多年來對身患絕症的女友不離不棄,獨自擔起照顧伴侶的重任,成為好男友好丈夫的“標杆”。
通常到了這裡,故事已經結束,但當我聯絡上丁一舟,他告訴我,他算不上報道里的“好男人”,他們的愛情故事裡沒有英雄也沒有惡人。只是兩個不甘於平靜的年輕人相愛了,與疾病無關。
像剝開洋蔥那樣,一層層剝開這個被包裝過的故事外殼,他們的感情依然動人。
與死亡纏繞共生的男女
如果不是懷孕和突如其來的疫情,賴敏想過“安樂死”。
“安樂死”,是讓臨近死亡的重度疾病患者,可以相對無痛苦死亡的一種方式,目前在荷蘭、比利時等部分歐洲國家及地區合法。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激起過廣泛的社會討論,支持者認為病人有資格選擇體面的死亡方式,反對者則認為“安樂死”有悖生存權利。
賴敏沒有想那麼多,第一次產生這種想法,是她與時任男友、如今的丈夫丁一舟環遊中國期間,他們原本想從新疆穿過中東去歐洲,如果條件足夠,賴敏打算在歐洲完成“安樂死”。
賴敏的意外懷孕擱置了這個計劃。那是2017年,當時她坐在輪椅上,勉強還能站起來。
4年後,賴敏的萎縮情況更嚴重了,她只能躺在床上,無法起身。育兒與生活瑣事由丈夫丁一舟完成,在這個家裡,丁一舟將妻子的角色定位為“家裡的精神支柱”,其他工作都歸自己。
21歲那年,賴敏確診了一種罕見病——“遺傳性脊髓小腦共濟失調”,俗稱企鵝病。患者行走時像企鵝那樣搖晃,身體也會逐漸萎縮,神經細胞變性直至死亡。企鵝病的發病機率約為十萬分之三,遺傳機率高達50%,以目前的醫療水準無法根治。賴敏的母親患有企鵝病,51歲離開人世。
《朗讀者》節目組敏感地抓住了這個故事,這期節目也成為《朗讀者》開播以來最令人難忘的一期。
這對情侶對待死亡的態度打動了不少陌生網友,他們身上沒有重症患者及家屬常見的苦難感,臨近死亡前,以豁達灑脫的態度環遊中國。
節目播出後,人們的目光對準這對患難情侶,無數媒體探究他們的旅行細節,來自天南海北的觀眾第一次意識到,生命的終點,不止眼前生活的地方。
然而,隨著聚焦在他們身上的目光增多,故事卻被添加了更多戲劇性標籤,逐漸演變為:一個命運悲苦的女人,在行至絕境處遇上有情義的男人,成了“感動中國”式感人愛情,男主人公丁一舟被奉為“中國好男友”。
“感動中國”式故事的背後,丁一舟的故事有另一個版本。
那些被不斷重複書寫的經歷是真實的,但也有很多被刻意遺漏的細節:
他不認為自己和報道里的“好男人”沾邊,和賴敏重遇前,丁一舟處在迷茫階段,經歷過輟學、叛逆、流浪,比同齡人更早進入社會,與2、30位女性發生過性關係;
起初他只是帶著同情,打算將境況不佳的老同學賴敏送到每月收費一兩千元的療養院;
丁一舟還提到了故事裡的另一個角色——拋棄賴敏的“渣男”前任,事實與媒體敘述的形象迥然不同,賴敏與前男友18歲相戀,戀愛7年,這意味著女孩確診病症後,他們共同度過了4年。
前男友家人強烈反對下,他們才選擇分手。丁一舟為那位素未謀面的前男友解釋,“我不覺得(賴敏)前男友屬於拋棄行為,網路報道總說賴敏被拋棄,我心想至於嗎?”
丁一舟以近乎祛魅的形式重新講述了這個故事,提出假設,如果當初賴敏真的因為這份同情而依賴上他,他或許早就對她產生反感。
但賴敏沒有,她從不把自己當病人,愛笑愛撒嬌,哪怕病情惡化,也會嘗試各種方式養活自己,賴敏的簡單與生命力吸引了丁一舟,“跟一個人過日子,是跟她的人過,不是她的病過,不能說把人丟一邊,只看(關注)她的病。”
兩顆孤獨的心
丁一舟將他與賴敏的感情歸為極高的精神契合,精神契合具體指什麼,丁一舟說不上來,但他有種預感,如果伴侶不是賴敏而是別人,自己一定做不了那麼多。
外界普遍認為,和重症患者在一起,照料方需要消解更多現實生活的壓力,丁一舟否認了這一點,“精神也好,生活也好,我們相互需要。”他說,如果賴敏找到一個好護工,完全可以獨自生活,“我們分開都能過,但是沒有理由讓我們分開。”
2014年,丁一舟和賴敏27歲,賴敏與前一任男友分手2年,獨自在廣西南寧租房生活,屬於企鵝病早期階段,心態樂觀,偶爾也擔憂母親的結局在自己身上重演,某天,她在QQ空間留下一句話,“忽然有一種心被抽空的感覺,如果有一天我死去了……”
丁一舟偶然間看到了這句話,賴敏是他的小學同桌,他印象裡,賴敏是個開朗的女孩,不明白她為什麼說出如此沮喪的話,因為“很好奇”,重新聯絡上賴敏。
隔著螢幕,賴敏簡要介紹了自己的現狀,大約一週的時間,他們一直在聊關於企鵝病即“小腦共濟失調”的症狀、病因、治癒可能性。賴敏說過,丁一舟是第一個因為她特意搜尋病症的朋友。更令她意外的是,一週後,丁一舟告訴她,自己要來南寧看她。
那一年,丁一舟在柳州做理髮師,生意紅火,月薪到手一兩萬,原本有個談婚論嫁的女朋友,婚房已經買了,後來談崩了,抱著“遊戲人間”的想法,下班後穿梭在一家又一家酒吧裡。
為什麼要去南寧看賴敏,丁一舟是想看看老同學現狀如何。時隔16年,丁一舟看到的賴敏,住一個月八百塊的簡陋出租房,父母去世,走路有些不穩,還佯裝一切如常。
此前有報道稱丁一舟從小默默暗戀著賴敏,才會在女孩境遇不佳時挺身而出,當我丟擲這個細節,電話那頭傳來丁一舟的笑聲,“小學時的好感怎麼可能維持20年?”他稱那時想法簡單,自己過得還不錯,能幫一把就幫一把,“不認識也就算了,但我認識她。”
他建議賴敏回柳州,“你在南寧也是租房,我有房子可以租給你,還可以幫你找工作,比你現在的情況強。”
沒等賴敏決定,再去南寧時,丁一舟僱了一輛車,將賴敏和行李寵物一起打包回家,住他家隔壁房間。
那是間三居室,原本丁一舟為結婚而買,婚沒結成,丁一舟獨自住在新房裡,那時他和賴敏還是朋友關係,隔著一層窗戶紙,誰也沒捅破,賴敏在專欄“幸福在路上”寫道:“也許是因為我的病,我們之間有一種莫名的隔閡存在。”
時間沖淡了隔閡感,丁一舟上班早出晚歸,賴敏在家負責做飯和打掃衛生,晚上一起散步遛狗,有時賴敏的鞋帶散了,丁一舟下意識會蹲下來繫好。
起初幫助賴敏或許出自同情,時間長了,丁一舟的想法發生了微妙變化,賴敏沒依賴他照顧,反倒自己買菜做飯,為人單純樂觀,“我的性格特別野……她是那種堅強和溫柔並存的人,什麼都柔軟,連堅強也是柔軟的。”
丁一舟剛經歷一段失敗的感情,明白自己就想找這種想法簡單的伴侶。
一個喝醉酒的聚會夜晚,兩人睡在一起,自此確立了關係。
丁一舟的母親反對他們的關係,罵兒子神經病,“沒事招惹一個有病的女人幹嘛?”丁母反對了大半年,最嚴重的時候提出要和兒子分家,好在丁一舟經濟獨立,沒有動搖。
他理解母親的行為,為人父母很難接受自己的孩子和病人在一起,丁一舟口中,母親也是位堅強獨立的女性,和丈夫離婚後,將兒子拉扯養大,“她是那種可以把柔軟也變得強硬的人”,母親和賴敏生日只差一天,讓丁一舟覺得很巧合,“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女人,生日相近,但是性格相反。”
母子拉鋸半年,直到丁一舟和賴敏的故事被不斷報道,鄰居好友都向丁母誇讚她有個好兒子,丁母的態度才稍微鬆懈一些。
丁母根本性的態度轉變發生在2015年春天。春末夏初的雲南,兩個同樣堅強的女性在麗江聊了一整夜,丁一舟至今不清楚她們究竟聊了什麼,只知道那次之後,母親對賴敏改觀了不少。沒有再反對他們的關係,還讓兒子好好照顧賴敏。
兩人,一狗,一輪椅,200元
丁母對他們的關係有所改觀,賴敏的病卻沒有絲毫起色。兩人確立關係之初,賴敏可以獨自切菜、炒菜、逛超市,日復一日,她連行走都變得困難。
丁一舟想過帶她看病。最初,丁一舟對“企鵝病”的認知沒那麼全面,認為治病就要送醫院,“去總比不去好,她去治一下,我又不是給不起這個錢”,他當時有近30萬存款,經過一段時間治療,丁一舟發現他真的“給不起”。
治療費用一個月上萬,吃一種叫他汀瑞林的進口藥,一盒八千多,只能為企鵝病初期患者延緩病情,無法起到控制作用。為了照顧賴敏,承擔高昂治療費用,丁一舟換了份時間更自由的工作,把三居室租出去,和賴敏住到農村。
比負擔不起高昂的治療費用更令人沮喪的是,當他們聯絡上更多“企鵝病”病友和家屬,患病多年的老人直接告訴丁一舟,“不要治了,這個病治不好”。
這期間,丁一舟還做過一個錯誤決定,讓兩人處境雪上加霜,他抱著賭一把的心態,花了存款的三分之二投資貴金屬,結果重金屬爆倉,他嚐到了一無所有的滋味。
丁一舟投資失敗,賴敏病情不見起色,兩人的經濟狀況臨近崩潰,做出“環遊中國”的決定與賴敏的病情有關,也與丁一舟當時的處境相關。
一個傍晚,丁一舟下班回來,他們在住所周邊散步,看著天邊的赤紅色晚霞,賴敏感嘆,如果每天都能看到這樣美的景色就好了。
丁一舟說,“我們幹嘛每天看一樣的,看不一樣的不行嗎?”賴敏提議,要不出去走一走?兩人一拍即合。
在別人看來,帶重症患者全國旅行是個非常理想化、難以實現的計劃,沒有人相信他們真能成行,丁一舟沒當回事,他叛逆時期也流浪過,睡過橋底,被傳銷騙過,“我們只是覺得換一種生活可能會更好,所以我們就換了一種生活。”
2015年1月1日,丁一舟和賴敏正式出發,兩個人,一條狗,一個輪椅,還有僅剩的200元錢,賴敏坐在輪椅上,丁一舟弄了輛腳踏車在前面斜拉著,另一邊拴著他們養的狗,行李捆在輪椅後面,保持相對平衡的狀態。
有些文章將他們決定旅行的過程形容得浪漫又倉促,文章裡的故事與他們的實際情況截然不同,稱丁一舟在兩人出發前,提前計劃要在中國地圖走出“心形”,出發時全身僅帶200元。
實際上,丁一舟為這趟旅程籌備了整整三個月,準備好輪椅改裝、帳篷、狗糧、油鹽柴米等生活物品,也做好了邊旅行邊打工的準備。
最初的籌劃裡,他們壓根沒想過走“心形”路線,出發一兩個月後,丁一舟看了眼導航,才發現,“這個地圖示記到那個地圖示記,連起來不就是一個桃心嗎?”
兩人去過雲南、西藏、新疆、內蒙,環繞大半中國疆域,餓了起鍋生火,困了支起帳篷睡覺,天氣寒冷時多加幾層被子,酷暑炎熱時把帳篷拉開一條縫透氣。
後來,一位好心的旅客默默為他們資助了一輛三輪車,這趟旅行稍微方便了一些。
一路上,丁一舟和賴敏見過很多從前沒見過的美景,雄偉壯闊的秦嶺,一望無際的白鹿原,隱居聖地終南山,中國四大無人區,他們去了三個,在無人區搭帳篷,背後整個雪山都成了“家裡的後院”。
回憶起那幾年的旅行,丁一舟和賴敏都選擇講述美好一面,至於困難之處,“肯定有困難,但都在預料之中”,他向我分享旅途中的危急時刻,三輪車被衝下山去,路途前面碰到野牛……這些聽來驚心動魄的瞬間,丁一舟語氣雲淡風輕。
隨著丁一舟賴敏的故事被廣泛傳播,更多驢友加入了他們的行走,有驢友將他們的故事拍成紀錄片《幸福在路上》上傳到網際網路,其中一集裡,賴敏對著鏡頭笑著說,“這一路,我們遇到的人心比風景永遠美得多。”
丁一舟和賴敏原本只是想出去走走,換種生活方式,旅途中卻收到一些意料之外的“來自陌生人的善意”。
那輛被衝下山的三輪車,被好心的村民用卡車拉了上來;得知他們想要舉辦藏式婚禮,當地康巴藏人出動全村,為他們舉辦了一場藏式婚禮。
他們一路拒絕資助,沒錢的時候,丁一舟原地支起小攤剪髮,標價10元,還有人給他硬塞了800塊,“就當是我這輩子剪過最貴的頭髮吧,你們路上用錢的地方還有很多。”
行走,停下
2015年到2018年,丁一舟賴敏陸陸續續走了三年,去過這麼多地方,他們得到的最大收穫是“人可以不用按一種方式活著。”
“很多人都被目前的生活束縛住了,因為沒有接觸外面的世界,不知道別人如何生活,沒有對比,所以只能這樣生活下去……要走出去,到不同的地方收穫不同資訊,這些資訊充實起來,面對同一個問題,會有不同方式看待。
如果不是賴敏懷孕,他們或許會走得更遠。
賴敏的第一次懷孕是個意外,丁一舟原本不想要孩子,“遺傳性小腦共濟失調”的遺傳率高達50%。
但得知懷孕的賴敏很興奮,為孩子取名“丁路遙”,寓意為這一路路途遙遠,人生的路也很遙遠。
懷孕期間,賴敏給未出世的孩子寫了18封信,從1歲寫到18歲,丁一舟賴敏在《朗讀者》的舞臺上分享喜悅和擔憂,那時,他們還在等待檢測結果,北京有家醫院免除檢測費用,排查孩子是否帶有遺傳致病基因。
他們在北京的出租屋裡等了3個月,丁一舟接到電話,賴敏腹中的胎兒帶有遺傳致病基因,發病率99%,他愣住了,發呆了一陣,告訴賴敏這個訊息。
兩人為孩子的去留而爭辯,賴敏不願意引產,認為“即使孩子有病,也該有生的權利”,丁一舟不同意,“你能保證遇到下一個丁一舟?誰能來照顧ta一輩子?”
最終賴敏同意引產,為了紀念這個沒能出生的這個孩子,他們把自己故事的版權賣給影視公司,用版權費用得來的50萬,在理塘開了間客棧,取名“路遙星空”,理塘是他們舉辦藏式婚禮的地方,理塘涵蓋了西藏所有地貌,有高原、雪山、草原,還有很多牧場,“我們喜歡這個地方,還會有種在路上的感覺。”
丁一舟和賴敏開的這間“路遙星空“是整個理塘佔地最大、房間數最小的客棧,距離縣城三公里,他們養了不少的動物,也嘗試著用寫書、拍短影片等其他渠道養活自己。
賴敏還是渴望有一個孩子,2019年末,她再次懷孕,丁一舟告訴我,這個孩子是妻子扎破安全套才懷上的,他沒問過賴敏為什麼這麼做,“她沒有說我也不想問“,丁一舟猜測,或許妻子擔心哪天自己離開後,他會自暴自棄。
他們又一次做了基因篩查,幸運的是,這個孩子沒有攜帶遺傳致病基因,賴敏為孩子取名“安寧”,新手媽媽在日記裡留下樸素願望,“希望她以後的日子平安順遂,心能夠寧靜致遠。”
整個孕期,賴敏比普通母親更難熬,感冒時一口痰出不來,都會把自己憋暈過去。剖腹產期間,麻藥過了勁,她不停口吐白沫,直到醫生用了吸痰的機器,才緩過來。
經過驚險的生產過程,“安寧“來到這個世上,是個眼睛大而圓的女孩,臉頰鼓鼓的,很健康。安寧出生後,賴敏躺在床上無法起身,那是丁一舟最忙的時候,要經營客棧,還得照顧妻子與剛出生的嬰兒。
他同步在籌劃一個聽上去不可思議的計劃,全資拍一部電影,真實、完整地記錄下他和賴敏的故事。
為了實現這個計劃,丁一舟和賴敏嘗試接觸從前“看不上“的綜藝、直播帶貨,一小部分聲音質疑他們在“作秀”,兩人不在意,如果未來這部電影真的上映,有很多人看,“或許有觀眾覺得這(安寧)是男女主人公的女兒,會對她友善一點。”
丁一舟拿不準計劃是否能成行,他將自己和賴敏的另一個共同點歸結為“喜歡折騰,不甘於平靜”。
目前丁一舟和賴敏在客棧裡種滿花,養了幾頭牛,過著一種看似平靜的生活,私下裡,賴敏告訴他,自己不想死在醫院,“要死在路上”。
兩人悄悄約好,等經濟狀況改善些,他們會關掉客棧,再去“野”一趟。
END
“企鵝病”發病後,存活時間為10-20年,賴敏如今已經確診十多年,對丁一舟而言,妻子會在未來的某一天去世,是必將到來且不可逆轉的結局。
兩人偶爾還會爭吵,頻率很低,有時吵後,丁一舟會想到賴敏在《朗讀者》裡讀的散文——三毛寫的《你是我不及的夢》。
三毛是賴敏很喜歡的作家,這個故事裡,荷西失業後買了捧百合花,三毛為他在經濟窘迫時亂花錢而憤怒。四年後,荷西去世,三毛一口氣買了幾百朵百合花放在房間,愛人卻永遠地離開了。
有空時,丁一舟會和妻子談論死亡,賴敏笑著調侃他,讓他學一學妻子死後“鼓盆而歌”的莊子,敲鑼打鼓慶祝解脫,丁一舟同樣嬉笑,讓賴敏放心,如果她不在了,自己會“拿著遺產包小三”,該吃吃該喝喝。
兩人以玩笑的語氣,消解了死亡帶來的嚴肅感。
這次採訪的尾聲,我忍不住再次丟擲那個問題,“如果有一天賴敏真的走了,你會怎樣生活?”
丁一舟這次收起了玩笑語氣,“把孩子拉扯大,我再出去流浪。”
“有目的地嗎?”
“走到哪算哪,鬼知道目的地在哪,人生就不該有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