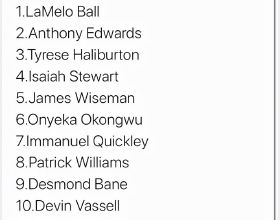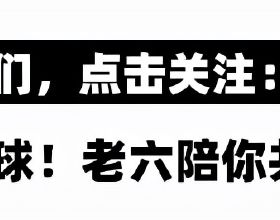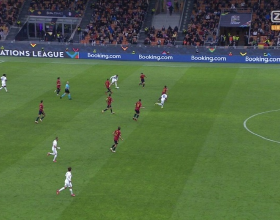滅絕的警示燈,近年一直環繞著中華鱘。2017年至今,我國已連續4年未監測到“水中大熊貓”的自然繁殖。
中華鱘已經在地球上生活了1.5億年。20世紀70年代,長江中華鱘有近一萬尾,80年代減少到2000尾左右,90年代只剩下200-300尾。
“拯救”它們的方法是人工繁育。同樣的手段已在大熊貓身上取得了成果——隨著人工繁育大熊貓數量的快速優質增長,大熊貓受威脅程度等級從“瀕危”降為“易危”,實現野外放歸併成功融入野生種群。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五次會議(COP15)上,我國公佈了首批五個國家公園名單。位列其中的“大熊貓國家公園”整合了多個自然保護區,將為大熊貓提供更大尺度的生態系統。
清華大學國家公園研究院院長楊銳表示,生物多樣性包含三個層面——基因、物種和生態系統。國家公園是對生態系統的保護,而不是對單一物種的保護;但生態系統保護好了,野生珍稀瀕危物種也會得到保護。
“國家公園”提出的背後,是瀕危物種保護理唸的新拓展。在專家看來,第一批國家公園的釋出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但並不是終點。

2020年11月,大熊貓國家公園管理局釋出訊息稱,雅安蜂桶寨片區工作人員在整理紅外相機資料時,發現野生大熊貓母子同框活動的珍貴畫面。圖/IC photo
從常見到瀕危:滅絕是一個過程
我國瀕危物種保護歷程,可追溯至40年前。
1973年3月3日,80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一次會議上,商定出《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的文字,旨在透過對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及其製品的國際貿易實施控制和管理,促進各國保護和合理利用瀕危野生動植物資源。
中國於1981年1月加入《公約》,同年4月8日,《公約》對中國生效。次年,相關條款寫入了《憲法》中。
回顧我國的瀕危物種保護工作,透過開展瀕危物種保護進行綠色扶貧的質蘭基金會秘書長張穎溢認為,它與我國1970至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與發展基本同步。
1984年前後,已經在我國野外滅絕的麋鹿從英國重回故土。對外贈送或租借大熊貓、朱䴉、金絲猴,將國外圈養的麋鹿和野馬引回國內等措施,直接推動了我國與發達國家野外調查、棲息地保護、繁育拯救等方面的合作。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我國建立起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並在全國設定14個野生動物救助繁育中心和400多處珍稀植物種質種源基地。
滅絕是一個過程。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高階工程師曾巖表示,“物種不是突然滅絕的,而是組成它的種群一個接一個地消失。種群滅絕是生物多樣性資本損失最敏感的指標之一,卻被很多人忽視。”
在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曾巖提到,瀕危物種的保護正規化目前主要有兩個,一個針對衰退種群,另一個針對稀有物種小種群。針對衰退種群的保護工作,可以在消除威脅因素後恢復種群。然而,小種群面臨的滅絕威脅往往是隨機災害,通常難以預測,只有針對性的保護行動才有助於避免其滅絕。
以中華鱘為例,長江水產研究所首席科學家危起偉認為,河道沖刷、航道疏浚與挖沙、防洪及城市景觀工程等人類活動使中華鱘仔稚魚棲息地喪失,進而導致補充群體減少,造成繁殖群體持續萎縮。拯救中華鱘,要恢復人工群體的生物學自然特性,大幅度提升科學有效的人工增值放流,改善產卵場環境,恢復其自然繁殖,從而延續和恢復中華鱘的自然種群。
COP15召開期間,在長江生物多樣性科普展上,一幅由危起偉製作的長江魚類分佈卷軸圖展示了不少珍稀物種的生存狀況。危起偉介紹,水生生物面臨著比陸生生物更大的威脅,長江白鱀豚、白鱘、鰣魚等從長江消失之後,許多物種也危在旦夕。
“相較於極小種群的動物保護,植物保護其實存在一定的優勢。因為動物保護的條件相對更為嚴苛。”國家林草局珍稀瀕特森林植物保護和繁育、雲南省森林植物培育與開發利用聯合重點實驗室主任楊文忠說,植物可採取嫁接、扦插、壓條、分株等無性繁殖手段,但動物的人工干預就十分有限,一些種群甚至在人工干預後也無法保證延續。
保護的關鍵,是讓它們繁殖下去
楊文忠的電腦裡存著一種植物的資料圖,這是一種當地特有的果子,名叫富民枳。它的原生地只有滇中高原富民縣老青山周邊海拔2100米至2400米的區域。當地人常將富民枳的果子切片晾乾,做泡飲或煮湯,有生津止渴的作用,因此不少農家將山間縫隙的富民枳移至家中種植。
2003年和2018年,楊文忠兩次帶隊負責全國極小種群野生植物調查,均未發現野生富民枳的痕跡,“當時我們提議,宣佈富民枳在原生地已野外滅絕。”《雲南省極小種群物種拯救保護規劃綱要(2010-2020年)》等檔案中,富民枳被列為優先拯救保護的“極小種群野生植物”。
楊文忠說,研究人員曾在農戶家中發現了8株“圈養”的富民枳。僅有的幾棵富民枳成為育種的唯一來源。科研人員小心翼翼,生怕種植失敗,每次移植還要有意識控制數量。如今,技術人員應用種子繁殖、扦插繁殖等技術研究,培育富民枳容器苗20000餘株,種子繁育成活率可達90%,扦插成活率達50%,嫁接成活率70%以上。
人工繁育是挽救眾多瀕危物種的有效手段之一。
在青海,祁洪芳已經用了28年守護一個瀕危物種——青海湖裸鯉。人工繁育成為保護青海湖裸鯉的關鍵。
“青海湖裸鯉資源的原始蘊藏量約32萬噸。隨著捕撈強度的增加和生態環境的惡化,上世紀90年代末,資源量已不足3000噸。”祁洪芳是青海湖裸鯉救護中心實驗室主任,她介紹,進入新世紀後,青海省政府對青海湖實施了零捕撈的封湖育魚政策,並開展人工增殖活動和過魚通道建設,青海湖裸鯉資源量由2002年的2600噸增加到2020年的10.04萬噸。
在瀕危物種的保護方面,祁洪芳認為,在建立保護區的同時,要加強保護區棲息地的生態監測,運用人工措施開展人工繁育,加快物種恢復程序。
同樣,植物育種繁殖也有自己的難題。一顆種子想要萌發生長,還可能遭遇“自毒作用”和“環境篩”兩個效應的歷練。
楊文忠說,“自毒”是植物防止結出的種子侵佔植物本體有限的生存空間,自我篩掉一批種子;“環境篩”則是萌芽後的植株難以承受環境風險,成長過程中被環境自動篩選掉。這也使本就稀有的極小種群野生植物繁衍變得更加困難。
以雲南藍果樹為例,被發現時全國僅剩8株、兩個種群。楊文忠及同事建立240平方米的種苗繁育基地,完成有性和無性種苗繁育技術研究,成功培育雲南藍果樹苗木3000株以上。
為瀕危物種留活路
除了人工繁育外,就地保護、遷地保護、近地保護、建立保護區等保護措施,也為保護瀕危物種提供了更多可能。
農業農村部資料顯示,至今,我國已建立5個長江江豚遷地保護地,遷地群體總量超過150頭。“遷地保護是目前長江江豚最有效可行的保護方式,無論是管理部門還是學術界,都在這個理念上達成共識。”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張先鋒說。
從相對不易控制的自然環境,遷移到可以管控的半自然環境,透過改善“吃住條件”,讓瀕危物種休養生息。張先鋒認為,遷地保護區中江豚數量穩中有升,證明了遷地保護的作用。
近年來,我國先後建立了一批具有遷地保護性質的保護區和保護溼地。比如湖北長江天鵝洲白鱀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湖北洪湖老灣故道、安徽安慶西江等多個江豚遷地保護區和保護場。
今年春季,農業農村部組織實施了最大規模的遷地保護行動,共從天鵝洲故道向7個遷入點輸出長江江豚19頭。“隨著遷地保護區江豚數量的增加,我們也要考慮做好種群管理計劃,避免近親繁殖產生種群衰退,需要把各保護區的江豚進行個體交換。”張先鋒說。
隨著長江十年禁捕的開展,漁業資源得到有效恢復,但航運、挖沙、水利設施等影響江豚生存的因素依舊存在。張先鋒坦言,希望若干年後,遷地保護的長江江豚達到一定數量,長江干流的自然環境得到改善,再讓江豚回到長江的自然環境中。
2021年10月8日,長江江豚在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壩下游大江水域逐浪嬉戲。圖/IC photo
除了江豚,棲息於青海湖周邊地區的中華對角羚也面臨困境。上世紀初,中華對角羚曾廣泛分佈於內蒙古、青海、寧夏和甘肅等地區。隨著生態環境的惡化和人為因素,這一珍稀物種一度僅存200餘隻。
今年4月,青海湖國家級自然保護管理局公佈了2021年度的監測結果,共監測到中華對角羚2560餘隻,種群數量14年間增長約9倍。
“現在,我們在315國道上就可以看到它們的身影。政府曾劃出5000畝草場建設中華對角羚保護救治中心,因湖水上漲,保護中心從青海湖鳥島遷到了青海湖南側,現在這裡有70餘隻對角羚。”青海省攝影家協會副主席葛玉修說。
長期以來,牧民家養的羊與對角羚爭奪草場和水源,密佈草原的網圍欄等設施也破壞著對角羚的生存空間。
“我曾親眼目睹老幼對角羚因跨越不過網圍欄而無奈徘徊的場景,也見過不少掛死在網圍欄上的對角羚。”葛玉修曾建議,採取補償機制,動員牧民降低網圍欄的高度,去掉頂部刺絲。
如今,網圍欄由過去的1.5米降至1.2米左右,這讓中華對角羚基本適應。此外,青海已建立2箇中華對角羚特護區、7箇中華對角羚飲水池,解決對角羚冬季飲水問題。
瀕危植物的保護也一樣。楊文忠表示,植物保護的探索是這樣一個邏輯:就地保護體系,最大程度保護野外種群;遷地保護體系,奠定種群恢復基礎;近地保護體系,快速儲存擴大種群數量;最終探索迴歸野外,實現種群恢復重建。
國家公園設立,“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10月12日,在COP15大會上,我國首批五個國家公園名單公佈。北京林業大學生態與自然保護學院教授雷光春表示,國家公園的建設考慮了動物對生態系統的需求,包括動物在不同階段對棲息地和遷徙通道的需求。
目前,野生動物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棲息地片段化,國家公園強調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原真性保護,使棲息地片段化的問題得到有效破解。比如,大熊貓國家公園把很多大熊貓自然保護區整合在一起,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大熊貓種群交流限制的問題。
雷光春稱,此次第一批國家公園的釋出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此次首批5個公園都是山地生態系統,將來對溼地生態系統、海洋生態系統在佈局上需要重點考慮”。他解釋,溼地系統可以保護鶴類、珍稀魚類、水生生物等。
中國未來還有哪些區域有潛力建國家公園?雷光春認為,國家林草局在前期做了比較系統的分析,在全國一萬多個保護地中,根據生態系統的代表性和空間佈局,優選了約60個,目前還在進一步醞釀之中。
清華大學國家公園研究院院長楊銳表示,生物多樣性包含三個層面——基因、物種和生態系統。就國家公園本身來講,它實際上是對大尺度的生態系統的保護,而不是對單一物種的保護,不過生態系統保護好了,野生珍稀瀕危物種也會得到保護。“東北虎豹國家公園、大熊貓國家公園雖然是以這一個物種的名稱來命名,但仍然是對東北虎、豹和大熊貓棲息地和它們所在的生態系統的保護。”
另外,他建議國家公園全面提升治理能力,設立“園警”制度。“國家公園面積很大,比如三江源國家公園接近20萬平方公里,公園裡面需要綜合執法。”他說,國外的“園警”有綜合執法權,部分“園警”學歷較高,甚至有生物學、生態學的博士,他們可以一邊執法,一邊進行自然教育。
“我認為,第一批國家公園正式設立,是‘萬里長征’走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如何走出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公園治理的道路”。楊銳說,中國人口多、密度大,國家公園也都在老少邊窮地區,一定要在生態保護第一的前提下,探討人和自然和諧共生的治理模式,把生態保護和社群的生計結合起來,形成良性互動的方式。
成效之後:需用科學的手段尊重自然
2000年以來,中國實施了15個野生動植物重點拯救專案,包括大熊貓、朱䴉、老虎、金絲猴、揚子鱷等。目前,全國共建立各類自然保護地近萬處,約佔陸域國土面積的18%。90%的陸地生態系統型別,65%的高等植物群落和71%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種類得到有效保護。
“我們現在的保護不僅是防盜獵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強對棲息地的保護。”中國人與生物圈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周海翔認為,用科學的手段尊重自然,或許是保護瀕危物種的最好方式。
認識自然是基礎,但目前人類對於自然的認識還存在一定偏差。周海翔舉例,鄱陽湖是中國最大淡水湖和重要溼地,也是東亞-澳大利亞西候鳥遷徙路線上的越冬地和停歇地。每年的秋冬季,鄱陽湖都會進入枯水期,但實際上,鄱陽湖還會存在週期性更長的枯水期。
“我們不能一遇到週期性長的枯水期,就要建壩建閘,這些工程會嚴重影響鄱陽湖冬季的水文條件,給候鳥遷徙和棲息帶來危害。”在周海翔看來,在棲息地的保護上,“不帶建設”的保護意識和行為尤其重要。
此外,人為透過種莊稼或者投食,來吸引和留住鳥類,也是違反自然規律的做法。“好比這個地方的生態系統只能容納500只鳥,刻意投餵玉米、種蓮藕,讓鳥類數量達到1000只,這種做法沒有意義,它從根本上破壞了物種之間的平衡關係。”
自然界中,物種之間是相互關聯的。多個物種組成一個穩定的生物群落,形成的原因在國際上有幾種理論解釋:一種是隨機自然生成的中性理論,另一種是植株高低搭配的生態位選擇結果。
作為植物學家,楊文忠認為,不能忽略植物之間的資訊交流,“無論是透過揮發性物質,或是其他物質交換,植物之間是有‘語言’的。”楊文忠說,從生物多樣性保護角度看,少了一個物種就缺少了一個交流者,保護極小種群看上去只是保護了某個物種,其實是在保護自然生態系統,在保護我們的生存環境。
周海翔認為,只有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人們才能學會與動物、自然和諧共生。
新京報記者 張建林 張璐 馬瑾倩
編輯 白爽 校對 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