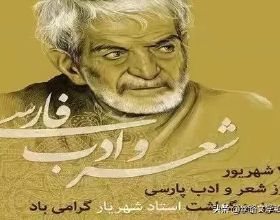吳思敬《 中華讀書報 》( 2021年08月18日 11 版)

《孩子們的詩:給媽媽炒雨》,耿立、荒林主編,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3月第一版,40.00元
“真”是詩歌的基本品格,在這本詩集中,基於生命本真、而又在虛幻的時空中展開的詩作比比皆是。
兒童詩就作者而言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詩人給兒童寫的詩,這些作者儘管是成年人,但葆有一顆童心,能以兒童的眼光觀察世界,寫出的詩受到孩子們歡迎,可有時也難免流露出一些“大人腔”“說教氣”;另一類是則是兒童自己寫的詩,他們不是為別人而寫,也不是為某種實用目的而寫,他們只是有話要說,有感受要表達,寫出的詩句,儘管稚拙簡單,卻自然天成,是真正的兒童詩。這本詩集《孩子們的詩:給媽媽炒雨》,便屬於後者。這些詩歌的作者大多是從五六歲到十三四歲不等的孩子。翻開詩集,讀著那些稚氣的、奇妙的詩句,彷彿面對著一個個充滿好奇、純潔善良的靈魂,小讀者們會從中照見自己的影子,成年讀者也會從浮躁的世俗生活中解脫出來,回到自己的孩提時代,讓靈魂得以淨化,心緒得以安寧。
孩子們能在生活經驗欠缺,知識結構不完善,語言儲備不充足的情況下寫出奇妙的兒童詩,靠的是一顆童心。童心的特點在於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李贄:《童心說》)。“真”也是詩歌的基本品格,說到底,詩是掏自心窩子的一句真話。這個集子中孩子們的詩,所寫內容不同,深淺不同,但共同的特點是真,孩子們寫詩不需要戴面具,完全出自內心,我手寫我口,我口言我心。童心的另一特點是超脫實用,這與兒童的思維方式有密切關係。按照皮亞傑兒童發展心理學的觀點,兒童的思維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社會化的思維,是兒童與社會打交道時用,有明確的指向性;另一類是我向思維,是一種自我中心化的思維,是朝向自身的,兒童的自言自語便屬於這一類。兒童在非自覺的狀態下把自己的需要和慾望投射於客體,為自己創造一個想象的夢幻般的世界,它不是為了適應現實的某一目標,而是隻求滿足內心的慾望。我向思維由於排除了實用的功利俗念的干擾,因而有可能超越詩人所處的具體時空,建立一個瑰麗奇妙、閃耀著自己審美理想的藝術天地。在詩集《孩子們的詩:給媽媽炒雨》中,這種基於生命本真、而又在虛幻的時空中展開的詩作比比皆是。
殷明碩小朋友在吃掉渣餅時,突發奇想:“是誰把吃剩的/掉渣餅扔了/扔在/那漆黑的夜空/一半變成了月亮/掉下的/渣渣/化作星星”(《是誰把吃剩的掉渣餅扔了》)。這樣的寫法,讓人想起詩人顧城12歲時寫的《星月的由來》:“樹枝想去刺破天空/卻只戳了幾個微小的窟窿/從那裡透出天外的光亮/人們叫它月亮和星星”。這兩位小作者,均置星月由來的科學結論於不顧,或者是不懂,卻從身邊的生活展開聯想,對星月的由來做出自己的解釋,異曲同工,令人叫絕。
考察一下孩子們寫詩的思路,會發現他們大多是從眼前的生活景象出發,但不是遵循尋常的思維路線,而是突然轉換方向,迸發詩意。如徐聖喬的《海螺》:“我聽到了海的聲音”,循正常思路,下邊應是對海的聲音的具體描摹,小詩人卻突然一轉:“我想進到/海螺裡面,/看看裡面/有沒有海”,這就把那種喜歡探險、好奇的孩子心境合盤托出了。再如盧君珂予小朋友的《西瓜藤》,也是從眼前見到的景物寫起:“西瓜邊上的藤是什麼?”按正常思路,下邊該是對瓜藤的介紹了,但作者卻做出了自己的判斷:“是電線嗎?/西瓜也要充電吧”,一個稚氣、天真孩子的形象就浮現在你面前了。再如林蔚然的《曬被子》,也是從日常生活寫起,但作者寫的卻不是常見的被子,而是把受潮的白雲看成被子:“天空把受潮的/白雲被子/掛在山頭晾曬/沒想到/山調皮地/伸了一個懶腰/被子一下子/滑了到了/半山腰”——山腰中的白雲居然是這樣來的,真是匪夷所思!這種隨心所欲的想象,打破常規的寫法,連成年詩人都不能不佩服。
當然,孩子也並非處在與人隔絕的世外桃源,當他走進成人社會的時候,他所持的觀察世界的態度,會與成人的思維方式相碰撞,這在他們的詩作中也有反映。像劉存豫的這首《紙飛機》:“我有一個飛翔的夢/那天,我折了一個紙飛機/幻想它能飛上藍天/替我向白雲阿姨問個好/這時老師走過來了/紙飛機碎了/我的夢也碎了”。
至於成人社會中為追求工業化而導致的環境汙染,在孩子的純潔心靈中更是不能忍受,他們用稚嫩的聲音發出了抗議。像穆薇的這首《天空哭了》:“天空哭了/它渾濁的淚水/驚醒了小草、小花//它們問天空/你為啥哭呢?//那黑黑的大煙囪/把我的眼睛/燻壞了”。像鄭子都的《海的眼淚》:“誰來保護海/大海像委屈的孩子/那海岸像彎曲的眉毛/一片狼藉/垃圾、汙水沾染了她的眼珠/使她睜不開眼/她揉揉刺痛的眼/幾滴淚流出/可淚水融入海水/又有誰看得到她的痛苦呢?”
隨著年齡的增加,孩子在成長。成長的經歷自然會成為孩子們詩歌創作的內容。孩子的生活不只是遊戲與喧鬧,孩子的心靈也不只是離奇的夢幻,他們也有對自己人生的思考。黃祥鈺有首詩叫《我到底從哪裡來》,追問自己是怎樣來到這個世界的。一個叫明年的小朋友寫的《如果克隆一個我》,則展示了真實的我與克隆的我的對話,是對自我的重新發現與真實解剖。
這種成長的歷程,在典典的詩歌中有更明顯的表現。典典七歲的時候,她把天上的雲彩當成綿羊,寫出了充滿稚氣的《綿羊,雲彩》;當她14歲,成為少年的時候,她開始思索人生,在《童年》一詩中,她寫道:
我揹著一個大口袋,/出門去尋找童年。/找啊找啊,/童年終於被我找到了。/我把它裝進袋子裡,/背到家一看——/哎呀!/童年只剩下一點兒了。/原來,當我翻過高山時,/樹枝勾破了袋子;/當我走過平原時,/荊棘刺破了袋子;/當我渡過小河時,/河水浸透了袋子;/於是,童年就從袋子裡,/悄悄地溜走啦!/——這個袋子就是回憶。
這首詩的思維方式、所用的口氣,都是孩子式的,她把看不見、摸不著的“回憶”賦予了一個“袋子”的外形:“我揹著一個大口袋,出門去尋找童年”——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何等鮮明!“童年”是這首詩所要寫的主題,“尋找”是這首詩的主旋律。這是一首成長之詩,意味著孩子由兒童向少年的轉換。
為了保留與強化詩集中的童真童趣,編者還特別請中國摩西奶奶楊佩蓮配了插畫。楊佩蓮奶奶80歲了,卻葆有一顆童心,富於想象,她的畫自然天成,趣味盎然。她用孩子的眼光觀察世界,用稚拙、獨特的畫筆,給孩子們的詩還原出了一個童話世界。孩子們的天籟之音與老奶奶的畫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為這部詩集增添了無窮的魅力。
來源: 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