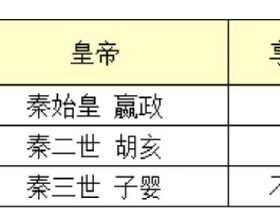“民族”不僅僅是以血緣、地域關係為基礎形成的人類共同體,更為重要的是以文化的共同體而緊密聯絡在一起的穩定的人類共同體。巨大的文化差異使人們可以區分“我族”和“他族”。
民族認同是一種心理活動,在民族認同逐步加深的過程中,族群成員透過對本民族文化的認知和感受進一步確認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因此,可以說文化是民族認同的基礎和天然邊界,是體現民族認同的一個最主要、最基本的方面。民族的認同感總會在特定的民族文化上得到表現,留下或隱或顯的印記。
民族認同是在一定歷史情景當中建構的,它也會隨情景變化而變化。影響民族認同的因素既有社會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同時也有心理方面的因素。這種複雜性決定了民族認同研究需要多學科的視角。民族認同的文化聯結來自原生性要素的紐帶,如習俗、血緣、祖源、語言等的共同性,除此之外,宗教、服飾、建築等所有外顯的文化要素都可以作為人群互相區別的標誌。這種認同的因素,在中國古代可能表現得更為直接或明顯。
“北魏(386-534)是中國佛造像的黃金時代,許多佛像名品大多出於北魏”,而且“在北魏時代的佛教造像上,非常流行在臺座或背面表現胡服(中國北方民族穿著的衣服)供養人像,說明了鮮卑族接受佛教,以造像的形式實踐佛教活動。造像主,即供養人留下自身的形象目的是作為‘造像的記錄’,以明示自己的發願及出資,享受造像的功德。供養人像的表現早見於太平真君年間的造像中,在單體金銅佛和石雕像上是通常的做法,在石窟造像中多表現於佛龕臺座部分。”
佛教造像中無論是供養人還是佛像,他們的服飾都非常直觀地反映了當時人的服飾狀況,尤其是中國石窟造像中的供養人形象,大抵都是造像功德主本人形象的狀摩。十六國北朝時期大量的造像碑記不斷地被發現,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的姓氏、服飾資料,這為進一步探究當時的社會生活、民族關係等提供了方便,同時使研討十六國北朝時期的民族認同成為一種可能。
因此,在這一部分,分析的落點主要放在影象上,即從各種石窟造像或題記中供養人服飾與姓氏的變化上探討其中所反映的民族認同情況,因此,在論述這一問題之前,有必要先釐清何謂胡服,何謂漢服,以及在中國古代姓氏與服飾如何表達民族屬性資訊,如何反映民族認同等問題。
一、胡服與漢服的形制
“胡”是我國古代尤其是兩漢時期至南北朝時期漢文文獻對北方遊牧民族的統稱。因此,本書中所指胡服主要是指古代非漢民族或非華夏民族服飾。
胡服在漢文史書記載中出現得比較早,戰國“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到南北朝時期,有相關史籍比較詳細地記載了胡服的具體形制。“(高祖)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由此可見,“夾領小袖”為胡服的一種形制。
《梁書》載:“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女子披髮為辮。”《舊唐書·輿服志》載:“爰至北齊,有長帽短靴,合胯襖子,朱紫玄黃,各任所好。”王國維的《胡服考》載:“胡服……其制,冠則惠文,帶則具帶,履靴。其服,上褶下袴。”
此外,“張晏雲‘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講述鮮卑郭落帶刻有瑞獸,並認為“鮮卑”族名即其瑞獸之名。但是,由於漢服也有腰帶,在雕刻中服飾腰帶細節較不明顯,故不能以此進行判斷。此外,還有從左右衽來區分胡、漢民族,認為漢族的服飾為右衽,胡族的服飾為左衽,即胡族“披髮左衽”。由所引史料,可以推知胡服形制應為遮耳長帽、夾領、窄袖、長褲、短靴等,故本書在此後的討論中主要以是否具有這種特徵來判定供養人的服飾是否為胡服。
與胡服相對的即為漢服。《漢書》載:“武帝末……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後漢書》載:“郭太字林宗……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釋名疏證補》卷五《釋衣服》詳細介紹了東漢後期褥、絝、褶、禪衣、裙、袍的漢服形制。《陳書》載:“胡服縵纓,鹹為戎俗,高冠厚履,希復華風。”因此,漢服以冠冕、廣袖、長袍、厚履為主要形制,故在此後的討論中以此形制為特徵的“褒衣寬頻”服飾均判定為漢服。
關於胡服,有沈從文、周錫保、呂一飛等先生的研究,其中有關北朝胡服的情況,在呂先生的著作中有詳細討論,可參閱。基本上“胡服的上身男女都是交領(衣襟重疊)、窄袖(筒袖。袖口很小,袖子很短)的長上衣,下身穿短褲(與今天的褲子一樣分兩岔的形式)”。
人類從矇昧時代進入文明時代後,服飾便成為必不可少的日用生活品。服飾除用來遮蔽和保護身體外,還有一項極為重要的功能就是社會標誌功能。“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是中國古代對一個群體的不同認識。
透過一個人的服飾,可以大致看出其社會地位、經濟狀況、生活方式、審美趣味等。《春秋繁露》載:“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
《禮記·大傳》載:“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中國封建社會中,服飾強烈地反映著等級、名分的差別,社會成員都必須依照自己的等級身份來穿戴,衣、帽、鞋、襪、裝飾品等等,無一不在形制、質料、圖案花紋及色彩上有嚴格的區分,不能僭越。皇帝的服飾,自然是唯我獨尊,臣民不準僭越。百官的服飾,平頭百姓當然也不許穿戴。
百官之中,大官與小官的服飾又有區別,不得混雜。就連一般老百姓——士、農、工、商的服飾也各有區別。還有,男尊女卑,其服飾也得有所區別,不能混同。這就形成了一套完整嚴密的服飾制度,把人們的高低貴賤區分得清清楚楚”。
服飾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在一定歷史階段中的文化傳承現象,是生活民俗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它既有歷史的傳承性,同時又受到民族性、階級性和區域性等諸多社會因素的制約,是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折射。
也正因為服飾有如此多的功能,所以在中國古代特別重視服飾,每逢改朝換代,首先便要“易服色”,以宣示新朝的建立及正統性,讓“服色”的政治意義首先服務於新王朝的合法性,在運用“改正朔、易服色”來說明自己政權的合法性時對之進行了種種改易,正朔、服色的影響最終僅作為一種儀式性的政治名分而存在。帝王透過“改正朔、易服色、別衣服”,可以使臣民意識到改朝換代,促使其認同的轉變,達到取得天下正統的目的。
不僅如此,服飾也時常是民族邊界的一個標誌。“冕旒衣冠,在現代人看來,也許只是外在裝束,充其量也就是一個民族風格,或者在正式場合中作為身份標誌,並沒有什麼太嚴重的意義。
但在古代東亞來說,冕旒衣冠卻是‘承認’和‘認同’的象徵,不僅涉及民族(華夷),而且涉及國家(王朝),甚至呈現文明與野蠻(文化)。傳統儒家學說所形塑出來的政治制度和觀念世界,似乎特別在意衣冠的象徵性,無論是政治上的等級,還是家族內的親疏,都要依靠衣冠服色來確認,就連王朝的合法性與文化的合理性,也得要靠衣冠來建立”。
不只是中國學者對服飾與民族認同有如此闡釋,外國學者也認識到在中國古代,服飾與民族認同的密切關係。如日本學者在對雲岡石窟造像研究時,認為其11窟“著鮮卑服的供養人像,表現佛教信徒形象的同時,也表示自己是屬於推崇跟佛陀同等的皇帝的鮮卑國家的成員”。
“他們雖然是從佛教信仰出發,但實際上極具政治性和社會性的意義、目的和功能。以胡服表現的供養人像意味著他們是鮮卑國家理想的臣民像,具有表示向統治者順從意志的功能。”
“當然,供養人影象的意義、目的和功能隨時代、民族和地域不同而有所變化。北魏時期,經服制改革,漢服被定為公服後,漢服供養人像成為理想的臣民像,而胡服逐漸失去了其‘表示服從意志’的功能。相反,胡服也有被視為對統治者‘不信服的表示’的可能性。服裝顯示該時代的民族性和國家的統治構造,這不僅僅是北魏唯一的時代現象。佛教造像這一宗教活動被利用為向統治者表示意願的一個‘場所’,供養人像這一影象功能是其表現方法”。
也正因為服飾在中國古代有如此重要的意義,因此,“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武而毀趙他”。在各個新建王朝服制改革過程中,經常會出現一些強烈的反對或抵抗等事件,尤其是在非華夏民族建立政權的情況下,反抗行為可能會表現得更加激烈,而這種反抗情緒無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人們的民族情感及認同傾向。
我們比較熟悉的是清朝的剃髮令引起的風波。從清初入關起,滿族統治者就強調天下應當“剃髮易服”,以表示遵從大清正統,這也說明在滿族人的心目中,服飾與髮型也是王朝認同的一種標誌,當然這種想法也許是他們受到漢族政治觀念的影響,才意識到“改正朔,易服色”對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性。
因此“明末清初,清兵殺進中原,漢人為君父而做的抵抗沒有多少,但因為剃頭和易服卻進行了激烈的抗爭。國土淪亡、君父誅殺、朝代更迭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都沒有像改穿衣服和剃頭這樣的小事能引發百姓心理上的失衡。
同樣,滿清朝廷也在這些看似小事的方面更較真,‘留髮不留頭’,一點通融也沒有”。這種現象可以是佛教造像中“(供養人)透過對服飾……的描繪,可以清楚地反映供養人的性別、族群系屬……社會地位,這些都是認同建構的核心要素”最好的解釋,而且在現代社會,服飾在一定程度上與一個群體也有密切的關係,比如,20世紀八九十年代流行的一首歌的歌詞“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仍然是中國心”,將“裝”與“心”聯絡在一起,從另外一個方面說明服飾的確能體現一個人的民族特徵,以及對某一群體的認同與歸屬。
雖然,在現代社會中,服飾作為民族認同、民族界限的標誌已經有所弱化,但是,從古代帝王以“改正朔,易服色”的方式試圖改變民眾的認同,以及自古觀念中的胡族“披髮左衽”,漢族“褒衣博帶”的固有認識,可見在中國古代,服飾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一個民族或政權的邊界表徵,那麼對服飾的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就體現了民族認同。
二、姓氏
除服飾之外,姓氏在古代也是判定族屬的重要標準之一。姓氏制度並不單純是一種名號制度,而是與當時的政治制度、經濟關係、家族形態、社會心理、禮俗特徵等各個方面都有密切的聯絡。
在古人看來,“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為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之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姓則表其所由生,氏則記族所由出,其大略然也”,因此姓氏與宗族、婚姻聯絡在一起。但隨著國家的產生,社會分化為不同的階級,出現不同的階層,姓氏的意義很快突破“別婚姻”的侷限,而被賦予區分社會等級、體現社會成員尊卑貴賤的特殊政治功能。
姓氏的尊卑貴賤等級之分,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其一,某些姓氏的起源,與姓氏家族的政治身份及社會地位有直接的淵源關係;其二,天子、國姓在姓氏系統中享有神聖的至尊地位;其三,以現實官位權力大小劃分姓氏的高低等差”。
由此可知,姓氏在中國古代成為族群認同的一種文化符號,亦成為人們獲得合法身份的一種象徵符號,另外,姓氏在宗族觀念的發展和宗族組織的建構中,是一種可資利用的文化符號,姓氏的改變更表現出人們面對具體社會情境所做出的策略性選擇,是人們對文化資源的合理巧妙利用。
正如陳連慶先生所說,“姓氏對歷史研究的作用至少有三:一是對史實的考證。特別是在民族關係複雜的歷史時期,對政權、戰爭的民族屬性判斷,首先是要弄清人物的族屬,而姓氏則是判斷族屬的重要根據……二是有助於民族史的研究,可以由姓的發展變化淵源,推知其族屬,探尋出其族的歷史變化……三是有助於文化史的研究。
我國古代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漢族與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是雙向交流,但有關歷史文化的記錄多體現在歷史人物身上,因此只有從姓氏判斷出人物的族屬,才能弄清文化的民族淵源”。故自古以來姓氏中本身存在一定的認同因素,而這些姓氏與各民族聯絡起來時,對姓氏變革,經由姓氏進行的族源追溯,又使得姓氏中的認同展現出民族因素,即體現民族認同現象。
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學術界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認可姓氏在研究民族史上的重要地位。
幾千年來,中國人的姓氏一直起著別婚姻、分貴賤、辨親疏、團結同姓、鞏固宗法制大家族的作用。正因為如此,姓氏研究也得到了學者的重視,也多有學者從姓氏的變化情況來研究十六國北朝時期內遷民族的漢化,以及漢人胡化的情況。
馬長壽先生《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一書透過造像題記中體現的姓氏等內容,分析與印證中古時期關中各族的族屬淵源、姓氏變遷、分佈、通婚及融合等問題;周偉洲先生也透過姓氏並結合相關史料研究十六國北朝時期的民族史,同時,周先生也利用造像資料探討氐、羌民族在關中、隴右地區與漢族錯居雜處及與漢族融合的狀況;何德章先生利用北朝墓誌資料所反映的姓氏變遷情況研究拓跋鮮卑等族的漢化。
這一切都說明,在中國古代姓氏與民族身份有千絲萬縷的聯絡。因姓氏在判定族屬、研究民族認同中的重要作用,故本書基於造像中出現的供養人形象以及題記資料,在胡服、漢服、胡姓、漢姓判定的基礎上,主要對造像中供養人姓氏、服飾中體現的民族認同進行探討。
(作者:吳洪琳)
(來源:《合為一家:十六國北魏時期的民族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