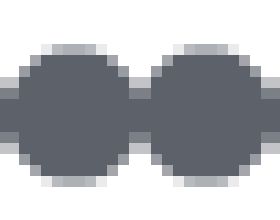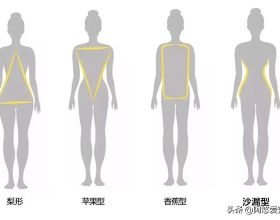茹誌鵑的小說《百合花》被茅盾撰寫評論推薦後,成為廣受歡迎的作品。圖為1981年出版的連環畫版《百合花》。資料圖片
1980年11月,茹誌鵑致信茅盾,感謝茅盾先生為其新作品作序推介。資料圖片
【如何讓文學評論更有力量】
1944年春天,翻譯家、文藝理論家傅雷在《永珍》雜誌發表《論張愛玲的小說》,對張愛玲的作品進行鞭辟入裡的評論。在分析《金鎖記》時,他對其人物刻畫之入木三分、意境營造之出神入化、語言技巧之鬼斧神工等都予以激賞,認為這部作品“頗有《狂人日記》中某些故事的風味,至少也該列為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
同時,傅雷對正在《永珍》連載的張愛玲長篇小說《連環套》徹底否定,認為無論內容還是語言風格,皆流於惡俗,預言這部作品“逃不過剛下地就夭折”的命運,正告作者務必愛惜自己的才華,嚴肅創作態度。
年少氣盛的張愛玲對傅雷的耳提面命大不以為然,寫了《自己的文章》聊作回應。晚年的她翻閱《連環套》羞愧難當,坦言“儘管自以為壞,也沒想到這樣惡劣,通篇胡扯,不禁駭笑”。
七十多年後的今天,重讀傅雷的這篇評論文章,感覺仍不失為一篇見解不凡、文采斐然的妙文,給人以藝高人膽大、赤誠相見的鮮明印象。我們依然期待這樣“有力量”的文學評論文章。
對好作品“叫好”也是有力量的評論
文學評論與文學創作本為文學之雙翼,是一種相互砥礪、並駕齊驅的關係。但很長時間以來,文學評論似乎只會說“好話”了。並非文學評論不能褒揚,也並非文學評論必須吹毛求疵,這裡所說的“好話”,實際上指的是那種“強將笑語供主人”式的言不由衷的“好話”,或是那種“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式的人云亦云的“好話”,或是那種“皇帝的新衣”式的自欺欺人的“好話”。
假如文學作品確實達到了爐火純青之境,又何嘗不可以拍手稱讚、逢人說項呢?這種毫無保留的“叫好”,同樣亦是“有力量”的評論,而且意義重大。
1958年3月,茹誌鵑在《延河》發表短篇小說《百合花》,以靈妙之筆寫殘酷的戰爭題材,講究鋪墊與神韻,講究留白與象徵,與當時流行的英雄書寫風格迥異,卻令人內心深受震撼。
茅盾慧眼識金,讀後立即為之撰寫精彩評論,通篇都是讚語。《百合花》得以轉載於當年《人民文學》第6期,贏得好評如潮,至今仍是膾炙人口的經典佳作。設若當年沒有茅盾的披沙揀金和著意推舉,《百合花》銷聲匿跡於當時的文化語境之中,恐怕是極有可能的。
培養優異的審美直覺和悟性
識人賢否不易,道作品長短亦難。好的評論家要有紮實的理論功底與出色的理性思辨能力,更要有優異的審美直覺和悟性。二者兼具,方能對作品的內涵進行精闢闡發,方能對作品的得失作出令人信服的評判,並提出中肯的建議。劉勰說:“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這“操千曲”與“觀千劍”,意味著長期不懈地流連於古今中外文學原創經典,孜孜不倦地含英咀華。
應該說,詩乃一切文學之核心。無垠的想象、極致的抽象、神秘的哲理,最是集中於詩中。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無不是詩性的充分呈現,《紅樓夢》《阿Q正傳》《雷雨》《哈姆雷特》《堂吉訶德》《局外人》《老人與海》《邊城》……我國自古就是詩之王國,天人合一觀念始終統攝著文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意象思維從來都是文學創作的看家本事。要加倍增強審美感知能力,必須多讀詩,多讀詩性之作。中國古代的詩話,對培養審美眼光尤為得力。而西方深刻的文藝理論著作,則有助於提升我們的理性思辨能力,深化對文藝作品的理解,並啟迪我們找到恰當的研究視角與學術路徑。
有生命力的文學評論,建立在真切而深刻的審美感受基礎之上,而不可能只是冷冰冰的就事論事,乾巴巴的邏輯推理。評論家首先應該從文學作品中體驗到一種異乎尋常的生命感動和靈魂震撼,引發深入思考,然後才去抽繹和總結隱含其中的某些本質性、規律性的東西。在當今全球一體化的時代,不少學者發現,將西方現代人文社科理論應用於我國的當代文學研究,對於開啟思路、拓寬視野、構建新的學術體系頗有裨益,但在實施過程中往往由於對文學作品缺乏真切生動的審美體驗與感悟,文章寫得生硬艱澀,了無生氣,讓人難以卒讀。
好的文學評論要開拓創新、持論有據
文學評論界少諤諤之音、多好好之言,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很多,近來一段時間專家學者已從諸多方面進行了探究和反思,此不復論。除此之外,大概還有“溫良恭儉讓”傳統文化因素的潛在影響:“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不彰人短,不炫己長。”……長期接受這樣的心理暗示,在評價作家作品時,自然而然地會收斂起自己的直性和鋒芒,謙恭自持,溫柔敦厚,只關注好的、有價值的地方,忽略差的、有缺陷的方面,以免傷人自尊,從而規避可能引起的麻煩與爭執。“禮之用,和為貴。”為了“和”而按下內心的種種“不同”。顧忌多多,思維勢必受到侷限,研究思路就易於循規蹈矩,難以創新,難以出彩。
事實上,文學作品一旦問世,它就成為一個獨立而客觀的存在。評論家有必要拋開世俗的私心雜念,依照自己的認知與體悟,對作品的價值進行闡發。唯有這樣,他才能有新發現、新收穫,評論才能有的放矢,發揮實效。學術乃天下之公器,需要一種為達真理無私無畏的勇氣,褒貶出自公道,推論源自真憑實據。評論家也務必堅守學術良知,把研討限定在文學的界域之內,秉持公道心與同理心,持論有據。作家最要緊的是擁有一顆平常心,“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進行文學評論,再三再四的文字細讀自然必不可少,而評論者與作者雙方的溝通交流亦是一個行之有效的途徑,彼此互相啟發、互相促進。對作者而言,透過這種推心置腹的交流對話,他對自我內心世界的幽微角落抑或潛意識層面,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對自己作品的結構設定、推進節奏、語言技巧等方面所存在的問題,也常常會有不期而遇的頓悟。對評論者來說,則會因這種智慧的碰撞而靈光四射,發現新的研究切入點、開啟新的研究介面。
研究已經過世的作家,各種史料諸如作家本人的談話、日記、親友回憶錄、作家年譜等,有必要加以細心研讀。路遙自傳色彩很濃的小說《人生》,讀者不約而同地認為小說中男主人公的原型是作家本人,而對書中女主角巧珍的原型則很少追究。中國社科院文學所青年評論家程暘《路遙〈人生〉中巧珍的原型》一文,透過對路遙生平各種史料的深入分析,認為巧珍的原型有村支書劉俊寬女兒劉鳳梅、路遙初戀女友林紅、妻子林達等多位女性的投射,亦有路遙自身的影子——面對文化心理強勢的北京女知青,路遙在戀愛、婚姻關係中始終是十分軟弱和自卑的,其本人在彼此交往、相處過程中所體驗到的種種酸澀苦痛,都為他寫活善良、痴情、怯懦的巧珍這一農村女孩形象注入了養分,“路遙在巧珍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困守鄉下無法施展的制度性障礙”。這就超越了個人層面,與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發展程序具有多重關聯。這樣的視角對研究其他作家的創作心理亦很有啟發。
愛因斯坦曾說:“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因為解決問題也許僅是一個數學上和技術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問題,新的可能性,從新的角度去看舊問題,卻需要有創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標誌著科學的真正的進步。”這段話也適用於文學評論,只不過解決科學問題需要資料分析,而解決文學問題則需要史料支撐而已。
文學創作,需要才情、學力和嘔心瀝血的忘我投入,方能有所建樹;文學批評,相比之下對理性思辨能力的要求更高一些,需要在類比分析和邏輯推理方面多下功夫,但同樣也和作家一樣,需要“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博覽群書,取精用宏,有開闊的視野,有深刻的洞察力,有敏銳的判斷力。唯其如此,面對文學作品時,方能獨具隻眼,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和主張,並能左右逢源、有理有據,令人信服。
(作者:趙海菱,系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