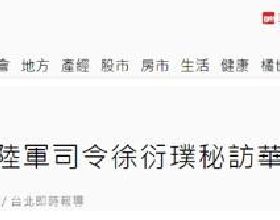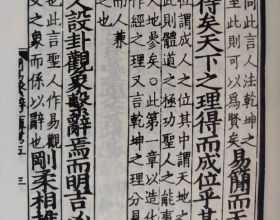□ (美) 凱瑟琳·保爾森 孟心怡 譯
這個墊著保鮮膜的紅陶盆,曾種過菊花,現在裡面放著一些硬幣,已經有一年時間了。盆很乾淨,但邊緣仍有一些泥土的痕跡。紅陶盆佔據著工具臺的中心位置。它這麼小心翼翼地被放在正中間,很明顯不是個多餘的破爛兒,來訪的朋友總是問,你什麼時候用那個東西種花啊?她會回答,等到有人送我一棵。然後笑笑,指指盆底的一把硬幣。
很快,朋友也開始丟一分硬幣了。是一個年輕,又沒那麼年輕的,和她“經常見面”的男人開的頭,其他人很自然地跟風。他們叫它“凱特的許願井”,有些人聲稱真的有願望成真了。她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認真的,因為每個人都知道,說出願望的內容會倒黴,尤其是在願望已經成真後。
凱特自己從沒許過願。她問自己,有什麼我想要的東西不是半好半壞的。她很害怕好壞參半的東西,多數東西對她來說都是這樣。她的年輕男人,新的那個,叫邁克,現在還很好。他的前一任,瞞著凱特開始用硬幣許願的那位,覺得穩定且不那麼神秘的年輕女士更合適自己,能為他做飯生孩子,而這些凱特不太情願去做。她不覺得留住這個男人,或其他任何男人,值得為之許願。

有時候她想問,她能用那些“許願幣”做什麼。尤其深夜,她在小桌前寫作時,光禿禿的燈泡把她的影子投射在對面的牆上,在牆角邊,還有廚房的窗戶上,影子看上去有十英尺高。這些硬幣大部分都來自她自己,是節約得來的,既瑣碎又無用。儘管其中的一小部分——那些朋友拿來的硬幣,充當了給幸運之神的賄賂。當她沉思時,一隻巨大的手指會掠過她一綹綹頭髮,之後下移到打字機上,彷彿柔軟黑暗的動物。她可能會嘆氣,下巴撐在手腕上,那怪物的頭就會突然出現在拐角。
一天,傳來一陣意想不到的敲門聲。是個鄰居,樓下住的那位邋遢、蓄鬍子的年輕人。他取下帽子,像鐘擺一樣來回揮著它,說道:“我聽說您有個許願碗。我不太相信那種東西,但是我覺得您會樂意讓鄰居扔個硬幣,討個好彩頭。”

“其實是個花盆,”凱特回答,領他走到那兒。他扔下兩枚一分硬幣。走到門口時,像是要取回落下的大衣一樣轉過身來(其實他忘拿的是他的帽子),扔進第三枚硬幣。
其他鄰居也開始順路拜訪,獻出他們的硬幣,凱特的花盆幾乎滿了。裡面有多少硬幣?一千?五千?還是五萬?一旦花盆滿了,她就不得不想法處理這一小筆錢。硬幣要是溢位來就不好了。
問題是,她要用它們買點什麼。不能是普通的東西——實際上凱特寧願不用這筆錢買任何東西,但是她有一點點迷信,覺得這些硬幣不能再被送出去。她可以把它們埋起來,讓它們滋養土地,但她的公寓樓沒有院子。
想了又想,她突然有了主意:花盆自己會告訴她怎麼花掉這筆錢。她要帶著它出去,到廣闊的世界上,四處走走直到有什麼東西說“買我”。
一個晚春的傍晚,當硬幣滿到了花盆邊上,硬幣堆中間略有凹陷時,她扔下了那天最後一枚硬幣,想著,“完成了。準備好了。”她最後一次用指尖撫過硬幣表面,聽它們叮噹作響。明天就是購物日了。
那晚她幾乎沒睡著。

早上,她打扮好,肩上挎著她的郵差包,鑰匙放在口袋裡,把門設成自動關閉,這樣她就不用空出手鎖門了。她在花盆上方彎下腰,雙手繞住盆底,抱起了它。它比她希望的重一點,但也沒有她期待中那麼重。
她出門下了樓梯,外面一陣涼爽、親切的風迎接了她。她向右轉,走到街角再左轉,走上了第一條購物街。她小心翼翼地經過了理髮店、美甲沙龍、修鞋鋪、藥店和餐廳,停在拐角處,直到可以安全透過。雖然沒有對視,但她感覺到了陌生人好奇的目光。花盆是不是比一般的幼兒重呢?
下一個街區有一家小飯店、一家影印店、一家二手商店。她在二手商店停留了一會兒,檢視櫥窗裡的物品。沒有東西呼喚她。她本可以走進店裡,而不是繼續走下去,就這樣路過了一家比薩餅店、一家玩具店,走到一家音樂商店,在這裡她又等待了一會兒:她的未來會不會有一件樂器,或至少有張CD呢?如果沒有其他東西呼喚,也許是在回來的路上……
又出現了一個拐角:是直走還是轉彎?她轉彎了,出現的是銀行、手機店、投幣式自助洗衣店。面前的一家藝術用品店令她嚮往。風越刮越大,她也越走越快——她已經習慣了臂彎裡的重量——直到有什麼東西撞了她的胳膊肘。一隻大塊頭橘貓跳到她面前,她雙手一鬆,花盆飛了出去。

像一輪巨大的帶斑點的太陽,銅幣之間點綴著陶土碎片撒了一地。幾千個一分硬幣。撿起大部分硬幣需要好幾個小時,何況已經沒有裝它們的容器了——她的計劃到此為止。
那隻貓向上蜷縮起後背,向她咆哮著,就好像在說,看看你做了什麼,大傻瓜。
“沒錯,我是傻,”她自言自語。她至少可以撿起花盆的碎片。當她彎腰開始撿的時候,那隻貓大步走近,貼著她的手。它的皮毛髒成了一片毛墊,一隻耳朵缺了個口子——是隻流浪貓。現在是她的貓了。她展開臂彎,而貓走了進去。
她輕撫著它的毛,抱起了貓。它比那一盆硬幣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