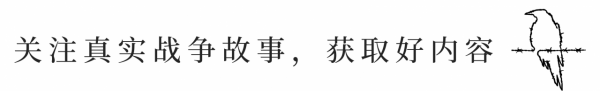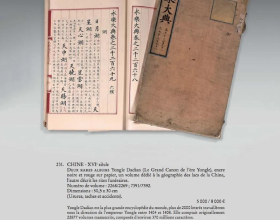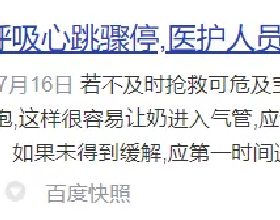1951年的5月21日傍晚,我在“三八線”以南的韓國境內,等待隨軍撤退。
突然,遠處傳來了一箇中國老太太的聲音:
“志願軍孩子們,你們家裡的父母都在想念你們,快回家過太平日子吧,不要再替別人去賣命了。”
我還沒反應過來怎麼回事,營地槍炮聲大作起來。
我們極有可能已被敵人包圍,形勢千鈞一髮。
27軍第五次戰役的東進突擊,真可謂出師不利。
進攻第二天軍政委就翻車身負重傷,第四天,政治部又遭遇重創,現場慘不忍睹。
我至今記得十分清楚,那是5月的12日拂曉。軍政治部隨部隊急行軍後,在一個山溝裡開始露天宿營。
我沿著山溝走到一棵孤立的樹蔭下,覺得在此睡覺既隱蔽又涼快,也便於發現敵機。於是,我解開雨衣鋪在地上,枕著揹包仰面朝天躺了下來。
也就那麼一支菸的功夫,敵機呼嘯而至,機關槍和炸彈傾瀉而下,一顆炸彈的氣浪將我掀倒在地。
我爬起來用盡生平的力氣,頭也不回在45度角的山坡松林中,一股氣跑到了山頂,兩腿如同癱瘓了一般。
眼前的整個山溝濃煙滾滾,敵機已經換做了凝固汽油彈,落在哪裡哪裡燃燒。
敵機飛走之後,我急忙下山往還在燃燒的小木房處趕,那間唯一的小木屋裡,有政治部的首長。
儘管已經有了心理準備,但走到近前還是震驚了:小木房成了一堆灰燼,11具燒成黑色的屍骨沒有半點毛髮和皮肉,有的連骨頭也燒成了灰狀。
據不遠處的目擊者說,小木房中彈燃燒之際,兩位警衛員一齊撲進了烈火中,企圖救出自己的首長。
然而,一人被燒焦,一人被燒成重傷,只救出一位燒傷面積達70%的首長,結果也未能倖免於難,只保留了一個完整的屍體。
這兩位首長和那位警衛員,我都十分熟悉啊,可我欲哭不能,想喊又不成。
我們是軍裡的宣傳部門啊,五次戰役第二階段還沒正式打響,我們要是呼天嚎地痛哭流涕,基層部隊的官兵怎麼看我們啊。
我一看身邊的曲社長,眼淚也在眼眶裡打轉。剛剛在空襲中頭部受傷的社長,臉色蠟白,忽然身體一歪要暈倒,我急忙示意警衛員小徐將社長攙扶到衛生隊包紮傷口。
社長剛一轉身,我的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只是沒有哭出聲來。
警衛員救出的那位首長面目全非,並不知道是誰。最後,憑著一塊錶殼尚未熔化的手錶,這才認出了是張樂天部長的屍骨。
當時的手錶還十分稀罕,軍宣傳部只有張部長戴手錶。
就在昨天夜裡的急行軍中,見我實在撐不住了,張部長騎著一匹棕色馬從隊伍旁邊趕上來,說道:“小孫,看樣走不動了,你騎一會兒馬怎麼樣?”
見張部長彎腰要下馬,我反而覺得不累了,急忙上前推了一把:“我不累,部長。”
張部長又說:“要不,把你的揹包放在馬上。”
我一再擺手,並加快了行軍速度:“部長,我背得動。”
張部長見我一再謝絕照顧,只好打馬跑了過去。
張樂天部長是蓬萊人,老八路軍,是27軍少有的大知識分子,不僅工作水平高,也十分體貼部下,在機關部隊威望很高。
含淚分清屍骨後,我們就近刨了幾個坑,將兩位首長和警衛員的骨骸和遺物埋了進去,再插上一塊寫有姓名的小木樁。

當時的志願軍烈士大都是這樣匆匆掩埋的,至今他們都還未能回家(網路配圖)
這一天的宿營,軍政治部幾乎沒人睡覺,以至於軍首長下命令,睡不著也得閉上眼睛。
太陽落山時,部隊又開始出發了。
政治部的戰士去牽首長的戰馬時,它們一看是生人,立即悲鳴刨蹄,折騰了好長時間才加入了佇列。
戰馬是戰友,它通人性啊。
沒走多遠,兩匹戰馬突然回頭,又刨著蹄子嘶鳴起來。這情景,若不親眼所見,你是無法想象的。
真正是——馬蹄聲碎,喇叭聲咽。
不知為何,這一次的東進追擊一開始就很詭異。
戰士們徒步一夜快要追上時,敵人又坐上汽車開走了。
而且敵人並不一下撤退老遠,始終同我軍保持著若即若離的狀態,白天我休敵走,夜間我走敵休,走前必向我軍來一陣猛烈的炮擊,像是有意引我上鉤。
這分明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啊。
幾天後,急轉直下的形勢表明,這的確是敵人設下的一個圈套。
兵者,鬼道也。帶兵打仗謀略第一,戰術次之,虛則實之,實則虛之,這個老祖宗的東西我們當然明白,但敵人也不是笨蛋一個。
如果敵人一打就跑,一打就敗,抗美援朝志願軍怎麼會傷亡百萬呢。
綜合考慮後,我軍決定停止進攻,於5月21日結束五次戰役第二階段的作戰,開始回撤。
此時軍部位於“三八線”以南一帶,所屬部隊均駐紮在軍部以南,也就是說,此時的27軍全部在現在的韓國境內。
這天傍晚,由於部隊沒有作戰計劃,我一人去了附近的小河邊溜達。
我十分清晰地記得,這一天是陰曆十八,月亮一早就升起來了。河邊一片寧靜,金達萊花還沒有開敗,安靜的只有潺潺的流水聲。
突然,遠處傳來了一箇中國太太的聲音:
“志願軍孩子們,你們家裡的父母都在想念你們,快回家過太平日子吧,不要再替別人去賣命了。”
我先是覺得奇怪,戰場上怎麼蹦出箇中國太太來。
一會兒又傳來了一個成年男人的聲音:“你們帶的糧食已經吃完了,不能再打仗了,你們馬上就要敗退了,快投降吧!”
原來,這是敵人的“政治攻勢”。我納悶的是,我們還沒有接到撤退的命令,敵人怎麼已經提前知道了呢?
更奇怪的是,這個聲音,說它遠也近,說它近也遠,可又找不到喊話的人在哪兒,令人毛骨悚然。
我四處瞭望了好一會兒,才發現80師方向似乎一架像閃著航燈的飛機,聲音就是來自那裡。
這是一種美軍專用宣傳的飛機,不但飛得高播放範圍廣,而且馬達聲極小。
我還沒反應過來,突然,80師方向槍炮聲大作起來。
我立馬衝回了報社營地,曲中一社長正指揮大家將各自手中的檔案和有字跡的材料,全部就地燒燬。
社長沒有再說什麼,大家也沒有追問。因為命令燒燬檔案和材料,只能說明我們極有可能被敵人包圍,形勢已是千鈞一髮。
我的挎包裡放著我的木刻本和木刻板,上面也有我軍的標緻,我看著這些心血,實在不忍一火焚之,我偷偷把它們重新塞回挎包裡,死了也算有個安慰。
原來就在部隊決定向北撤退時,敵人搶先一步,派特遣隊開路進行大規模猛力反撲。
前一秒還在勝利進軍,一轉眼卻要開始逃命,我實在想不通。
緊急撤退的隊伍剛穿過一段平坦的公路,敵人的探照燈就射了過來。
方圓近百平方公里的山川道路,即使路上掉下一根針,也可以看清把它揀起來。
同時,敵人的宣傳機又開始了空中喊話:“27軍的弟兄們,你們撤退的路被切斷了,想走也走不成,只投降一條路了!”
“媽的,敵人怎麼知道我們是27軍,難道出了叛徒不成!”我一邊走一邊罵道。
沒有一個人相信敵人的喊話,但大家都意識到了危機四伏。不光是我,就是首長們也對能不能逃出險境捏著一把汗。
往日行軍的歡聲笑語沒有了,甚至連“後傳跟上”的口令也免了,因為人人都怕怕掉隊,落於敵人手中。
但越急越怕越出問題。
前行的隊伍被懸崖擋住了去路,退回換個方向同樣遇到了懸崖,只好掉頭原路返回。
這恰好進入了敵人彈炮的轟炸範圍,再加上側翼敵人的步兵衝擊,原本井然有序的建制頓時亂套了。
我是編輯部佇列的最後一名,可急走緊跟還是被後面的人擠到了路邊。不料,踩塌了溝邊,一下滑到了七八米深的溝底。
等我清醒過來,本能地張口想呼救,但口乾嗓子啞,嘴張得老大,就是喊不出聲。
我拔出了3號手槍又要鳴槍,可此時鳴槍,恐怕會驚嚇到撤退的隊伍,黑暗中極有可能被當做敵人,遭到亂槍射殺。
唯一的辦法只能原路爬上去,但溝坡的沙土發滑,四周也沒有能借力的樹木和雜草,我爬了幾次,每次都又滑回了溝底。
這時,後面敵人的槍聲越來越近了,都可以隱約聽到他們的吆喝聲,某一瞬間,我甚至有了結果自己的念頭。
因為敵人一旦靠近,我那把三號手槍自殺身亡倒可以,對付人手自動武器的敵人一點兒用處也沒有。
如果被敵人打死還好,但若當了俘虜,這就意味著投降,活著回來一輩子被人瞧不起,那還不如死了好。
我想了又想,跟敵人正面較量,死了那叫死得其所,讓我一槍不放就結果自己,老子我絕不幹這種傻事,但一個人藏在這,不被敵人活捉也得活活餓死。
想來想去,我既不想在撤退途中窩窩囊囊地自盡,更不想當俘虜,只要一息尚存我就得爬出去。
我用盡全身力氣開始攀爬,爬一步退半步,也咬著牙死命地爬,終於爬到了離溝崖一米處,竟然發現有根下垂的樹枝。
天無絕人之路,我一把夠了上去,突然,“咔嚓”一聲,虎口粗的樹枝與樹幹裂開了。
如果樹枝完全斷裂,我掉進溝底即使不被摔死,也得摔殘,除了自殺就真的沒有活路了。
這時,我真的想鳴槍了,可已經無法騰出手掏槍了。
千鈞一髮的危急時刻,路過的報社電臺的臺長發現了我,急忙將我拉了上去。
等跑到了相對安全的溝北,我才想起來感謝臺長:“如果你剛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過去了,我就沒命了。”
“哪能啊!即時不認識也不能見死不救,何況我們是戰友啊!”
我至今記得臺長,身材魁梧,有張憨厚黝黑的方臉,待人十分謙和。
這時,王文之編輯過來,一把奪下我的乾糧袋說:“再晚回來一會兒,就找不到我們了,你在我前面走,我關照你。”
山路越來越難,許多險峻地段,都是王文之把我拽上去的,沒有他我肯定再次掉隊。
到處險石林立,坑坎遍坡,許多陡坡足有七八十度,只能四肢落地往上攀登。
大家心裡明白,無論再陡再懸都得爬,除此之外,已無路可退。
夜裡的山坡上到處都是人,根本沒有隊形可言了。
戰士們不光要自己爬,還得拉戰馬,戰馬身上的行裝都卸掉了但還是爬不上去,戰士們只能前面拉後面推,硬把馬拽了上去。
軍保衛部幹事吳明,揹著全軍僅有的兩個檔案箱爬山,首長交待,他犧牲了檔案也不能丟。
按照保密條例,除了吳明誰也不能接觸檔案箱,就連保衛部長也只能眼睜睜看著。
許多難走之處吳明都要先搬一箱上去,再回來搬另一箱,他的肩膀和脖子上的皮被磨掉一層。
中途,他累得坐在地上,失去理智地哭了。一個堂堂的營級幹事就這麼當眾哭起來。
後來,我才知道,吳明不是因為累因為餓而哭,而是為27軍陷入如此窘迫的困境而哭。
原本27軍是打了勝仗啊,怎麼會如此狼狽不堪。
想起長津湖戰役,美陸戰1師戰鬥力那麼強,都被我們追著打,現在倒好,讓敵人追得躲進山裡逃命。實在是冤枉和窩囊。
敵人派出的“特遣隊”,跟我們之前的尖刀突擊隊一樣,也是要快速穿插、分割我們的大部隊,為了求快,並不理會我軍的零星人員。
5月25日凌晨2點,軍機關越過了高山,來到了另一座小山上臨時休息。
一聽說要休息,我只想倒地睡覺,可我掉隊掉怕了,就和王文之挖出來一個小溝,鋪些樹枝,擠在一起打瞌睡。
剛睡著沒幾分鐘,王文之又把我弄醒了,說敵人靠上來了,趕緊轉移。我有點發毛,彷彿還在做夢。
剛睜開眼睛,敵人的幾發炮彈就在附近爆炸了,我的困勁瞬間被炸沒了,爬起來又是一陣急行軍。
原來剛才的臨時休息,是偵察分隊在選擇突圍路線。
敵人的穿插分割之下,此時的三八線已經是敵中有我,我中有敵。
軍機關只能邊偵察、邊轉移,那兒安全就往那兒走,不分白天黑夜,能走則走,不能走則停。
記不清翻過了多少座大山,也記不清穿越多少次敵人活動的公路,我只知道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戰場上的局勢變幻總在一瞬間,勝利的前提是要先活下去。
這次全軍轉移中,糧食供應已經完全中斷。
車輛都被抽調去搶運傷員,炊事班無糧做飯,全靠每個人自挖野菜,自採樹葉,自己想法搞吃的。
飢困交加中,許多人已體力不支。
一天夜裡,軍部正沿公路向北轉移,在敵機的照明彈發出的亮光中,我發現有幾匹馬拉大車由北向南奔跑過來,想迅速逃出敵機的襲擊圈。
由於馬跑得太快,道路又不平,大車顛簸得厲害,車走之後,路面上掉落了一個黑乎乎的東西。
我估計是一雙鞋子,正好我的鞋子不中用了,就跑去弓腰撿了起來。
沒想到,竟然是一條鹹巴魚乾。
我心中大喜,這可是我們膠東人最愛吃的東西,每到漁汛季節,總要醃一些,以供常年食用。
入朝以來我從未嘗到鮮魚的味道,現在能撿到鹹魚幹,那真是天大的福氣。
興奮下我竟忘記了防敵空襲,看到馬車跑遠後又掉下了兩條魚乾時,我想也沒想就豁出去了。
藉著照明彈的光亮,向南跑出十多米,將另兩條鹹魚幹也撿了回來。
我剛離開公路向一側的山溝裡跑,空中的敵機就開了火,機槍子彈在公路上爆起一串串煙塵。
我邊跑邊想,如果這趟死了也算沒做餓死鬼,俗話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我既不是為財,也並非貪食,實在是因為肚子太空虛了。
或許是老天可憐我,又給我開了後門,讓我又一次幸運地逃過了敵機的密集掃射。
第二天到達宿營地後,報社機關的炊事班仍無糧可做,讓大家各憑本事自給自炊。
我靈機一動,昨夜撿的那三條鹹巴魚乾,再加上每人乾糧袋內的少許白麵,湊一湊可以包一頓餃子吃。
包餃子沒有菜,就用野菜代替,沒有炊具,我們就用小刀當菜刀,刻木棍當擀杖,木板當面板,用瓷盆當鐵鍋下餃子。
這頓我豁出命去撿來的“餃子”,可以說是在這場大轉移中最幸福的一頓飯了。
要說在部隊轉移中,最危險、最困難的是誰,那一定是傷員。
27軍當時共有三千多名傷員,許多剛剛負傷,急需治療搶救。後勤部當機立斷,將有限的運輸車停運糧食三天,先把傷員搶運出來救治。
醫院多是弱小的女同志,還要接收傷員,敵機又轟炸……特別是敵人實行大規模反撲後,更增加了搶救傷員的困難。
他們每日經過大半夜的艱苦跋涉,到達宿營的山溝裡後,可以說是一天最疲憊的時候。
然而,這時從前方運送傷員的汽車才趁著夜色到達救治站,醫院的同志們轉眼又要投入更緊張的戰鬥:接收和搶救汽車運來的傷員。
由於就地搶救會遭到敵人的空襲,汽車又無路把傷員直接運到山溝裡去,無奈,只好把傷員抬下汽車,一個個背到山溝裡去,然後才能展開搶救和治療。
背傷員,對醫院的女護士來說,體力是大問題。男性傷員年齡、體重都比女護士大。而女護士最小的只有十六七歲,最大的也不過二十剛出頭,都是妙齡少女。
她們面對著這些比她們重的傷員,開始也有點憷頭。但一看傷員痛苦地在等待著搶救,就什麼也顧不得了。
一整夜的進行軍,姑娘們已經近乎虛脫,但沒有一個人停下休息,一氣不歇地從汽車上將傷員抱下來,又一個個背在身上,用盡全身力氣向山溝裡走去。
年輕的女孩們累得臉色一陣發白,一陣發紫,路上有人幾次差點暈倒。有時剛把傷員背到安置地點,就昏過去了。
醫院院長看到這樣的場景,勸她們休息,但沒過一會,就又看到她們忙活的身影。
我到醫院採訪時,見此情景,也加入了背傷員的行列。
剛朝運傷員的汽車走去,老遠就聽到車上有人在吵吵什麼。靠近一看,原來是一名傷員死活不肯下車。
這是一名年輕的戰士,腿部負了重傷,傷口包紮處的鮮血還在外滲,白色繃帶被染成了一片暗紅。
大家好不容易把他抬下車來,他又死活不讓女護士揹她。他說:“我已經快不行了,請不要把我背到醫院去了。”
護士們動員他說:“你的傷口需要儘快動手術,否則會有生命危險。”
這位戰士一聽生命有危險,神態反而平靜下來,他說:“那正好,就乾脆不要揹我了。”
我很奇怪,這位戰士看樣子才十七八歲,臉盤身材長得也英俊,只是由於傷口出血過多,面部顯得蠟黃,兩眼深深陷了下去。
他的傷口並不致命,為什麼拒絕救助呢?
女護士勸阻無效,無奈對我說:“孫記者,你看他不讓背怎麼辦?”
“我背。”我說著就對這位戰士作了一番動員。看得出來我的動員並未打動他的心,但總算老老實實讓我背了起來。
我揹著這位戰士邊走邊問:“你為什麼不讓女護士背,是害羞嗎?”
我察覺他的頭搖晃了幾下,然後深沉地說:“孫記者,不瞞你說,我不是害羞,是我的傷太重,反正活不成了,何必……”
我聽到這裡,越發覺得不對頭。看他的傷勢,只要及時止住血,還不至於有生命危險。那他為何說活不成了呢?
我敏感地意識到他有輕生的念頭。經我再三追問,他終於說實話了。
原來他除了腿部負重傷之外,生殖器也被飛彈片削去了。
我很同情戰士的不幸,雖然一路給他說了很多鼓勵的話,但我真不知道他聽進去了沒有。
當把所有傷員背到山溝安置停當後,大家已經是筋疲力盡了,可是誰都沒有睡意。
醫生馬不停蹄地檢查傷員的傷口,清創、包紮,需要動手術的馬上動手術。簡單的在樹林就地搭土手術檯,蒙上毯子、白布就幹起來。
複雜的手術在樹林裡做光線不足,在露天又難防空襲,就得構築臨時手術洞、甦醒室,洞內留個天窗,靠天窗射進的陽光照明。
手術治療結束以後,護理組的任務仍很繁重。
許多重傷員生活不能自理,女護士們就親手給他們洗臉、刷牙、洗腳。有些自己大小便都很困難的傷員,女護士們就給他們解褲子、穿褲子,包括擦屁股。
姑娘們不嫌髒,也不怕累,一直等所有傷員都治療結束,休息了,才肯在傷員身旁閉一閉眼,打個盹。一聽見有傷員的喊聲,就又馬上醒過來。
我正在抓緊時間進行採訪之時,突然聽到了一個不尋常的訊息,一位急救傷員的輸血針頭脫落在地,因黑夜視度不良,護士沒有及時發現,結果傷員死了。
聞訊,我立即趕到現場。那位的值班護士正在受批評,滿眼的淚水閃著自責的亮光。
我彷彿有個不好的預感。靠近一看,果然是他。
我從他的上衣口袋內發現了一封沾有血跡的簡訊:
“秋紅:
我已經死了,但我死而無憾,因為我沒有給祖國丟臉。我們的山盟海誓已被戰爭毀滅。死是我圓滿的結束;但願你能幸福地活下去,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李成功1951.5.26”
他就是那位被我背來的戰士。
我看了信更明白了,原來他是不願給未婚妻增加痛苦,而執意結束生命的。
這不僅是一個年輕生命的結束,更是一個美滿家庭的毀滅。
院裡決定將李成功的遺體掩埋在山坡上,大家在面向祖國的方位挖了一個墓穴。沒有棺木裝殮,護士們就在他的身上多纏了一些白布。
他死後一直睜著眼,但臉上沒有痛苦的表情。
人們輕輕抬起他的遺體,慢慢地向他的墓穴處走去。隊伍裡沒有哭聲,都在默默地走。
我找了一根青松樹幹,用木刻刀削成一塊小木碑,在上面刻了“志願軍李成功烈士之墓”十個字。
有位軍醫從別處移來一棵小小的青松栽上了;兩個女護士從周圍的山坡上採來些金達萊花,放在墳頭。
這一切都是在沉默中進行的。有些話太重了,是說不出口的。
這件事情當時不能見報,我也沒有寫。但是這位戰士的名字,他的痛苦,他的樣子,一直銘記在我的心中。
許多人會講,戰場上的危險主要是進攻,其實不然,轉移和撤退的危險半點也不亞於進攻。
場面之壯烈也一點不遜色於正面戰場。
5月27日,軍機關脫離敵人大炮封鎖線的當天上午10點,聽說斷後的部隊也突圍出來了,我急忙跑到了隱蔽的後山坡觀察。
他們是真正的英雄啊,沒有這些一線部隊死命阻擊,我們軍機關不是槍下鬼,也得被活捉當俘虜。
山腳下有一條橫貫東西的公路,我有意在靠近公路的地方,觀察下方公路上轉移部隊的情況。
山高谷深,轉移的隊伍擁擠不堪,隊形紊亂,著裝不整,步履艱難,但都緊跟佇列不敢落下。
公路北側幾間被炸燬的小屋,只剩下一堵矮牆,有十幾名戰士坐在牆根,背靠牆壁,兩肘抵頭,像是走不動了在休息。
幾架美國戰鬥機又飛來掃射了,公路上的撤退隊伍,包括靠牆坐著的人,竟然無一人臥倒隱蔽,無一人逃離公路。
人們就這麼在彈雨中向前挪動,打死誰,誰就倒下,未打死者照常向前走,彷彿這些人都不想活了似的,對待敵機的掃射毫無反應。
他們連著幾天沒有吃飯、睡覺了,他們的血肉之軀就是最堅固的防線。
我目不轉睛地盯著公路上遭到空襲的部隊,每一幕都觸目驚心。
生還計程車兵後來採訪中告訴我,他們都清楚空中有敵機突襲,身後有敵人追擊,但他們不能停,不能躲。
因為有任務在身,要趕快到前面有利地形去構築工事,交替掩護後面兄弟部隊的轉移,徹底擋住敵人步兵的追擊。
所以,任憑敵機怎麼肆虐,部隊也不能停下來隱蔽,只能冒著敵機的火網穿行。
他們還說,仗打到這個份上,死了也是一種幸運。
當時我不理解啊,直到44年後的1995年,有一天我看到了安徒生的名言:
“在人間的歡樂中,在完成了他對人間的任務後,沒有絲毫痛苦地結束了——死,也是幸運的。”
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官兵們那種近乎空靈的壯舉:你打不死老子,老子就照樣前進!
當時,我也十分清晰地看到,一名美機駕駛員也歪著腦袋在看下面,那個表情,一看就是吃驚的樣子。
這分明是一場裝備與實力相差懸殊的戰鬥,而戰爭從來就沒有對等。
我腦中突然蹦出一個問題:究竟誰是勝利者,誰是失敗者?
個人只是戰爭這座大山上的一粒沙,在其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不管是部長張樂天,還是士兵李成功,當我們不瞭解他們時,他們的生死於我們是毫無感受的。
但是,此時此刻,我相信,看完故事的每一個人,都在為他們心痛。
因為我們知道了他們的人生,他們的理想,也就知道了他們所為之付出的犧牲。
而這一切,都源自於孫佑傑的記錄。不管他曾經是記錄在報紙上,還是記錄在自己的心上。
孫老讓我感動的是,他的文字沒有高喊的口號,直面戰爭殘酷時,甚至讓人不忍卒讀。
作為一名隨軍記者,他首先是一名戰士,在生死麵前,再振奮人心的話都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他比誰都清楚,戰場上的每一個士兵,都只是想活著回家而已。
孫佑傑是幸運的那部分人,而樂天、成功永遠留在異國冰冷的土地上,至今還不能魂歸故里。
這是孫佑傑老兵戰地紀實的完結篇,謝謝他。
編輯:趙斯卡 羅伯特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