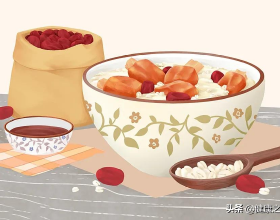博經道長此時已經年逾花甲,卻是黑髮如墨,臉膛紅潤,腰桿筆挺,動作敏捷。猶如三十歲的後生。看了楊令公寫給師父的書信,不禁想起了當年的情景,也就唏噓不止。猛然想到出家人應該六情斷絕,不該如此兒女情長,便自我解嘲道:“為師既不能割斷六情,可見絕不能超凡入聖。既然如此,咱們師徒倒不如任情適性,做些凡人該做的事情吧。如今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六郎、七郎雖然是來投奔先師真如道長,而先師已經羽化,也不能叫你們白跑一趟。我的本事雖然不濟,總算你們的長輩,叫我一聲師父也還說得過去。不知二位公子以為如何?”楊六郎趕緊說道:“家父的師兄,本來就是我們的師伯;況且家父常常懷念師伯的情義,羨慕師伯的武藝,據說家父的大半武藝就是得之師伯的傳授。承蒙師伯願意收我弟兄為徒,我們感激還來不及呢,哪有不願意的道理?如果師伯不收留我們,我們還有什麼臉面回去見父母呢?”
博經哈哈大笑道.“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我這賢侄比他父親小時候還聰明幾分呢。算我運氣,又收了兩個高徒。”楊七郎原以為出家人一定是道貌岸然,枯燥乏味,今見博經道長十分有趣,心中暗暗高興,更願意做他的徒弟了。於是六郎、七郎向博經磕了三個頭,算作拜師之禮。
俗話說:“忙裡光陰易過,閒時度日如年。”楊六郎和楊七郎學藝既很忙碌,忙中又有樂趣,所以三年時間眨眼而去。六郎時已十八歲,七郎也有十六歲了。論武藝,弟兄二人難分高下;比力氣,六郎卻要甘拜下風哩。七郎似乎得天獨厚,年雖弱冠,身高卻過七尺,渾身肌肉隆起,膂力大得驚人,不但同齡人望塵莫及,就是壯年漢也相形見絀。連武當山上那口古井旁邊倒栽著的那一根碗口粗的鐵杵,足有八百多斤,七郎也能拔得起來。
楊六郎和楊七郎學藝已滿三年,既怕父母思念,又想早日為父母分憂,只得與師父和眾師兄告別,各騎上自己的戰馬,各懸寶劍一把,灑淚而去。
汴梁繁盛圖
從武當山到代州,本來中經洛陽,再向北走,是一條最近的直路。可是一入河南地界後,楊七郎卻向楊六郎央告道:“六哥,聽說汴梁城四通八達,好生熱鬧。咱們住在山後,難得出門,今日何不前去看看?反正也繞不了多少路。”
楊六郎猶豫道:“如今汴梁是大宋的都城,咱家又與宋兵多次交戰,萬一被他們認了出來,如何是好?”楊七郎道:“汴梁五方雜處,人山人海,咱們的名字又沒寫在臉上,只住一天就走,哪裡就那麼巧呢?好六哥,咱們就去一趟吧。”楊六郎被他纏不過,自己也有點心動,略一思索,便說道:“去也可以,只是你要依我兩件事。”七郎滿口答應說:“只要你答應去,莫說兩件,二十件、二百件也依你。你說,你說。”楊六郎道:“頭一件,你要聽我的,我要你怎樣,你就得怎樣。”楊七郎笑道:“這算得了什麼?我啥時候不是聽六哥的?”楊六郎又道:“第二件,咱們得換個名字,我叫木易六,你就叫木易七。”楊七郎道:“依倒是依你,不過小弟不明白,世上有的是現成名字,什麼不好叫,為何偏偏要叫這麼個古里古怪的名字?”楊六郎道:“你總是不動腦子。這叫做拆字法,‘楊’字折開來不就是‘木’、‘易’二字嗎?如此則既瞞了別人,又不改本姓,豈不是好?”楊七郎一樂,連連說道:“六哥,真有你的,果然妙不可言。小弟佩服得五體投地,怎敢不聽你的?”於是二人拐向東北而走。
此時正是夏末秋初,這一年的秋老虎又格外厲害,忽晴忽雨,十分悶熱。不過一早一晚,倒還涼爽。因此楊六郎和楊七郎早晚趕路,中午歇腳。這一天,太陽好容易藏到了西山背後,卻還留下滿天彩霞和滿地餘熱,幸而吹起了習習涼風。這時候,楊六郎和楊七郎趕到了汴梁城的天波門外。二人停馬觀看,果見城高河深,吊橋高架,十分雄偉。城門口肩挑負販,驢馱馬搭,川流不息,更為熱鬧。緩響來到城門之前,只見一側貼著一張紙,有幾個人在那裡仰頭觀看。楊六郎和楊七郎也立馬停韁,站在人們後面看去。原來是一張皇帝的聖諭,寫的是朝廷為了一舉剪除楊家將,踏平太原城,特命當朝樞密使潘仁美之子潘虎在酸棗門外擺設播臺,以期切碰武藝,招募天下壯士。凡有一能一技,必當量才錄用。期限只有一月,萬勿錯過良機。楊七郎看罷,不禁心中大怒,真想上前將它撕得粉碎。猛然想到這是宋朝的都城,又答應過六哥絕不輕舉妄動,這才極力忍耐,然而面孔已經憋得發紫。楊六郎見他臉色大變,生怕惹出是非,急忙使了個眼色,頭裡便走。楊七郎只得緊緊跟隨。
汴梁城內景象
二人來到城裡,一路穿街過巷,一邊左右觀看。但見房屋挨挨擠擠,行人熙熙攘攘,茶樓連著酒肆,店鋪滿目琳琅。楊六郎暗想:“看這汴梁景象,倒與太原有天壤之別。況我一路所見,村村雞鳴狗吠,滿野豐收在望,也與俺河東大不相同。可見這宋朝的趙姓皇帝倒有治國的能為。神州自古一統,中華本為一家,只因人心各異,以致你爭我奪,天下大亂,黎民塗炭。倘能江山再歸一統,百姓復見太平,那時解盔卸甲,牧馬南山,該有多好。”一路胡思亂想,忽見騾馬大店一處,便與七郎進去住了。
晚飯之後,店小二送進茶來。楊六郎是個有心人,見他倒也斯文,便與他東拉西扯,問長問短。恰好這個店小二是個多嘴的主兒,你問他一句,他便告訴你十句。楊六郎暗暗高興。說來說去,便扯到城門口那張聖諭上去了。
楊六郎問道:“這個潘虎到底有多大本事?為何朝中有那麼多能征慣戰的名將,皇上卻偏偏要讓這個潘虎來擺擂?”店小二說道:“說來話長,客官如果不嫌絮煩,小人倒可給你講個詳細。”楊六郎趕緊道:“客居無聊,天氣又很悶熱,早睡也睡不著。小二哥若肯相告,倒可使在下弟兄二人長些見識。”說罷,便給店小二斟了一碗茶,並遞給他一把蒲扇。
店小二謙虛了幾句,便搖著扇子,開口說道:“二位客官大概也知道,當今皇上原本是周朝的一個大將,官居殿前都點檢之職。後來周世宗柴榮駕崩,他的兒子柴宗訓接了皇位。這柴宗訓年僅七歲曉得什麼國事,凡事都由趙大將軍做主。這趙大將軍見他寡母孤兒,如何能治理天下,便輕輕地把那皇位搶了過來,自家坐了上去,從此改朝換代,成了大宋趙家的天下。人人都說當今皇上不該搶那皇位,小人卻不以為然。有道是:“皇帝輪流轉,明年到我家。遠的俺不知道,單說這幾十年中,光這汴梁城已經換過幾姓皇帝了。別姓既然可以當皇帝,趙姓為何就不可以當?況且俺親眼所見,當今皇上文能治國,武能安邦,在位不過幾年,就滅了好幾個小國,安撫了黎民百姓。就拿俺這汴梁來說,從前兵荒馬亂,如今十分太平。只有一般不好,不該寵信那潘仁美老賊。”
潘仁美
店小二說到這裡,端起茶碗喝了幾口。楊六郎乘機插問道:“照老哥說來,當今皇上可算十分英明,為何又寵信潘仁美呢?準是潘仁美有過人的本領吧?”
店小二不慌不忙,繼續說道:“客官年紀輕,難免世故不深。有道是‘出頭的椽子先爛’,又道是‘好話人人愛聽’。因此君子常常失意,小人往往得志。當今皇上從前本有十個結拜弟兄,個個武藝高強,彼此親同手足。他們同當今皇上打天下時,都立下了汗馬功勞。可是當今皇上做了皇帝以後,大約是怕他們居功自傲,也學他的樣子,搶了他的皇位,所以不知怎麼一來,有的罷了官,有的降了職。潘仁美並不是當今皇上的結拜弟兄,武藝也十分平常,說不上有甚汗馬功勞。不過他倒有一種本領,舉凡溜鬚拍馬、順水推舟、笑裡藏刀、落井下石等等,他倒是不學自會,樣樣精通。況且潘仁美武藝既不高,功勞又不大,也就沒有搶奪皇位的危險。大概當今的皇上就是看上了他這兩條,才對他十分寵信。無怪乎古人說:‘曲如鉤,定封侯;直如弦,死道邊。’”
楊六郎聽他說得頭頭是道,出口成章,實在不像一般的店小二,不禁有點疑惑,便問道:“想不到老哥職業雖卑,學問倒很淵博。敢問老哥,恐怕坐過寒窗,讀過詩書吧?”
店小二不好意思道:“小人只顧說得高興,倒不料露出了自家的本相。不瞞客官說,小人本是書香門第出身,只因生不逢時,兵荒馬亂,所以雖讀了幾年書,卻是一事無成。又逢契丹進人汴梁,滿城被洗劫一空,敞寓也不例外。小人僥倖逃得性命,卻是無以為生,便淪落為傭工,做了這伺候人的店夥。如今雖然天下初安,然而小人年紀已大,舊業難以重操,只好苟延殘喘,了此餘生罷了。小人以此為羞,所以從不對人提起,不意被客官識破,只好直陳,想來不至恥笑吧?”
楊六郎聽了,不禁心中惻然,急忙說道:“老哥說 哪裡話來。人之順逆,不由自主,而在時運。運來則飛黃騰達,運去則難免淪落。古往今來,莫不如此。老哥生不逢時,以至大才不得施展,只能令人浩嘆,豈有恥笑之理?在下有眼無珠,方才倒不曾動問尊姓大名,老哥可肯下告?”店小二見楊六郎毫無鄙薄之意,便欣然說道:“賤姓黃,本名慕孔。後來淪為賤役,以為有辱聖人,便改名悔生,無非悔恨生而為人之意。小人斗膽,敢問客官與令弟高姓大名?”
楊六郎不禁為難起來:若說假姓假名,似乎不合情理;若報真名實姓,又怕萬一出事。只得暗暗祝告道:“皇天在上,恕我楊六郎對朋友說一次謊話。以後但有機會,定然謝過。”於是說道:“敝兄弟複姓木易,並無大名,只以排行相稱,在下為老六,敝弟為老七。”黃悔生道:“尊姓雖屬少見,卻也偶見史書記載,北魏時就有木易於其人。”
楊六郎暗驚道:“此人學問果然不小。我原以為這木易的複姓是我的胡謅,原來倒確有此姓。這倒更妙,別人更不會想到我們姓楊了。”楊七郎在一旁聽了,卻暗自發笑道:“想不到這麼個牛鼻子店小二,肚裡的墨水倒有一缸。可惜你的墨水喝得太多了,反而想不到俺楊姓也可以變成木易呢。”
後來楊家歸了宋朝,搬到汴梁來住,楊六郎到底找到了黃悔生,對他說明了今日隱姓埋名的緣故,並給了他三百兩銀子,讓他養老送終,這才把這樁心事放下。此是後話,表過不提。
當時彼此周旋了一番,黃悔生又接著說道:“潘仁美有三個兒子:長子名叫潘龍,次子就是潘虎,三子名叫潘豹。潘龍是個庸才,雖沒有什麼作為,倒也沒什麼劣跡。潘豹年紀尚小,剛剛送到少林寺去學藝。眼下惟獨潘虎最壞。他也曾到少林寺學過三年武藝,回來後就像他去過一趟玉皇大帝的寶殿一般,把他興頭得不知姓什麼了。殺了人,就像捏死只螞蟻。至於打人罵人、欺男霸女之類的事,更是家常便飯。因此對著窗戶吹喇叭——惡名在外,—座汴梁城,無人不知,無人不罵,都說他是一隻吃人不吐骨頭的惡虎。要說他的武藝,確實倒也不同尋常,比如打擂十幾天來,死傷在他手下的已有二十幾個。你想,他本人既有武藝,又仗著他老子的權勢,這不是如虎添翼,誰還敢惹他?”
楊六郎乘他停下來喝茶,又問道:“在下有二事不明。聽說少林寺的規矩是凡入寺中學藝,必須剃髮為僧。為何潘仁美的兩個兒子都到那裡去學藝?難道他們也都做了和尚嗎?這是一件不明。在下見當今皇上的聖諭上說,朝廷所以命潘虎擺擂,為的是切碰武藝,招募天下壯士。怎麼潘虎倒把他們打得死的死,傷的傷?這豈不有忤聖旨?難道當今皇上都不知道嗎?這是又一件不明。老哥可也知道這其中的原委?”
黃悔生嘆道:“頭一件是世情冷暖,可想而知。第二件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客官聽小人慢慢講來。少林寺確有客官所說的那種寺規,不過只用於平民百姓的子弟,倘若達官顯貴的子弟也要去學藝,那裡的長老可就忘了他自家的寺規了。這倒也不能全怪長老,因為僧徒雖然號稱超脫紅塵,其實也還是皇帝的子民,要是得罪了達官顯貴,就連和尚也恐怕做不成了。所以寧可破了寺規,也不能打碎飯缽。以潘仁美的權勢,送自家的兒子去學點武藝,長老別說不敢剃人家的頭髮,恐怕就連一根汗毛也不敢動呢。至於說到眼前擺擂一事,如果能像聖諭上說的那樣,倒也未嘗不是件好事,只因為用人不當,以致好事變成了壞事。此話怎講?說來一言難盡。近來聽說皇上貴體不適,三天早朝,倒常有兩天停舉。潘仁美老賊看準了這個機會,才想出了這擺擂的毒計:一來讓兒子顯顯本領,好在朝裡討個大大的官做;二來毀掉些天下的壯士,將來也少些爭功的對手,好讓他父子獨霸朝政。於是上了一本。皇上不知是計,也就恩准,並出了一道聖諭,限定擺插一月。此計雖未完全得逞,卻已壞了二十幾條好漢的性命。倘若完全遂了潘家父子的心願,不是潘家一手遮天,便是天下重新大亂,夙夜細想,令人不寒而慄。此非小人杞人憂天,實乃路人皆知。但願蒼天有眼,使潘家父子不得好死,使黎民百姓免遭塗炭。”
黃悔生說到這裡,戛然而止,連連嘆氣。楊六郎和楊七郎也被他感染,默默無言。停了一會兒,黃悔生也就告辭而去。楊七郎自從在天波門外看了那張皇帝的諭旨,早就怒火中燒,有了個主意。只因沒有機會與六郎商議,所以忍而又忍,一直聽六哥與黃悔生閒談,不作一聲。好容易等到黃悔生告辭而去,再也忍耐不住,向楊六郎說道:“六哥,這趙家皇帝專與俺楊家作對,那潘家父子又作惡多端,俺先去宰了那潘家的狗崽子,出出俺的鳥氣。”楊六郎急忙攔阻道:“還不快快住嘴,這是何等地方,由你大呼小叫。只憑匹夫之勇,焉能成事?我也有了個主意,你把耳朵伸過來,讓我說給你聽。”楊七郎趕緊把耳朵湊了過來;楊六郎便對他唧唧噥噥了好一會兒。楊七郎尚未聽完,眉頭已經舒展,大嘴也咧了開來。等到聽完了,果然一言不發,只是捂著嘴巴暗笑。弟兄二人計策既定,也就熄燈歇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