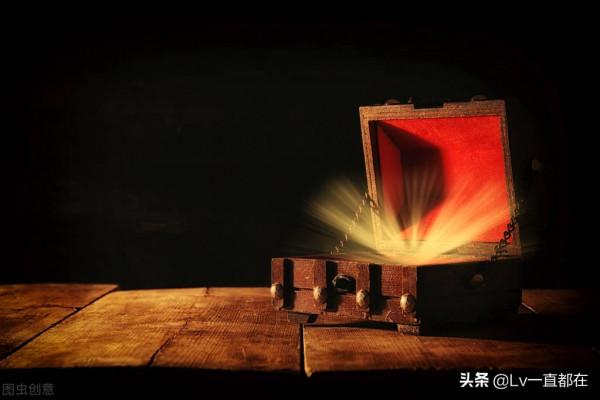來自20世紀“世紀偉人”的一封信,熔斷了本應束縛在戰爭眼前的一道枷鎖,它不經意間流露出的兇惡利用著這位心憂蒼生的科學家。 ——題記
科學,本不應被如此揪扯著推上歷史舞臺;舞者,在踏出舞步的那一刻可能便已知曉,厚重的幕布因他而開啟。
此舉本是好意
核試驗的最新進展驚醒了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工作的愛因斯坦。
他很快看出了其中的深遠意義,於是將一封信呈送到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手上。
在信中,他小心翼翼地表達了自己對這項新發現的看法,用科學家犀利獨到的眼光捕捉著角落裡即將釋放的潛力,同時希望羅斯福總統將推進工作派給一個沒有官職在身的人,讓他來製造這樣一名“頑劣的孩童”。
身為猶太人的愛因斯坦在希特勒的瘋狂壓迫下來到美國,他絕不允許威力如此巨大的武器落入這個“瘋子”的手裡,給慘痛的時代再次籠罩上一層恐怖。
羅斯福總統在白宮內默默地研究著來信,他額頭上沁出的汗珠兒聚集在緊皺著的眉頭,他也感到了這扇緊閉的大門後隱藏的威力,變得舉棋不定。
但當他想到德國正在加緊研製原子彈時,一陣寒意立即從他的身後襲來。
經過一星期的全面考慮,他最終對來信做出了肯定回答,發出了進行核試驗研究的指令,並將實驗室設在了芝加哥大學。
“舞者們一齊邁出了舞步,渴望緊跟時代的音符。”
魔盒就此開啟
費米的核反應堆建成,製造原子彈專案被加速提上日程,“曼哈頓計劃”應運而生。
奧本海默集結了費米、玻爾等人,組成研究團隊,透過夜以繼日的工作,鑄造出了開啟魔盒的鑰匙。
在計劃開展後的第二年零七個月,這個“新生兒”便嘗試揮出一記重拳:一聲巨響過後,一團巨大的火球升上天空,末日的景象浮現在每個人面前。
費米別出心裁地將一把碎紙片從頭頂上方撒下,強烈的衝擊波將它們帶起,他如炬的目光緊隨著碎紙片飄落的軌跡,斷言:
“這顆原子彈的威力相當於兩萬噸TNT炸藥釋放的能量。”
而事後儀器測量的結果和他的預言只差毫釐,在場的所有人都被“魔盒”開啟瞬間的威力震撼了。
此時的德國已經投降,日本法西斯也處於崩潰邊緣,墨西哥州基地中的兩顆原子彈本已經再無使用的必要。
但羅斯福總統的突然離世,把所有不確定因素放到了新上任的總統杜魯門身上。
由於“曼哈頓計劃”的嚴格保密,這位新上任的總統在上任當天晚上才瞭解他之前從未聽說過的核武器,一向看待事物非黑即白的他拿到了核武器便急切地想加以利用,以此改變戰爭的走勢。
隨後,杜魯門簽署了對日投放原子彈的命令。
“領舞者沉浸在躍進的樂章中,卻忘記了微笑,掛著思索中的憂鬱。”
災難滿目瘡痍
之後發生的一切,世人皆知。在廣島與長崎投下的兩顆原子彈,爆炸的強烈光波使成千上萬人雙目失明;放射雨使事件的經歷者與死神提前打了照面,留給他們的只剩下夢魘;頃刻間街道化為烏有,無數無辜百姓消失在這道光亮中……
誠然,這一切瓦解了日本法西斯抵抗的最後一丁點兒幻想。但是,將徹頭徹尾的罪惡擊得粉碎的代價是那些無辜的人的生命。
科學,在那一刻也被蒙上了血色。得知訊息後,愛因斯坦陷入了深深的自責中,這位“領舞者”對自己未能阻止原子彈的研發而內疚不已。
在面對記者的採訪時,他說了這樣一句話:“上帝呀,我有罪!”參與計劃的研究人員也大多陷入了心靈的泥沼。
潘多拉的魔盒被他們以科學的名義開啟,將其關閉已是天方夜譚。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研製氫彈仍是政客們追逐的目標,掌控權力的標籤被貼在氫彈的外殼之上。
“狂熱的粉絲一哄而上擁擠在舞者身前,領舞者則選擇默默退場,把這場不完美的演出封存於記憶。”
未來去往何地
奧本海默沒有選擇迴避世人的目光,更沒有妄想從氫彈上收穫名利,他拒絕緘口不言的縱容,毅然決然地踏上了強烈反對核武器研製的道路。
在我看來,他是在世人彎曲的目光中正視了自己,是那句“我們的手沾染了鮮血……”
讓他寧願用盡綿薄之力,以為那是對科學真諦的救贖。
在生命的最後時光裡,奧本海默淡然面對莫須有的罪名,經歷監禁和各種限制,但他一直堅持自己的態度——禁止核武器,將一切放置於崇高的道德地位,從而贏得了世界的敬重。
可憎的不僅是對待科學彎曲的目光,還有對科學精神的漠視。
時間總會讓更多人幡然醒悟,而這些勇士更願意燃燒自己,提前驅散黑暗,帶來光明。
在二戰後的軍備競賽中,對核武器的研究與生產已經嚴重威脅到了世界人民的安全。
此時,和平好似離弦之箭不得不發,《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在聯合國的提議與磋商下誕生。“人海的喧囂逐漸散去,舞者不再盯著舞臺的一隅,周圍好像看到了光!”
1957年蘇聯奧布靈斯克核電站的落成,推開了核發展的另一扇窗。
世人被窗外美麗的景色吸引,原本彎曲的目光也重新變得充滿善意,散發著勃勃生機。
美好源自心底
科學以無知之行始,以能行之知終。
放鬆彎曲的目光,以好奇心探索未知是科學探究精神的合理方式。
科學同時具有時代性,因時代而被創造也應該順應時代被利用:科學正如一把雙刃劍,努力將劍鑄造得愈加鋒利,而劍柄向來懸掛於細如髮絲的倫理底線上。
“對科學家來說,不可逾越的原則是為人類的文明而工作。”
如何將科學合理運用,使其造福人類而非帶來災難,這是時代給科學出的難題。
“舞者也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不僅是演出,用表演帶來幸福與美好才是自己舞動的最終命題。”
他們也曾用彎曲的目光視物,但正義的目光最終直透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