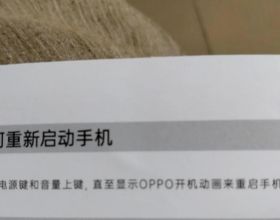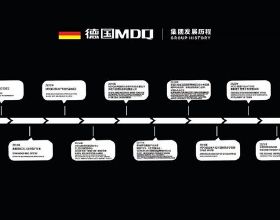任遠被俘了,那年他25歲。
他當時擔任冀東東北情報聯絡站站長,公開身份是中共冀東軍區聯絡部部長,化名劉傑。
他在一場戰鬥中受傷昏迷,被日軍俘虜。
那是1944年10月15日,由於我方情報洩露,日軍裝備精良的獨八旅團包圍了河北豐灤縣的楊家鋪,這裡有轉移途中的冀熱遼特委、行署和軍區機關的幹部戰士八百餘人,日軍兵力數千。
敵眾我寡。敵人有備而來,我方遭遇突襲。
突圍戰鬥中,我方犧牲430多人,被俘150餘人。任遠是被俘者中職務最高的一個。
在突圍戰鬥形勢危急的關頭,任遠請示上級批准後,下令處死了一個叛徒。
任遠也沒有想到,此舉為他被俘後上演無間道埋下一個的伏筆。
求 死
任遠從昏迷中醒來時,發現自己已經被俘。他腦海湧入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我該怎麼儘快結束自己的生命?”
作為一名情報人員,特別是任遠這樣高階情報人員,一旦被俘沒有抵抗住敵人的審訊,失守變節,對組織的破壞影響是十分嚴重的。
當年學習情報課時,老師叮囑過,一個優秀的情報人員,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背叛自己的底線,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價,也要堅守自己的理想。
任遠決心以死來保守情報工作秘密。他在回憶錄中記述了當時的想法:
“軍區重要的內線和上層關係均由我直接掌管,組織一定獲悉了我的情況,地下工作者也一定知道我已被俘。因為我,會不會影響組織的派遣部署,會不會給同志們帶來危險?……我知道,我必須用生命來證明忠誠,免除黨和同志們的牽掛,保全地下組織。”
他的思維十分清晰:
第一,不讓組織以及他“直接掌管”的“內線”和“上層關係”擔心。組織上得知他被俘後,必然擔心他是否能夠經受得住嚴峻的考驗,必然會擔心他一旦失守會交代出這些內線關係。
不僅僅是擔心,組織還可能採取必要的應變措施。按照秘密情報工作紀律,在情報幹部被俘後,必須通知他“直接掌管”的內線關係撤離。這樣做,就會影響到“組織的派遣部署”,給情報工作帶來干擾和損失。任遠認為只有一死,才能消除同志們的擔心,消除對派遣部署工作的不利影響。
第二,敵人是十分兇殘的,在酷刑之下,意志能否戰勝血肉之軀的痛苦,是否能夠堅持到底,萬一出現了挺不住的脆弱瞬間……
任遠還想,即使在清醒的時候可以保持堅強意志,但是在受刑昏迷後,萬一不小心吐露了黨的機密,那將會令他悔恨終身。
第三,敵人是不擇手段的,如果日軍使用迷幻劑之類的藥物,使自己出現意識不能自控的情況,秘密的防線也會失守。
於是,任遠決心赴死。
他給上級領導寫了遺書:
我因重傷被俘,難以脫險。為保護組織,嚴守機密,我決心以死報國。
任遠先是嘗試自殺,結果未能奏效。隨後,由於叛徒指認,日軍得知了任遠的真實身份,加強對任遠的審訊與勸降。
任遠決定命令同監的交通員李永幫助自己以死明志。他把遺書交給李永,要李永到了晚上趁敵人看守鬆懈時,用室內掛手巾的一條麻繩將自己勒死。任遠對李永說:
“敵人已經查明我的真實身份,必然不會放過我,我不可能出去了,為了保護組織,免除同志們的危險,我必須一死,我現在命令你,用那個掛毛巾的繩子,把我勒死,要快。”
李永流淚苦勸:“首長,你不能死,一定會有辦法的。”
任遠在黑暗中摸索著,在牢房的牆壁上寫了“為國盡忠”四個字,然後低聲命令道:“快動手吧!”
但是,李永最後還是手軟了。
李永在幾十年回答外調人員的詢問時說:“任遠是我的領導,年紀那麼輕,又負了重傷,我硬著心將他勒得昏死過去,他下意識地掙扎,我又狠心勒了幾次,實在不忍心將他勒死,手軟了,放手後很久,他才慢慢地甦醒過來。”
任遠最終求死未果。
用 計
任遠被勒昏迷時,身體本能地發生了強烈掙扎,看守聽到動靜,立即將李永拖走,關到了別的牢房。
日軍為防止任遠再度自殺,加強了監管,上廁所都有專人監視。
求死不成,任遠思考下一步該如何與敵人鬥爭,他想起了當年在延安接受情報工作培訓時,潘漢年同志曾經講過的話:
情報人員的使命並不是在被捕之後就告以終結,被捕後要學會在法庭上、在監獄裡同敵人作殊死鬥爭,善於用狡猾的手段對付敵人,當敵人沒有充分掌握確鑿證據時,機智地採取假供、亂供,來應付敵人的審問。
任遠豁然開朗,開始盤算利用敵人迫切想要情報的心理,編造提供假情報,既可保護自己,還能在敵人內部製造懷疑,以敵制敵。
日軍從叛徒口中得知抓住的這個人是冀東軍區聯絡部部長劉傑,大喜過望,專門指派1420部隊宮下大尉、憲兵隊長川上大尉,一起對任遠進行審問。
日軍一心想要從這位冀東地區共產黨情報領導幹部身上開啟突破口,進而徹底摧毀冀東地區的中共地下情報網路。
任遠決定“滿足”敵人的願望。
審訊的兩個日軍軍官都是特務行家,他們想從任遠口中得到的,主要是我方地下組織的人員姓名、住址、身份等具體情報。這些東西,是摧毀情報網路的要害。
這種情報,要編假的,很容易;但是,要不被敵人識破,很不容易。
任遠年紀不大,經驗卻很豐富。他深諳情報活動的特點與門道,瞭解敵方如何鑑別真假情報的心理,瞭解日軍特務機關的內部運作與相互關係,知道對方的軟肋與破綻。
於是,他開始了他的無間道。
任遠的第一步,是編造了一個在偽滿洲的共黨地下情報網。
之所以編造偽滿洲的,因為任遠知道,冀東的日軍特務機關與偽滿洲的日本特務機關,不僅在地域上相隔遙遠,而且在管轄上隸屬於不同系統,各有地域利益,互相聯絡不暢,關係並不密切,甚至存在隔閡與矛盾。
編造偽滿洲的情報網,冀東的日軍一來難辨真假,二來也很難核實。即使要核實,也是環節繁瑣,耗時漫長。在漫長的核實時間裡,任遠相信會有機會逃脫魔爪。
任遠編造的偽滿洲共黨情報網,有人名,有住址,有代號,有建立時間,有聯絡方法、有具體任務。
宮下大尉吃驚不小。他萬萬沒有料到,被日本視為銅牆鐵壁偽滿洲國內,竟然會有如此多的共產黨地下組織。
雖然裡面的內容沒有一個真實的,但是這個假情報網聽上去很詳細,很精確,要素齊全,十分專業,而且是從情報站長任遠口中說出來的,兩個日軍軍官感覺可信度極高。
任遠初步取得日軍信任後,他開始走出第二步:借刀殺敵。
任遠知道,日軍更感興趣的肯定是身邊的冀東共產黨地下組織情況。
對於身邊這個地區的情況,日軍必定掌握得不少,而且近在咫尺核查方便,因此不能像編偽滿洲情報網那樣全是假貨,那樣很難騙過日本人。
這難不倒任遠。他在情報策反工作中,對冀東地區日偽軍的情況瞭解得相當深入。在他的策反物件中,有些是左右搖擺的不堅定分子,有些是偽裝革命抗日、其實反共頑固的鐵桿漢奸。
他決定從這些人裡面,選擇幾個對我危害比較大的,作為“共產黨地下人員”,提供給日軍。
但是,只提供偽軍中的漢奸肯定不足以令日軍滿意與相信。
任遠決定再提供幾個自己掌握的聯絡站地址。他斷定,在自己被捕之後,組織上肯定會按規定立即安排轉移,這些聯絡站的同志肯定都轉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於是,他把這幾個聯絡站的舊址提供給了日軍,日軍按照地址去抓人,雖然撲了個空,但是他們認為任遠的情報是真實準確的,只是共黨跑得太快罷了。
任遠取得了日軍的進一步信任。
任遠在給日軍提供冀東地區情報時,打定主意一定要交代出的一個人,是偽軍駐山海關警備團團長張愛仁。
這個傢伙當了漢奸後,內心也是忐忑不安,到了抗戰後期,看形勢發展對日本越來越不利,就想著找條後路,於是向我方傳信,說有心投降。
任遠專程出面去做他的策反與接應工作,並商定了張愛仁率部起義的時間與具體計劃。
但是,張愛仁隨後發現自己的起義計劃被日方察覺,又立即轉身投向日軍,配合日軍設計騙局,以假起義誘騙我八路軍主力踏入日軍圈套。
按原來約定的起義時間,我主力部隊已經開往預定地點準備接應起義偽軍,但是,張愛仁卻正在幫助日軍向我軍展開包圍。
多虧任遠派出的偵察員及時發現異常,我主力部隊緊急撤退,才使敵人的陰謀落空。
張愛仁臨陣背叛,險些造成我軍的重大損失。
任遠痛下決心,必須除掉這個背信棄義的漢奸。但是,張愛仁一直躲在偽軍部隊裡,有著日偽部隊保護,難以下手。
此刻,任遠覺得機會來了。
任遠對宮下大尉說:“還有一個重要情況要告訴你們,山海關警備團團長張愛仁曾經與我軍聯絡,準備投靠我軍,被發現後,表面上與我軍一刀兩斷,其實在暗地裡,依然保持著和我方的秘密聯絡,並且對我表示,他願意繼續長期潛伏,等待時機,屆時反戈一擊,為國家效力。”
為了增加可信度,任遠還提供了一個細節:就在這次日軍包圍楊家鋪的時候,張愛仁還派了一個秘密聯絡員來給我通風報信。這個聯絡員在突圍戰鬥中為了保護首長,不幸中彈犧牲。任遠說,這個聯絡員,名叫江東。
這個江東,就是文章開頭提到的,在楊家鋪突圍戰鬥極為危急的關頭,任遠下令處死的那個叛徒。
此人本是任遠領導下的情報幹部,被派到張愛仁部做策反聯絡工作。但是他腐化墮落,反被張愛仁拉攏,叛變投敵。他從張愛仁部返回軍區後,任遠發現掌握了他叛變的證據。本來還打算利用他對敵開展謀略工作,但是在楊家鋪突遭敵人包圍,特殊時刻只能除掉了這個禍患。
任遠當時也沒有想到,臨陣的應急之舉,居然在被俘後有了妙用。
日軍研究分析了任遠提供這些情報後,感到任遠提供的情報與日軍自己掌握的許多情況的比較吻合,再加上此前任遠的積極配合態度,他們認為任遠提供的情報基本可信。
日軍對任遠提供的張愛仁這個“臥底”,尤其感到吃驚,同時又感到慶幸。日軍本來就對偽軍不太信任,對張愛仁的搖擺不定也深懷疑慮,而且任遠說的那個通風報信的江東,日軍一查,確有其人其事。
於是,日軍毫不猶豫地將張愛仁逮捕關押,隨後把他送到了東北勞改,讓這個漢奸落了個極為悲慘的下場。
供出張愛仁後,任遠看宮下渴望得到更多的線索,決定再施一計,把矛頭指向日本鬼子。任遠作出猶豫的表情說:“有件事不知該不該講。”
宮下的胃口一下子讓吊了起來:“不要有顧慮,統統講出來。”
“秦皇島的日本憲兵隊長武田,跟我們有些生意上的往來,是我們的老主顧了。”任遠知道,日軍對抗日根據地實行著嚴厲的經濟封鎖,對任何與“匪”通商的行為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任遠掌握,就在武田所管轄的區域,時有通商情況發生,而且武田又是一個作惡多端的日本鬼子,為根據地軍民所痛恨。把通商的帽子扣到武田頭上,既有事實鋪墊,又能借機治一治這個可惡的鬼子。
任遠說:“我們經常用煙土交換藥品,這事只有我的警衛員趙濯華和我知道。趙濯華被俘過,武田隊長放了他,條件是讓他幫助販賣鴉片。我們一直用這條線和武田隊長保持秘密合作。”有人有事有細節,宮下臉色都變了。他沒有料到,“皇軍”內部居然還有這樣的事。
任遠的計策再次奏效,不久,武田因“私通八路”,被判刑十年,押回日本服刑去了。
任遠的借刀殺敵之計效果甚佳。
因為提供情報有功,任遠很快被日軍從監獄裡放了出來,改為軟禁,有了一定程度的行動自由。
任遠對日軍實施了反間計,他當時不知道,日軍也在針對他使用反間計。就在任遠被俘後不久,日本人派飛機跑到了根據地上空。這次,他們不是扔炸彈,而是空投印刷品,這份印刷品的標題是:《劉傑告冀東同胞書》。劉傑是任遠擔任軍區聯絡部部長對外使用的化名,叛徒在指認任遠時說的就是這個名字。日軍在這份傳單裡,借劉傑之口,宣揚“東亞共榮、中日親善”,製造劉傑已經投靠日本人的假象。
日軍的這套做法,給任遠後來的人生製造了不少麻煩。
生 還
對於已經“變節”的任遠,敵人將他從牢中放出,安排在唐山市富商苗圃如的一大片房子裡。這裡有十幾個小院子,住著好些個先前投敵的漢奸。
任遠住在這裡,表面上似乎獲得了自由,其實日夜都有漢奸監視他的行蹤。
然而,日本人沒有想到的是,在任遠住處的附近,還住著一個地下共產黨人張家聲。張家聲曾經被捕過,出獄後假裝與黨組織脫離了關係,但實際上一直暗中繼續從事地下黨工作,並被委任為唐山情報站站長,由任遠單線領導聯絡。
任遠被捕之後,組織上一直在設法營救,並安排張家聲與軟禁中的任遠建立了聯絡,尋找機會,協助任遠出逃。
日本人對任遠的態度,一方面,漸漸放鬆了監視,另一方面,對任遠始終不願意在公開場合宣佈投降的態度,也越來越沒有耐心。
1945年2月17日晚,日軍大佐將任遠叫到辦公室,提醒他應該識時務,不要再有任何僥倖心理。
任遠面對日軍表面和善、實則咄咄逼人的舉動,也暗暗下定決心,要立即果斷地逃出敵營。
第二天一早,任遠吃過早飯後假意散步,轉了幾個彎看無人跟蹤,就敲開了張家聲的家門。十分不巧,因為任遠是臨時決斷,事先未與張家聲通氣。張家大嫂說張家聲頭天晚上出門打牌,此刻還未回來,他也沒有交代什麼時候回來。
沒有張家聲的幫助,出城和沿途如何對付敵人盤查,都是問題。
張家大嫂看任遠事急,不能等待,就從被子下取出1000法幣,給任遠做路費,看他能不能再找其他同志幫忙。
任遠出了張家大門,急速盤算後,決定去找一個特殊的人物。
此人名叫王新民,曾經是共產黨員,擔任過縣委書記。被捕後經不起嚴刑拷打,投降當了日本特務。後來經過黨組織爭取,又回到革命隊伍中。不久,他被敵人發現再次被捕,慘遭重刑後又投降敵人,出任開灤煤礦高階職員。可是他不久後,又秘密與黨組織聯絡,要求再回到革命隊伍中來。
任遠被俘前聽說了王新民的情況,曾向上級黨組織提出建議,把這個人交給自己做情報關係使用。上級黨組織認為,此人兩次叛變,敵人已不重用,對情報工作意義不大。不過可以視為統戰物件,作為特殊關係考察使用。
任遠被日軍從牢裡放出來軟禁後,住在附近的王新民借春節的機會,請任遠到自己家去過一次,並暗示自己與北邊(指根據地)有聯絡,有什麼事他可以幫助。任遠當時已透過張家聲和黨組織取得聯絡,所以對王新民的表示未置可否。
此刻,任遠對王新民是否可靠也是心裡沒底,但別無選擇,只能冒險一試了。
看到任遠一大早意外進門,王新民起初有些慌亂。但是,他隨後的態度,讓任遠放下心來。
王新民對任遠說:“你放心,北邊早有訊息,給我任務,要設法營救你,有什麼困難,你可以坦率直說,我們共同商討應對辦法。我已經被捕過兩次了,對日本人這一套,我已經受夠了,真不是人乾的!”王新民的憤怒溢於言表。
任遠覺得王新民可以信任,就把自己打算立即逃脫日本人控制的想法合盤托出。
王新民痛快答應帶任遠出城,直奔根據地。
任遠意識到這將給王新民的家庭帶來極大危險:“不行,鬼子不是人,我們走了,大嫂和你兩個女兒怎麼辦?”
王新民說:“現在管不了她們了,況且她們都是婦道人家,鬼子能把她們怎麼樣?”
王新民的妻子曾是根據地的女幹部,不愧俠義女流,她從屋裡走出,出言爽利:“你們說的話我都聽清了,現在趕快下決心,馬上就走,以防夜長夢多。你們先走,我們母女三人僱上一輛大車,都先回老家,躲開鬼子。都是中國人,一家人不說兩家話。”
她知道此一別離,相見不知何日,又拿出了一個金戒指遞給王新民:“帶上做個念想,這是我倆結婚時的信物。”
任遠流淚說道:“大嫂,你放心帶好兩個女兒,我們會時刻惦記你們母女的。多保重,根據地見。”
王新民用手捂著嘴,低聲說了句“走”,頭也不回地邁出家門。
王新民提議兩人“扮成開灤職員,佯稱到豐潤縣去提貨。”兩人的目的地是豐潤縣劉家營,冀東軍區機關常在那一帶活動,任遠比較熟悉。
兩人出城順利,一路疾行30多里,快到中午時,突然看到前面公路上出現一小隊打著膏藥旗的人馬迎面走來。任遠一驚,是不是日軍發現了自己脫逃,追了過來。
王新民熟悉這一帶情況,對任遠說:“這是日本巡邏隊,你別管,我來應付。”日軍走近,用夾雜日語的中國話盤問。
王新民掏出開灤煤礦高階職員的名片:“我們是開灤礦務局的,要去豐潤縣取貨,今天是正月初五,找不到車,公司急等用貨,派我們倆趕到豐潤取貨。”
日本兵見是日軍佔領區公司的高階職員,沒有發現可疑點,就換了口氣:“王先生既然是催貨的,可以過去。不過你們要小心,碰到八路軍時,你們要想辦法對付。這裡到豐潤縣城還有幾十裡,你們抓緊趕路好了。”聽到日軍反而叮囑起來,兩人放了心。
兩人繼續疾行,一路再無麻煩。走到下午四點多,太陽西斜,天色已經擦黑,終於看到了前面村莊的模糊影子。
終於走到村邊,突然傳來喊聲:“幹什麼的?拿出路條來!”隨聲閃出了兩名十多歲的兒童團員。
兩人正在答話間,一個兒童團員忽然看著任遠叫起來:“哎!這不是劉傑大叔嗎!”這孩子知道任遠的化名。
任遠心頭一熱,被俘四個多月,歷經生死考驗與艱險曲折,終於到家了!
餘 波
回到根據地後,任遠受到了組織與同志們的熱情歡迎。組織上對他是信任和關心的,否則也不會花大力氣策劃和實施營救。任遠回到根據地才知道,當初日軍將他從牢裡放出來改為軟禁,不僅是因為他施用反間計得到日軍的信任,而且是組織委託關係,給貪財的日軍軍官送了十多根金條,才使得日本人放鬆對他的監管措施,為後來營救成功打下了基礎。
但是,按照政策規定,任遠還必須接受組織對他被俘後表現情況的審查。
日軍飛機投下的《劉傑告冀東同胞書》,組織當時就判斷是日本人慣用的離間手段。不過,最終結論,還是要靠事實、靠證據說話。
經過一年多的審查後,1946年7月1日,晉察冀中央局主要負責人劉瀾濤、李葆華、許建國、姚依林等人共同討論後,正式作出了恢復任遠黨籍的結論。
結論寫道:任遠在“被俘期間政治上沒有原則錯誤,工作一貫積極負責,相信本人交待,決定恢復組織生活”。很明顯,這個結論是基於“相信本人交待”做出的,因為當時條件所限,審查中很難獲得其他客觀證據材料。所以,結論還留了一個尾巴:“如發現新的情況,另行處理”。
任遠也認為:我這段歷史具有特殊性,要徹底澄清的確有相當的困難,主要在於三個方面:首先,我無法找到同案的人證,因為從被俘之日起,我始終處於單獨囚禁、與世隔絕的封閉狀態,找不到任何一個人可以證實我的言行;其次,關於我被俘表現的佐證材料未被找到;最後,對我被俘審查的材料也找不到了。由於戰爭年代,敵人頻繁掃蕩,撤出張家口後有關我的審查材料找不到了,這又為日後的審查帶來不便。
在後來的漫長歲月裡,任遠因為這段被俘歷史,又經受過多次審查,一段時間裡甚至給他做出了“自首叛變”的審查結論,懷疑他是叛變後被敵人派回來的內奸。在極大的壓力之下,任遠本人也違心地說出了“假供騙敵是典型的個人主義、怕死鬼,喪失了共產黨人的氣節”的話。
他這段被俘歷史情況的最後澄清,是因為新的證據和證人的出現。上世紀70年代中期,組織上終於找到了當年日軍駐唐山1420部隊憲兵隊對任遠的全部審訊記錄,又找到當年地下黨組織在1420部隊的潛伏內線進行核實,組織據此再次做出審查結論:“經反覆查證,任遠所領導的地下組織沒有受到任何破壞,他被俘後沒有叛變和被敵人派回的事實”。事實證明,任遠在被俘後不僅經受住了考驗,而且表現得相當出色。
遺憾的是王新民的遭遇。王新民護送任遠回到根據地後,被安排住進了邊區政府招待所。後來,因為他曾經有過兩次被俘與叛變經歷,又被安排到政訓班,一邊接受培訓,一邊接受審查。
審查中,發現他曾經有叛變出賣同志的事實,結果將他處決了。
任遠後來在回憶中說:“其實他叛變的招供也沒對黨組織造成什麼破壞,因為都在根據地,日本人抓不到。後來中組部副部長李楚離說打錯了。”
王新民確實當過叛徒,確實沒有做到堅定不移。不過,他在叛變後的招供中又做了保留,給敵人耍了花招,後來又有重回革命陣營的意願,在營救任遠的過程中,又一次回頭是岸,表現得果決勇敢。
對於這樣一個人,應該怎麼評價?怎麼對待?可以有多種結論,多種選擇。但是,他的死,無疑是一個遺憾和教訓。
隱蔽鬥爭,敵我交織,真偽互作,忠奸異相,很難用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利刃區別是非。一雙實事求是的慧眼,歷來是霧裡看花的最佳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