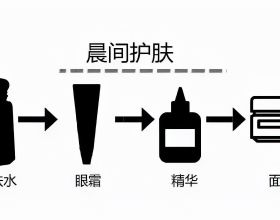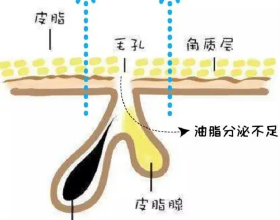來源:讀特
插畫 同春
作者簡介 韓東 詩人、作家、導演,畢業於山東大學哲學系。曾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高黎貢文學節主席獎、曼氏亞洲文學獎提名等。 2017年,執導電影《在碼頭》,入圍釜山國際電影節新浪潮競賽單元。著有小說集《西天上》《我的柏拉圖》《我們的身體》,長篇小說《紮根》《我和你》,詩集《吉祥的老虎》《爸爸在天上看我》,詩文集《交叉跑動》,散文《愛情力學》,訪談錄《毛焰訪談錄》等。其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
◎ 韓 東
1
五十歲不到,我就提前退休了,去農村租了五百畝地,過上了農莊主的田園生活。經常會有以前的同事、朋友從城裡過來,在我的農莊上釣魚,順便吃一頓“農家樂”。
一天,我接到一個女人的電話,說她三年前見過我一面。她說了自己的名字,我完全沒有印象。正有些尷尬,女人問,“你是不是有一個農莊?”“啥都不用說了”我回答,“有空你過來釣魚吧。”於是她就真的過來釣魚了。
我帶著小張去莊園門口接人,一輛紅色的甲殼蟲顛顛簸簸地爬過來。女人撳下車窗,那張臉依舊陌生,不過看上去挺正常的。她取下墨鏡,衝我笑了笑,準備下車,被我制止了。“先釣魚,”我說,“我們回頭再聊。”
小張手上拿著預備好的釣具,走在前面,甲殼蟲跟著,真的像只大瓢蟲一樣順著莊園裡的土路去了魚塘方向。目送完畢,我走回“大隊部”又歇下了。
這是一順七八間當地人蓋的房子,是當年人民公社時期生產大隊的大隊部。租這片地後,大隊部也歸我使用了。我沒有另蓋房子,平時就在這裡起居,接待客人也在這裡。躺在堂屋裡的老竹床上我正準備迷糊一會兒,小張回來了。
“咋回事?”
“人不見了。”
“人不見了?”
“這女的根本就不是來釣魚的。”小張邊說邊在一把竹椅上坐下,撩起衣服來擦頭上的汗。“我幫她打了窩子,支了魚竿,她就跑到樹底下乘涼去了,也不朝水面看,魚竿都沒摸一下。”
“那你就幫她釣嘛。”
“我是幫她釣。釣了一陣我一回頭,剛才還在樹底下自拍呢,不知道啥時候沒影子了。我就起來找人,到處都找不見,又不曉得怎麼稱呼,沒法喊。”
“現在她肯定已經回來了。”我說,“這樣,你回魚塘去,既然她對釣魚沒興趣,就不釣了,把人領到這兒來。”
“怎麼稱呼?”
“嗯?哦,你就叫她女士。”
“曉得了。”隨著竹椅幾聲響動,小張站了起來。“女士!女士!”他一路喊著出了堂屋門。小張的喊聲遠去,直到徹底消失。我在那張被這裡幾代人的皮肉摩得通紅的竹床上再次躺下,這次真的睡著了。
2
我是被一陣狗吠聲叫醒的。我餵了七八條狗,它們和我一起生活在大隊部裡。我睡覺的時候它們也在睡覺,現在先於我醒來顯然來了陌生人。我趕緊往赤膊上套了汗衫,走到門邊,看見小張拿著釣具往房子走過來,後面二十米遠的地方跟著那輛紅得像吐血一樣的甲殼蟲。
女人下車,身材盡顯。她穿著高跟鞋,背一隻名牌包,城裡時尚女性的標配。群狗衝過去,我大聲喝止。其實,這些狗並不會主動咬人,喝止它們算某種鄉間的待客禮節。女人倒是毫無畏懼,向狂吠的狗迎了過去。
“哎呀,這麼多狗狗。”說著她屈膝彎腰,做出迎接的姿勢。這時狗們對女人已失去了興趣,怏怏地散開了。女人不罷休,呼喚道,“過來,過來,寶貝兒過來。”
兩三條體型較小的狗試探著向她走過去,最後,女人一把摟過那隻西施品種的小狗。我想制止已經來不及了,女人一聲尖叫,手背上被西施咬了一口。親密接觸即告結束,小張甩起魚竿追著西施抽了幾下,後者兒兒地叫著跑走了。女人衝小張叫道,“別打它!別打它!都是我不好。”
我領女人去水池邊衝傷口。還好,不嚴重,虎口的面板上只有一滴血珠,水一衝傷口就看不見了。“小狗比大狗更有攻擊性,尤其是咬你的這條小狗,我養的狗裡數它最兇。”
“不兇不行啊,它要生存。”
看來這女人不僅愛狗,而且很通情達理。
“回城裡別忘了去打狂犬疫苗。”
“我會的。”女人說。
之後我們就在堂屋裡坐下了。我遞給女人一把芭蕉扇,她扇著說,“咦,你這兒沒有空調,但一點也不熱。”
“是吧。”我說,“老房子陰涼,加上前後門都開著,有穿堂風,我這是自然空調。我這有電風扇,要不要吹電扇?”
“不用了,不用了。”
小張端上來一盤切好的西瓜。我說,“吃西瓜,這是用井水冰鎮的。”
“真好啊,你這裡太好了。”
於是我說起在這裡的鄉居生活,說起我租的這五百畝地。有山有水,有農田也有尚未開墾的丘陵荒坡,什麼樣的景緻都有。本想著搞一個拍電影的外景基地,但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也就作罷了。目前我主要是僱了當地人種樹,供給樓市開發商,這些樹會被移植到城裡新建的小區裡……女人嗯嗯地聽著,似乎興趣不大。“它叫什麼?”她突然問我。
“誰?”
“那條狗,咬我的狗。”
“噢,旺財,它叫旺財。”
“旺財?”
“是土了點兒,我這兒的一切都很土……”
“以前它叫什麼?”
“以前?以前大概叫什麼團團、嬌嬌、寶寶吧。”
3
然後就開飯了。鄉下吃午飯早,加上我和女人也沒有什麼可聊的,不吃飯幹嗎呢?也許這女人此行的目的就是為了這頓“農家樂”。幾大碗肉菜很快就上來了,還有按當地人的方法自釀的燒酒。“也沒什麼好吃的,都是些土東西。”我說。
平時,如果來釣魚的人多,我會讓小張支起大桌子。今天只有女人一個人,所以就在小桌子上吃了。除了我和女人、小張,我讓做飯的戚大媽和在廚房裡燒火、當下手的戚大媽的老公也過來一起吃。老兩口先是不肯,我說,“又沒有外人,自家人吃飯。”他們才拖了長板凳過來坐下。由於桌面小,菜碗多,小方桌上放得滿滿當當的。
“老金,平時你就是這麼吃飯的?”
“可不是,讓你給趕上了。”我用筷頭指了指小張和戚大媽兩口子說,“他們都是當地農民,如今我也是一農民,戚大媽、戚大爺就像我爹媽,小張是我兒子,我們可是標準的農業之家,標準的農家樂,哈哈哈。”
戚大媽插話,“咱家就缺個兒媳婦了。”說著,還特意拿眼睛看了看女人。
我一想不對,沒準女人真是為“填空”而來的,於是趕緊接過戚大媽的話茬道,“不缺,不缺,我就是為躲媳婦兒才來當農民的。”
戚大媽的老公說,“農民也有媳婦,像我……”
我說,“我就是再娶也只會娶一個女農民!”
這話說得很煞風景,我也是急眼了。好在女人不以為意,她什麼都沒有說。
我們吃飯的時候,七八條狗也都進來了,在外圍繞了一圈等肉骨頭。除女人外,我們都把吃剩的骨頭往遠處扔,狗們順著拋物線撲過去,在堂屋進門的地方打成一團。只有女人不扔骨頭,在小方桌邊直接餵給了旺財。也只有旺財鑽到了桌下,啃完骨頭便直起身體。它後腿站立,前爪互碰,做出“作揖”的模樣。我告訴女人,這是旺財早年生活形成的習慣,現在派上用場了。
旺財不斷作揖,女人不斷餵它骨頭。骨頭用完了,女人乾脆夾起肉菜餵給旺財,連自己吃飯都顧不上了。其他狗也想鑽進來分享,旺財齜出尖牙發出威脅性的護食聲。我說,“小心,別再被它咬了。”
“沒關係,它現在已經認識我了。”
一條草狗終於從我腿邊擠過去,兩隻狗在小桌下開始翻滾廝打。我注意到女人用高跟鞋使勁地踢和旺財爭食的狗。“你不用幫它。”我說,“旺財可厲害了,別看它個頭最小,沒有狗能咬得過它。”
“是嗎?”女人興奮地說,滿臉放光。也許是燒酒鬧的。
“剛來的時候不行,那嬌貴的,一身毛病。”
“一身毛病?”
“哦,我是說一身的壞習慣,城裡人,不,城裡狗的習慣。在外面逛一圈回來還不肯進門,抬起腿來讓你給它擦爪子,不擦乾淨就不進來……”
“它是這樣的。”
“我哥們送它來的時候,還帶了一堆東西,狗梳子啦,電吹風啦,電熱毯啦,光是狗衣服就有好幾套。哥們囑咐我要善待團團——對了,它以前叫團團,不要讓團團受委屈。我滿口答應,可那哥們一走,轉身我就把那堆東西給扔了。”
“為什麼呀?”
“為什麼,為了生存,只有變成一條農村的狗,它才能生存。剛來的時候不吃不喝,後來餓極了,要吃了,又搶不過其他狗。現在倒好,什麼東西它不吃?連自己的屎都吃……”
突然我意識到,在客人面前,尤其是在女賓面前,吃飯的時候不應該說有關的字眼。女人似乎無所謂,她說,“我理解……後來呢?”
“也沒什麼啦,這不,如今旺財跟著它的土狗兄弟們滿世界地亂跑,跨溝過坎毫不含糊。它這種短小的身材實際上並不適合戶外活動,稍寬一點的水溝別的狗一躍而過,旺財沒準就掉水裡了。即使這樣,旺財仍然敢跳,更別說搶食吃了……”
“他怎麼能這樣!”
“不是怎麼能這樣,而是必須這樣,這就是自由的代價。”
“我不是說它,是說他。”
“是說他?你說誰?”女人把我搞糊塗了。
“李輝啊,不是他送它來的嗎?”
“哦……”
於是我想起了一件事。旺財的確是李輝送過來的,當時它也不叫旺財,叫團團。我想起來的並不是這件事,而是李輝送團團過來的緣由。李輝是把團團當成定情之物送給女朋友的,後來兩人鬧分手,女朋友就把團團退了回去。李輝睹物思人,對團團特別寵愛,但畢竟看著傷心,最後受不了了,這才把它送我這兒來的。
“你是……”
“是,我是李輝的前女友,王曉萍。老金,你貴人多忘事啊。”
“哎呀,哎呀!”我忙不迭地叫道,以此表達我的歉意。
“我本來不想說的,但是,”王曉萍又開始憤憤不平,“但是他怎麼能這樣!我們說好的,等我安定下來,條件允許,就會回來接兒子,不不,接團團,接旺財。他怎麼可以不和我商量,就把團團送人了呢?這人怎麼這麼差勁,太殘忍可怕了!把兒子送到這麼一個山溝溝裡,遭了多大的罪啊!”
王曉萍的聲音裡帶著哭腔。我說,“旺財是一條狗。”
“狗怎麼啦,狗狗也是生命!”
“是是。”
“他太讓我失望了,當初我怎麼會看上這種人的,真是瞎了眼睛!”
王曉萍開始抹眼淚。我問,“現在條件好了?”
“什麼?”
“現在你的條件允許養狗了?”
“我現在的老公給了我起碼的生活,兩個人住240平方米,跟你老金那是沒法比,但養幾隻小狗應該沒有問題。如果我們住別墅,或者一樓帶院子的公寓,就可以養大型犬了。我老公不聽我的,買了個大平層,花的錢足夠買聯排別墅……”
“你打算把旺財接回去?”
這會兒旺財已經到了王曉萍的膝蓋上,後者摟著它,做過美甲的指尖下意識地梳理著旺財身上的亂毛。“是有這樣的想法,但不知道你怎麼想。”
“我怎麼想?”
“畢竟你養了它這麼多年,現在是你的狗。現在,它是旺財,不再是團團了。”一滴眼淚落在了旺財的亂毛裡。
“那還不容易,叫回團團不就可以了?團團,團團。”我衝旺財叫道,旺財無動於衷。
“你看,它不知道自己叫團團了,也不認識以前的我了,還咬了我一口……”
“你不打算把團團接回去?”
“也不是。”王曉萍端起碗,喝了一大口燒酒,放下說,“那你開個價吧。”
“開價?”
“雖然李輝把團團送過來的時候,沒收你錢,但畢竟這麼多年下來,你還是有開銷的。”
原來如此。我當即表示分文不取。“物歸原主嘛,成人之美是我最願意幹的事兒。”我說,“這下子你們母子——你是把它當兒子養的吧,這下子你們母子就可以團圓了,我高興還來不及呢,談什麼錢!哈哈哈。”
王曉萍沒有笑,她說,“我知道了。”這讓我以為旺財迴歸的事已經確定下來。
4
這之後我就完全釋疑了,態度變得輕鬆。我給王曉萍夾菜,把肉菜夾到她面前的碗裡,她再用筷子夾了,餵給團團。動作連續,就像一條生產線,這我不管。我對王曉萍說,“這是地道的烏骨雞,你想有冒牌的我這都沒有!”
“是吧。”
“自然選擇啊。”我說,“我這散養了700多隻雞,黑雞、白雞、蘆花雞、麻花雞都有,天上有老鷹,把白雞和其他顏色的雞都叼走了,剩下200多隻是全黑的。”
“烏骨雞是骨頭黑。”
“誰說不是,老鷹就有這本事,能一直看到雞骨頭。毛黑骨頭白的也被它叼走了,毛白骨頭黑的卻沒事兒……”
“不可能,不合邏輯。”
“哈哈哈,我說笑話呢。反正我這生態好,什麼鷹啦,兔子啦,多得是,有時候還有野豬。”
“團團怎麼沒有被叼走?”
“你看它還是一隻白狗嗎?”
王曉萍看了一眼懷裡的團團,眼淚又要下來了。我覺得很有趣,能這麼聊聊我的農莊真是太好了。
突然王曉萍放下筷子,彎下腰,伸手去桌下似乎在抓撓。我問,“咋啦?”
“癢死了。”
“是跳蚤。”我說。
“哪來的跳蚤?”
我指了指團團,“你抱著一個跳蚤窩呢,是它身上的。”
“啊!”只聽一聲尖叫,王曉萍併攏的雙腿分開,團團冷不防重重地掉在了水泥地上——她似乎推了它一把。團團兒地叫了一聲,翻滾後站起,跑到我的腳邊尋求庇護。
“哎呀!寶貝兒,對不起。”王曉萍說,但自此以後就再也沒有招惹團團了。
她站了起來,提起裙子開始抖動,也不管小方桌就在下方,桌子上放滿了菜碗菜盤。王曉萍邊抖邊跺腳,灰土騰起,桌上的菜顯然不能再吃了。好在這頓農家樂已接近尾聲。
之後王曉萍又坐回去,脫了高跟鞋釦過來在地上使勁地磕。她伸直白得晃眼的腳丫子,腳背特別是腳踝附近密密麻麻有幾十個紅點。十指美甲在上面一陣猛撓,頓時體無完膚。
我讓戚大媽兩口子把碗筷收了,讓小張去找風油精。風油精找來後,王曉萍幾乎把一瓶全倒在了腳上。堂屋裡瀰漫著風油精刺鼻的氣味,所有的狗,包括團團都跑到外面去了。
“跳蚤怎麼不咬你們?”王曉萍問。
“也咬,不過……”
“不過什麼?”
“不過咬得沒那麼厲害,”我說,“我們已經適應了,這人不能太乾淨,洗澡不能那麼勤……”
“豈有此理!”
5
王曉萍穿鞋拿包,出了堂屋門,向停在前面水泥路上的甲殼蟲走去。她使勁地甩胳膊,試圖抖落想象中的跳蚤。這是準備返城的架勢,我也沒有加以挽留,只是提醒道,“團團。”
王曉萍腳下不停,“你不是說它是跳蚤窩嗎?”
“哎呀,那是形容,沒那麼恐怖。”我說,“回去後你帶它去寵物店洗個澡,驅下蟲就沒事了。”
小張已經抓住了團團,先我們一步到了甲殼蟲門邊,抱著後者等王曉萍過來。王曉萍停下,意思是讓他們(他和團團)站遠點。她轉向我說,“那它不是要進我的車嗎?跳蚤不會跑到車裡去?”
“反正你身上已經有跳蚤了。”我說。
“話不能這麼說。”王曉萍道,“回去我可以洗澡,團團可以交寵物店處理,但我的車怎麼辦啊!洗車又沒有滅跳蚤的業務。”
“那倒是。要不我讓戚大媽給團團洗個澡再走?”
“首先,戚大媽能把它身上的跳蚤消滅乾淨嗎?就算把團團身上的跳蚤全消滅了,我身上還有,我身上的跳蚤會跳到團團身上,團團身上的跳蚤又會跳到車裡面……”
“那您的意思?”
“我只好一個人走了。”
我不禁有點生氣,說,“你身上的跳蚤難道不會直接跳進車裡?”
“那到底好多了,我已經抖落半天了。”
這已經不講理了。於是我就不再說了,招手讓小張把旺財抱過來,好讓王曉萍上車。後者開啟車門鑽進車內,關上車門前說了句,“再說了,它也不認我了。”
我轉身背向甲殼蟲向大隊部走去,邊走邊在等汽車發動,心想,馬上這爛事兒就一了百了了。可一直沒有汽車發動的聲音傳來,車門倒是開關了好幾次。腳步聲響,幾乎在我跨進堂屋門的同時,王曉萍抱著一堆東西跑了過來。
“這是我給團團買的。”她說,明顯又帶了哭腔。“我,我還會過來看旺財的。”
王曉萍在小方桌上放下那些東西,馬上又跑了出去。我回過身,從堂屋門內一直看到了前面的水泥路上。紅色甲殼蟲小艇一樣在灰綠一片的山野裡漂遠了。
小桌子上放著狗梳子、狗衣服、狗項圈、狗玩具、狗餅乾、狗罐頭、潔齒棒以及一大袋進口狗糧。
小張說,“敢情這女的早想好了,根本沒打算接旺財。”
“她在猶豫,做了兩手準備。”我說,“你還年輕,不懂女人,尤其是城裡的女人。”
我讓小張去找一個化肥袋,把桌上的東西都裝了,找個地方給埋掉。
(原標題《我為什麼離開城市》)
本文來自【讀特】,僅代表作者觀點。全國黨媒資訊公共平臺提供資訊釋出傳播服務。
ID:j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