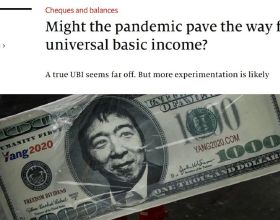第一次知道孫國章,是在二十七年前,我的老師、詩人孔德平先生給我一本孫國章詩集《無魚之河》,我記住了兩首。一首《尋梅》:“獨對/寒天//喊雪”,一首《無魚之河》:“滿眼風波/無魚……”
聞聽國章先生去世,孔德平先生髮給我《悼國章兄》:“無魚之河/大概因為網/很像走遠的記憶//無語之河/可能由於冰/如同此時的心情”,他特別註明“寫於秋風秋雨中”。
第一次見國章先生,是二十年前,在一次評獎會上,他抽著煙跟人爭論某人的詩。我記得他引用了帕斯的話:“每一個讀者都是另一首詩”。我問他這話的意思,他猛吸了一口煙:“小孩兒,你去悟。”又吸了一口說,“你這麼年輕當什麼評委呀,回去好好寫。”我當時三十出頭,他是我的父輩。
他以詩人孔孚先生為師,踐行孔孚先生“減法”“隱現”“靈視”“遠龍”詩論,講究煉字煉詞煉句煉意,崇拜孔孚先生的“高、淡、白”。他在《送孔孚師遠遊》一文中寫道:“經孚師點撥,我才懂得,一個真正的詩人,一個有出息的藝術家,不能在那裡咀嚼個人的恩怨和痛苦,必須超越社會和個體生命,在第三自然那個層面去構建藝術的殿堂。”真正的詩人應該具有社會良知和責任擔當,應該關注大事,有大格局,不能漠視。我們要用詩去凝固民族精神,燭照人性光輝。他講起來滔滔不絕。
他寫詩,愛詩,編的卻是《當代小說》,他選發的小說,也有詩意。他說,沒有詩意的小說,不是好小說。沒謀面時,我投過稿,隔了十年,跟他熟悉了,他還記得那篇小說。他說:“小說的核,是詩,你的這篇缺核。小說家只滿足於講個故事,只是完成了一半,字裡行間得流淌詩意。”寫小說要靠近詩人,詩人總是要擺脫有形的束縛,進行摶虛和再造,進入無的境界,無就是無限,無限就是大有。詩和小說一樣都是隱藏的藝術,它以其多義性和不確定性攝人心魄。
他一直在讀,在思考,不僵化,不媚俗,不跟風。
有一次說到中醫,我說我祖父也是中醫,他問我《內經》讀了嗎?我說買了,沒讀完。他吐出一口煙,笑言:“那你別說你爺爺是中醫。”他說《內經》中講醫有上工、下工之分,“上工守神,下工守形”。神是無形的存在,屬於道的範疇,形而上的範疇,也就是掌握了規律,達到了化境。詩無疑屬於“守神”的,超越對自然的臨摹的。“寫小說也一樣。”他補充一句。
他向我推薦葉芝,里爾克,茨維塔耶娃。又見面,我說讀了《內經》,又讀完了《湯頭歌》,他說“《湯頭歌》要背過,才是孝”,可我背不過。
他記住了好多名言和詩。比如愛默生的:“每個新時期的經驗要求有新的表達,世界似乎總是在期待著自己的詩人。”比如法國詩人勒內·夏爾的詩句:“個人的歷險,是我們人類共同的晨曦。”比如維特根斯坦的:“這種或那種動物之倖免於難,是因為它們具有躲藏的本領或能力。”比如王爾碑的《遺憾說》:“億萬年魚的淚晶瑩了海/不要去填……”
他的山東大學同學、我的老師鄭世華先生說,國章兄像普希金,在大學就寫詩,很敬佩他寫了一輩子。劉真驊老師說,國章給她的散文集寫過序,名字叫《愛到地老天荒》。大眾日報老報人、詩人趙鶴翔先生悼念國章先生的輓歌:“你的《無魚之河》的魚來到市肆,亦如萬家酒廠庫房的粱麥期待碎身,發酵,蒸餾,流變為酒,足以是詩人多產的詩使者。亦如居里夫人粉末兩座大山煉出半小瓶鐳,足以蕩平一座魔鬼之城……你同孔孚一樣,惜字如鐳,減之又減,字字都是鐳的裂變和震撼……”
秋風秋雨中,詩人的身影漸漸走遠,我手裡拿著他的書《漫筆》。在綠窗下,跟友人碰杯,腦海裡有詩人抽菸的姿勢,我彷彿聽到他在喊雨:“詩啊,我的苦戀,我的生命。”(大眾日報客戶端記者 逄春階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