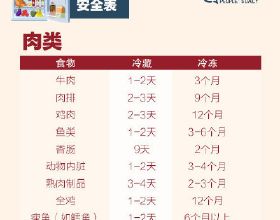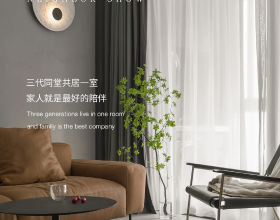作者:魯太光
面對文藝界的一些不良現象乃至亂象,最近常常想起魯迅的言論。
1935年5月,魯迅在《文學》月刊第四卷第五號發表題為《“文人相輕”》的雜文,對文藝界混淆是非、不辨黑白的現象進行犀利批評,在文末提出,做文藝批評“一定得有明確的是非,有熱烈的好惡”。
我以為,魯迅提出的這兩條是做好文藝批評必須守住的底線原則。
首先,做文藝批評一定得有明確的是非。文藝是與人心有關的事業,尤其需要是非心,容不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容不得和稀泥,更容不得指鹿為馬、以醜為美。我們的文藝界之所以出現一些亂象,原因很多,比如資本的操控——我們千萬不要忽視資本強大的操控力,但與我們的文藝評論也有一定關係。那些糟糕的作品之所以到處傳播,產生不良影響,離不開我們的一些評論者吹喇叭、抬轎子,而這些評論者之所以這麼做,是出於種種原因,放棄了是非標準、價值判斷。而放棄了是非標準、價值判斷,就等於放棄了文藝批評的底線原則。這種突破了底線原則的文藝評論,對文藝的嚴重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做文藝批評一定得有熱烈的好惡。這講的是態度問題。用魯迅在另一篇雜文中的話來講就是,“文人不應該隨和;而且文人也不會隨和,會隨和的,只有和事老。但這不隨和,卻又並非迴避,只是唱著所是,頌著愛,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像熱烈地擁抱著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著所憎——恰如赫爾庫來斯的抱緊了巨人安太烏斯一樣,是因為要折斷他的肋骨。”想一想魯迅的話,我們真應該覺得汗顏。我們的評論者是太“隨和”了,我們海量的評論文章中有“熱烈的好惡”的文字太少了。我們不僅很少對自己所是、所愛的作品發出熱烈的讚美,更極少對自己所非、所憎的文字發出理性而又毫不妥協的反對與批評。在這個方面,魯迅還是我們的楷模,他的雜文就是為了表達“明確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的,正因為如此,他的雜文才是“戰鬥的文學”,才產生了“行動的美學”,我們才能在裡面體味到人間的至愛和至恨,體驗到火的熱烈,冰的寒冷,自然也經常體驗到春風一般的溫暖。還是以“文人相輕”這個話題為例,在一般人看來,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魯迅為此卻斷斷續續寫了“七論”,一定要把道理講清楚。沒有“熱烈的好惡”,是做不到這一點的。這很值得我們學習。
再次,做文藝批評一定要有科學的方法。關於這個問題,魯迅也有明白的說法。他在《我們要批評家》中強調,為了推動左翼文藝發展,需要“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魯迅所說的“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指的就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現在批評理論很多、方法很多,這些理論、方法如果運用得當,都有益於文藝發展。但在我看來,要想推動中國當前文藝健康發展,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批評,因為只有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將文藝置於社會整體結構中觀察,因而最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不僅能夠對文藝作品做出美學價值判斷,也能夠對文藝作品做出社會價值判斷。比如,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引用莎士比亞《雅典的泰門》中一點點兒的金子“就可以使黑的變成白的,醜的成為美的;錯的變成對的,卑賤變成尊貴”的詩句來分析貨幣的力量,指出貨幣的力量有多大,貨幣佔有者的力量就有多大,貨幣的特性就是貨幣佔有者的特性和本質力量,而“貨幣作為現存的和起作用的價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換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換”。如果在這樣的理論視野中來看,我們就會發現一些頂流藝人身上閃爍的不過是資本的光芒,或者說,使這些人成為頂流的,是資本的力量。明白了這一點,我們的文藝批評就不至於過於膚淺,甚至能夠追根溯源,挖出這些看似閃亮的形象下面藏著的小,乃至醜與惡來,使受眾不上當受騙,或者儘量少上當受騙,也為文藝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鑑。
明確的是非、熱烈的好惡、科學的方法,是統一的有機體。如果沒有明確的是非,就難有熱烈的好惡;沒有熱烈的好惡,就很難堅持明確的是非;明確的是非、熱烈的好惡更需要科學的方法熔鍊、提升。
相信只要我們持之以恆地學習、發揚魯迅的批評精神,我們的文藝批評一定會好起來,形成良好的風氣,那我們的文藝也會好起來。(魯太光)
來源: 中國文化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