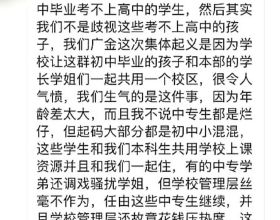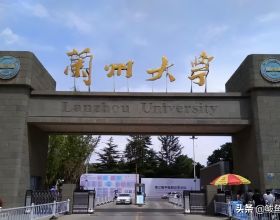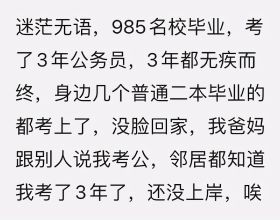本文來源於 真實故事計劃(id:zhenshigushi1),歡迎關注及投稿,符合者將獲得【1800元或2500元/每篇】稿酬
"
中考正變得越來越重要,一半初中生將在這次考試後,進入職業學校、技校,成為職校生。在職校老師的視野中,職校生並非“壞孩子”、“笨孩子”,他們也有自己要突破的命運壁壘。
開學第一堂軍訓課,穿著軍裝的職校學生們坐在操場的地上,一位男生雙手交叉於胸前,站立著面對教官。教官腳踢在男孩的右腿上,男孩踉蹌了一下又迅速挺直身板,瞪著眼睛,吼了句“X你媽”。
站在50米處的班主任陳莉目睹這一幕,小跑著趕過來。從教官的口中她瞭解到事情的起因,教官讓學生坐下,男生不肯坐,他嫌地面不乾淨會弄髒自己的褲子。
1米72個頭的男生身材消瘦,面容白淨,頭髮兩邊的鬢角推得老高,厚厚的劉海像西瓜皮一樣蓋在頭上。“你不能這樣跟教官講話!”陳莉嚴厲地說。男生沒有妥協,爆著粗口把話頂回去,氣焰更盛。陳莉只好請來教導主任。
身材高大的教導主任往男孩跟前一站,男生不再說話,變得畏畏縮縮。訓斥快要結束時,主任的手順勢在男孩的後背上拍了幾下,“不要碰我!”男孩又炸毛了。他快速掙脫人群,罵罵咧咧地離開操場,朝校門口走去。
眼看著男孩走出校門,主任趕緊拉來兩位老師,跑出去找。三位大人把他圍堵在巷子口,男孩逼急了,一邊罵一邊把皮帶從腰間抽出來當作武器,朝他們揮去。陳莉再次看見男孩,是被兩位老師分別架著胳膊抬回來的,送到校長辦公室。男孩還沒正式上課,就領了個留校察看的處分。
那是2016年的9月,25歲的陳莉在江蘇鹽城的一所公辦職業學校當老師,正式開啟了自己的職教生涯。入學軍訓持續一週,她就認識到管理這群學生的艱難。總有幾個“刺頭”不服管教,不換軍衣軍褲,不按口令做動作,與教官頂嘴,又或者謊稱頭疼,躲在教室裡玩手機。剛工作不久的陳莉毫無頭緒,只能口頭說教幾句。
1995年的侯藍藍教計算機專業。她所在的泰安市民辦職校,採取軍事化封閉管理,一個年級配備兩名教官,教官負責抓抽菸打架的學生,也負責晚上的巡邏和查寢。上課前班主任會要求學生統一交手機,還會在班裡裝攝像頭。
侯藍藍的課堂搗亂的很少,多數學生都趴在桌上睡覺。一開始她以為學生在故意裝睡,後來她才發現他們是真的困。因為白天接觸不到手機,晚自習後學生躲在被窩裡用手機玩遊戲、看影片,一直到凌晨三、四點。講臺上她彷彿對著空氣說話,她把看似脾氣好的學生拍醒,一些學生勉強支稜起腦袋,不一會又像一攤肉泥一樣蜷縮下去。
侯藍藍為此發過一次火。班上有男生馬上反駁道:“省省吧,我們已經給了你很大的面子,你是沒有見我們上其他老師的課。”聽到這句話,侯藍藍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教同一個班的老師向她抱怨,他們班真沒法管,有學生給老師的書本里塞辣條,也有30幾歲的大男人被學生氣哭。
學習習慣差,不服管教,是人們對職校生的慣常認識。他們本就是根據中考成績,篩選分流而來。2017年起,普高錄取率收緊,“普職比”從原來的6:4調整為5:5,這就意味著,初中畢業生中的一半人將無緣普通高中。越來越多的孩子將進入職業中學,成為一名職校生。
職校生極易被當成教育失敗的一個結果,除了成績差,多數學生與家人也不再對未來抱有期許。職校學校的老師,就是在這樣一種缺乏希望的氛圍裡開展工作,既要面對難以管理的學生,也要說服自己完成教育的職責。在這個過程,他們也在竭力扭轉社會對於職業教育的輕視與偏見。
易雲帆今年44歲,在職業中學任教長達22年。他是湖南省教育學院99屆的畢業生,也是國家最後一批包分配的大學生。畢業後他分配到湖南株洲縣的一所職業中專教計算機,那會計算機專業稱之為辦公自動化,還遠沒有如今時髦的叫法。
上世紀80年代,職業學校和技工學校的誕生是為工廠培養工人而設立,學制三年,學生畢業就能分配進工廠工作。在漫長的教學生涯中,易雲帆送走了一屆又一屆學生,執教生涯前半段的畢業生多數被電子廠招走,他們在崗位上或組裝電腦,或安裝手機晶片,成為流水線上的一員。進廠,被看作是職校生的宿命。
陳莉從未想過自己會在職業學院教書。她是南京師範大學的研究生,畢業後她回到家鄉鹽城,想在普通高中學校當老師。她學新聞傳播專業,在高中只能教語文,她對語文不感興趣。一次,她在市教育局出的一則招聘公告中,看到職業高中招聘攝影老師,她愛好攝影,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她考上了職教的崗位。
到職校報道時,陳莉才知道學校根本沒有攝影專業,也不開這門課。學校把她調劑到市場營銷專業,教電子商務。雖違背了她意願,好在也在她學過的範圍內,教起來也順手。
這所職業學院,設定了眾多的專業:汽修、電力、幼師、計算機、會計……進入職業學院的校門,學生第一件事就是選專業,這也決定著他們將來的職業去向。
剛來學校的那年,陳莉帶高一新生,是1602班的班主任。新老師擔任班主任的職務,這讓她不能理解。後來她才發覺這是因為沒有老師願意當班主任,許多空位等著年輕人去填補。
電子商務不算是熱門的專業,全班僅20個學生,18個男生,2位女生。第一次開班會,陳莉讓每位學生上臺做介紹,從哪裡來,有什麼興趣愛好。有十幾個學生說自己的愛好,是睡覺、吃飯、打遊戲。這讓陳莉不知道如何接話,與學生大眼瞪小眼。最後她對學生說:“你們是新進來的學生,我也是新來的老師,我們一起成長”。
頭一回教書陳莉充滿熱情,但她很快意識到,現實遠不像她想象的美好。課堂上不超過10人聽講,其他人要麼睡覺,要不小聲講話,有女生大大方方地將鏡子擺在課桌上,開始化妝、剪指甲。
起初,為了調動學生們的學習熱情,陳莉會想辦法開展好玩的互動遊戲。比如講到網上拍賣,她會模擬一場現場拍賣會,隨手拿一個水杯,誰出多少錢,誰得價更高,課堂氛圍變得熱鬧起來。又比如上商務禮儀課,她讓學生進行情景表演,一個同學當面試官,另一個作為應聘者,模擬應聘場景。有的同學做出誇張的肢體動作,引來一陣笑聲。
但不是每堂課都能達到這樣的效果。在職校,學生的課由文化課和專業課兩部分構成,文化課包含語數外三門,加上德育課和體育課。教文化課的老師最為痛苦,因為學生的基礎太差。差到什麼程度,一位數學老師曾對陳莉舉例,x-3>0,這樣簡單的不等式也解不出來,數學只能達到小學三四年級的水平。到了期末,劃複習重點,學生說不用複習了,“反正也不會”。結果不出意外,拿到捲紙,都是10分,20分的成績。一學期下來,那位數學老師白了七八根頭髮。
作為計算機專業的老師,侯藍藍上課一半時間都在機房。先用PPT演示十分鐘,再讓學生動手操作,有學生不會就下去一對一指導。她發現有一部分學生打字很慢,原因是他們無法熟練使用拼音。不會拼音,他們只好用手寫,或用語音錄入,又或者用手機拍了圖片後,再上傳識字。
侯藍藍髮現學生們不會鑽研學習,課程稍微有點難度,試幾下不行就放棄了。在後面的課程中,她有意刪除特別難的理論,留下學生能力可接受範圍內的知識,課堂氛圍就好了很多。
在學生眼裡,侯藍藍不像老師,更像鄰家的大姐姐,她戴著大框眼鏡,穿得也很時尚。在這所封閉的學校裡,學生每兩週才允許回家一次,侯藍藍住在學校宿舍,課堂以外,學生也樂於與她交流。
班上有個男生喜歡看耽美小說,經常與她分享,說到書裡的故事情節,男孩繪聲繪色,他自己構思小說,在格子本上寫下四百餘字,拿給侯藍藍點評。他還照著樣子畫了一幅老師的肖像,這幅畫被侯藍藍貼在了寢室的牆上。
後來另一位學生來做客,看到牆上的畫,隨口說自己畫得比他好,侯藍藍不信,故意與他打趣道:“你字寫得那麼難看,畫畫能好到哪裡去。”那個學生沒有答話,當天晚上,他用QQ發來幾張自己的畫,還附帶上素描十級的證書。
成為班主任的那一年,陳莉管理得事無鉅細,她立下班規,讓學生按照規則來進行自我管理。每天早上6:45分,全校學生都要繞著操場跑步,有的學生起不來錯過了早鍛鍊,陳莉會讓他們在課後時間補上,她在旁邊盯著,直到跑圈結束。
與學生交流得深了,陳莉也覺察出學生的可愛之處。有回她感冒,嗓子不舒服,課間休息再回來時,自己放在講臺的水杯又重新盛滿了溫開水。
但這種細微的感動只是一瞬間,很快又會被巨大的失落感所籠罩。每到考試,試卷發下去,一大半的學生都趴下睡覺,陳莉說這是她最感到教學失敗的時刻。
在軍訓中被留校察看的男生,陳莉見到了他的家長。這位母親柔柔弱弱的,說話也輕聲細語,是個性格溫柔的人。在校長辦公室,陳莉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家長,一旁教導主任冷著臉將處分單遞給她簽字。
男孩的母親很平靜,她沒有當著老師的面辱罵孩子,只是用責備的眼神看了兒子一眼,男孩把頭低下去,沉默著。得知校方不會把孩子開除,母親很感激,不停地跟老師道歉,鞠躬,整個人彷彿要躲進殼裡似的。
三年教書下來,陳莉發現男孩本性不壞,只是人很固執,不喜歡別人碰他的身體,也有些小潔癖。他的媽媽身體不好,常年在家養著,經濟上全靠爸爸一人支撐。
在陳莉的班級,像男孩這種家庭情況算是好的。多數家庭,要麼父母離異,彼此重組家庭;要麼是留守兒童,從小跟著爺爺奶奶生活;還有的母親受不了家暴離開,又或者父親是殘疾人。真正家庭圓滿的不超過5個人。
有一個男生的外號叫“邋遢大王”,他性格開朗,但是穿衣邋遢,不愛洗澡,沒有人願意跟他做舍友。後來陳莉瞭解到男孩的母親不知什麼原因離家出走,他跟著爺爺生活,但爺爺也老了。陳莉覺得家庭問題是造成學生內向、偏激、懶惰、自卑、自暴自棄或霸凌等不同性格缺陷的核心原因。“這是他們的問題,又不完全是他們的問題,沒有出生在一個好的家庭,使他們一開始就註定了無法成為更好的自己。”陳莉說。
每個學期的開始,學校要求老師挑幾個學生,去家裡做家訪。王小洋是陳莉很喜歡的一個學生,起初他天天打遊戲,連作文寫的也是遊戲,各種遊戲術語,陳莉也聽不懂。高二上學期王小洋突然不打遊戲了,上課開始認真聽講,平時打掃衛生也很積極。
一次家訪,陳莉來到王小洋的家中。王小洋的家在城中村,地處偏僻,周圍幾棟舊房子像是已經臨近拆遷。屋子是農村房子的構造,上下兩層樓,樓下經營著小賣部。他是單親家庭,父親過世後,他同母親生活。母親年齡不大,但頭髮已經花白。
陳莉說起孩子在學校的表現,誇他努力,但底子薄弱了些,努把力成績還可以再往上趕一趕,孩子的媽媽只是點點頭,她沒有表現出太大的期望。她和老師客套幾句,她不會說漂亮的話,更不會要求老師對孩子特別關照。
在職校,學生和家長不關心成績,對未來似乎也不報太大的期待。
開學第一天,陳莉組建起家長群,有時她在群裡發幾張學生在校的圖片,只有一兩個家長應和,其他人一片沉寂,甚至還有家長在群裡發廣告。她說家長很少管自己的孩子,她把學生的獎狀發到群裡,想讓家長看到孩子身上的閃光點。
如果要批評某個學生,陳莉不在群裡說話,她會單獨與學生家長聯絡。有學生上課總講小話,她找到學生的媽媽。那位媽媽向她倒苦水,說她不知道為兒子哭了多少次,她沒有辦法,管不了。陳莉看到她的朋友圈,裡面全是妹妹的照片,彷彿她的兒子不存在一樣。
這些家長的教育與陳莉從小接觸到的截然不同。陳莉出生在一個高知家庭,父親和母親都是英語老師,對她的教育很上心。陳莉重視考試成績,多一分,少一分,都會影響她的情緒。她高考失利讀了個二本學校,大二她就明確目標,一心考研,最終得償所願,進入更好的學校,攻讀廣告學。一路披荊斬棘,她不曾放低對自己的要求。
陳莉的大學同學有的去到國企,有的進入電視臺,有的在網際網路大廠謀得好的職位。反觀自身,她時常感到失落,“作為一個南師大研究生,自己打爛了一手好牌”。
教書幾年下來,她明顯感到自己的經驗,在這群學生身上毫無用武之地。當一個具有精英理念的老師和沒有理想的學生群體相遇,她感到更多的是失落和深深的茫然。她想起有位老師對她說的話:“學生不是那麼好教導的,先別說成才了,先撫養他們成人。”
透過學生群體,職校的老師們也會看到階層壁壘的森嚴。
一次上課,陳莉講到產品定位,拿一款打車軟體與另一款作比較,學生表示沒有聽過。他們中很少有人有過打車的體驗。前段時間,“水稻之父”袁隆平逝世的新聞刷屏,陳莉在課堂上提到此事,她驚訝於學生們對袁隆平一無所知,那天她沒有上課,找來袁隆平傳記電影供學生觀看。
易雲帆教書的早年間,他曾目睹學生邁進職業學院的大門後,想狠命改變家庭命運的急迫。2010年,他組織學生去診所看牙醫,一位男同學長了蛀牙需要治療,治牙的費用為3000元。男生的父親是一位智障人士,家裡拿不出這筆錢。作為老師他提出為學生出錢,卻遭到了學生的拒絕,學生對他說等畢業後他就可以去掙錢了。
教書多年,易雲帆目睹年輕的生命,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被現實甩出。與應試教育不同,三年的職業教育不足以讓學生在社會上立足,這些孩子就算找到了工作,也無法釋放自己的潛能,上升的瓶頸會立即出現。他感到在進入職校校門的那一刻,關於未來的答案就已經給出,教育能帶來多大的作用,他不太確定。
2013年,他迎來自己職教生涯的“臨界點”。學生沒有升學的壓力,教師教書的勁頭逐漸被磨平,沒有職業成就感,這個過程就好像溫水煮青蛙。
他感到茫然,想要有新的改變。學生大多排斥文化課,除了語數外,他們接觸不到地理、歷史等學科,知識層面狹隘。每日7點固定早讀,學生們拿著課本,朗讀得心不在焉,大好的光陰也浪費了。
基於此,易雲帆制定了一個早讀本,小冊子裡收錄了部分唐詩宋詞,第一篇文章是《少年中國說》的節選,最後一篇是荀子的《勸學》。
早讀開始,學生們朗讀詩詞,易雲帆也跟著一起讀。他告訴學生,中國文學的博大精深,流傳下來的文字經歷了時間的考驗,其中的道理,等著他們自己慢慢去理解。學生透過這種方式有了新的認知,同時易雲帆也在消解著自己的情緒。
他還成立了電影協會。晚自習播放電影,電影結束時他讓學生分享自己的體會。有一回他播放影片《千與千尋》,一位學生說自己的感想,他提到“腐爛神”不是真正的腐爛神,而是受到汙染的河神。這位學生說,我們要保護好環境,尊重自然。
中專培養的是一批怎樣的學生,這是易雲帆一直思考的問題。基礎學科的成績不再成為評判學生“好壞”的唯一標準,進入職業學校,他們被拉到另一條賽道的起跑線前。
職業學校的明星學生是那些技能大賽的獲獎者。每年的技能比賽從市裡選拔,到省賽再到國賽,可謂過五關斬六將。突圍出來的第一名不光有獎金,特殊專業的人才還能破格被本科學院錄取,進入大學學習。
2018年,陳莉帶領班上的四位學生組成團隊,去到市裡進行技能比賽。比賽的內容是在虛擬的電子商務平臺上開網店,從店面的設計、擺放,到計算進貨成本,定價,再到充當客服,與客人溝通,完成整個賣貨流程。在那場比賽中,他們取得了團體二等獎。衝擊省內半決賽,學生沒有獲得名次,陳莉覺得他們已經非常優秀,四名學生之中就有王小洋。
臨近畢業,陳莉再次來到王小洋的家裡,她想說服孩子的母親讓他繼續讀書。三年的學習期畫上句號,但這並不代表學業的終點。擺在學生面前的還有一條路,就是繼續升學。
並列於普通教育,職業教育也有著自己的升學和就業體系。或透過“3+2”中高職銜接,拿到大專文憑,又或者直接參加“春季高考”,進入本科學院。
早些年,職校學生只有百分之十會選擇升學,多數學生一畢業就去往各個工廠。最近幾年,選擇升學的學生越來越多,陳莉說學生思想的轉變大多是從實習期開始的。
高三一開學,學生們就被分配到各個企業中去,進行崗位實習。陳莉所在的電子商務專業,學生的實習單位是各類短影片公司。通常,用人單位會讓學生做一些簡單的活,比如網路稽核員。負責釋出前的片子稽核,這類工作單調,也沒有多大的技術含量。
這並不意味著工作輕鬆,三班倒,夜班從下午6點一直要上到第二天的6點。實習期的工資,底薪是1500元,再加上格外的提成。
實習期結束,學生拿著實習表格,重新回到學校,這時老師會統一詢問學生的意願,是否願意繼續讀書。“大多數學生在經歷公司實習後,無法忍受單調的工作,再加上家長了解到學歷對於找工作的重要,都會選擇升學。”陳莉說。
王小洋的媽媽最終同意升學的建議,她說再沒錢也要支援孩子上學。陳莉所帶的2016級第一屆畢業生,全年級50餘人,有三分之二的學生透過“高職單招”的形式進入到高職院校。
如果要衝擊本科院校,還需要學生自身付出更多的努力。2004屆的高考班,是易雲帆帶過的最棒的一批學生。
他至今記得班上的一位男生和一位女生,兩人最為用功,男生中考失利,來到職校後心有不甘,每門科目都拿第一。那年的本科分數線為540分,易雲帆記得尤為清楚,他兩的分數達到600來分,同時考上了湖南師範大學。那一屆考上本科的學生有8個人。
客觀來說,中考帶來分流效應,真正決定分野的關鍵要素還是學生本身。去年上半年,侯藍藍帶兩個高考班,看到了學生的另一面。
學生王濤的QQ簽名是“運動不止,生命不息。”他有著1米80的個頭,長相帥氣。從小學到初中,他是學校校隊的短跑運動員,熱愛運動,直到兩年前查出心臟病,體育訓練也被迫停止。此前,王濤將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田徑場上,學業落下,他只好進入職業學院學習電力專業。命運牽引他走向另一個方向,但他不想過早放棄,他向侯藍藍打聽體育相關的院校,他說等身體養好,能繼續在運動場上,他的理想是當一名體育老師。
另一位學生有聽力障礙,他本來在普通高中讀書,因為聽力問題學習跟不上,高二轉學進入職校的高考班,他想學醫,自己聯絡能接收的學校,最後找到一個醫學院,現在他正在為考那個學校而努力。
2014年,易雲帆去馬來西亞旅行,回國途徑深圳,一位2008年畢業的學生在那裡工作生活,他們取得了聯絡。時隔6年,學生在飯桌上提起自己的經歷,他在一傢俬企裡做網路維修,早年技術水平低,跟著老師傅學,經常被罵哭。好在他熬了過來,他說自己打算組團隊接活,那年他25歲。
陳莉所教的新一代學生,他們的就業有著更為多樣化的選擇。有的做廚師,有的當了司機,還有一位在蘇州做糕點師,最近做糕點的學生聯絡她,提到自己升職為店主,單獨運營一家門店。陳莉為他感到高興,也為自己高興,在豆瓣她記錄下自己的感想:“職業學校的學生需要以他們優秀的姿態被社會看見,因而他們需要好老師。”
教書5年,陳莉做的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開除了班上一個喜歡霸凌的學生。她覺得自己沒有盡最大的努力拯救他。後來,她看到那個學生和一群頭髮五顏六色的人停留在學校附近。她尷尬地走過,連頭也不敢抬,她彷彿看到這幾個孩子的未來。她不敢往下想。
- END -
撰文 | 周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