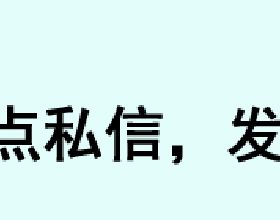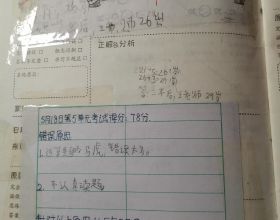剛入了秋,老韓就忙忙碌碌起來,長年工地奔波,被風霜雨雪漬紅的麵皮彷彿越發亮堂了。
老韓這次忙的不是鋼筋水泥,也不是生計來日,而是韓琳的的婚事。
整個莊子的人都知道,老韓把韓琳當成眼珠子疼,大家也都知道,韓琳不是老韓的親閨女。
老韓丟下手頭的活計,先從房子開始搗鼓起來。
老房子年頭久了,牆皮剝落,看上去坑坑窪窪的,老韓便從鎮上買了好幾桶牆面漆,挑了個晴好天氣,把自己從前在工地打零工的舊衣服找出來穿上,當了三天快樂的粉刷匠。
白色的油漆在老韓的頭臉和衣服上留下星星點點的痕跡,惹得鄰居們打趣。
“老韓你看你這把自己造的,你就不能找兩個油漆工給你幹麼,150塊錢一天,刷的又快又漂亮。”
“當了半輩子鐵公雞,我看你是改不掉這個臭毛病了。”
“你說你省這錢幹啥!”
聽這話的時候,老韓已經扒下了“工作服”,正在用柴油兌水洗臉,他使勁搓著已經鬆垮的臉皮,一本正經道:“我自個兒慢慢幹,那錢省著給我閨女還能做個指甲呢,前兩天她回來時候說了,現在大城市的姑娘都時興這個,我閨女不能比旁人差。”
大家一鬨而笑。
“你還知道做指甲?”
“你家琳琳缺你那點兒錢?”
“就是,琳琳多爭氣,又買房子又買車的,還要你給她省那幾個子兒?”
他一言你一語說的多了,老韓生出些驕傲,昂起頭眯著眼笑,不再接話,可幹活兒卻更有勁兒了。
拾掇完房子,老韓又去鎮上的鋁合金門市訂了一扇朱漆大鐵門,把原先那扇鏽跡斑斑,還吱呀作響的老夥計換了下來。
週末的時候,韓琳給老韓和她媽送保健藥回來,站在院前驚得張大了嘴。
“媽,老韓這是……要麼不拔毛,要麼全拔光?”
周海萍重重拍了兩下韓琳的肩膀。
“去你的,你爸一點一點地給你籌備婚事呢,說是都得換新的,讓你風風光光地嫁出去,城裡和這兒都是家,都得讓你們住舒服了。”
韓琳背過身,扯起胸前的圍巾抹了一把臉,大踏步地往院裡走去,一邊走一邊叫喚。
“老韓,你是不是把錢都砸房子上了,日子不過了啊……”
韓琳一開始不姓韓,跟她媽姓周,她親爸是個混球,一天名分都沒給過她媽。
八十年代末,港風歌曲和電影在內地流行起來,催生出一批搖滾青年,油光水亮的中分頭,花襯衫,喇叭褲,大頭皮鞋,這是當時小年輕的標配,人人都照著一個標準捯飭自己,韓琳親爸在這一水的模子當中脫穎而出,一下子就得了她媽周海萍的青眼。
因為她爸長了一張好看的臉。
韓琳親爸只用了一張臉加幾句甜言蜜語,就輕易俘獲了周海萍的心,讓這個家境優渥,從小嬌慣到大的獨生女對他死心塌地,不惜為了他與全家對抗。
很久之後,周海萍回想那一段歲月,已經很平和了,甚至能半開玩笑地嘲諷自己。
“真懷疑有人給我下了蠱,其實他當時什麼承諾都沒給過我,我就那麼一頭扎進去,不管不顧的,你姥姥姥爺那時候恨不得掐死我。”
模模糊糊地確定了關係之後,周海萍用實際行動來證明她對韓琳親爸的全心全意——從家裡搬出來,跟韓琳親爸住到了一起。
那個年代雖然已經漸漸開明,但未婚同居這種事,還是能掀起大風浪。
周海萍在小城一下子出了名,整天跟著韓琳親爸從這個迪廳混到那個迪廳的串場子,一把吉他走天下,牛的不行的樣子。
時間一長,周海萍就發現了不對勁。
她喜歡好看的臉,其他姑娘也喜歡,而韓琳親爸,似乎特別享受眾星捧月的感覺,從來都不會拒絕。
人們對好看的東西的容忍度是真的高,不管是對人還是對物。
周海萍忍著韓琳親爸和其他人的互動調笑,忍著韓琳親爸對她越來越不耐煩的脾氣,但是越忍越低到塵埃裡去。
終於玩出了火,周海萍懷孕了,發現的時候已經快五個月。
本以為這樣能攏住男人的心,周海萍回家求著父母去找了韓琳的爺爺奶奶,誰知道兩位老人壓根拿不住兒子。
“我是沒玩夠,你要想結婚也行,但你不能管著我。”韓琳親爸一副吊兒郎當的語氣。
周海萍當時就氣哭了,指著韓琳親爸罵流氓,沒想到男人嬉皮笑臉地吐了個菸圈:“你不早就知道我是流氓嘛,要不你肚子怎麼大的。”
在韓琳爺爺奶奶的捶胸頓足中,周海萍拉著韓琳的姥姥姥爺回了家。
走之前,周海萍已經收拾好心情,止住了抽抽嗒嗒,對韓琳親爸一字一句道:“從現在開始,我和這孩子都跟你沒有關係,咱們一刀兩斷。”
一刀兩斷的意思是,徹徹底底地撇清關係。
周海萍慫的時候是真慫,面對韓琳親爸的多次背叛都隱忍不發,硬氣起來也是真的硬氣,說不聯絡就不聯絡,一點餘地都沒留。
快五個月的孩子,已經有了感情,無論父母親戚怎麼勸,周海萍都堅持要留下,就這麼犟著一口氣,韓琳出生了。
單身姑娘未婚生子,周海萍的名聲臭出去二里地,好在家境殷實,嚼舌根的人也只敢在背後偷偷的議論。
除了沒爸,韓琳的日子還算得上順風順水。
但在老人的眼裡,還是要有一個完整的家庭才算圓滿。
周海萍的婚事,成了姥姥姥爺的心病,偏就周海萍自己不急。
因為家底厚,儘管周海萍名聲不好,還拖著一個半大孩子,但上門說親的人還是絡繹不絕,可週海萍這個看不上,那個沒興趣,總是吊著一張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臉,漂亮,卻也冷漠。
大約是在韓琳親爸身上把所有的愛和恨都用完了,周海萍一門心思地跟著父親做生意,一年又一年地蹉跎著,一直到了韓琳十歲。
那年長江中下游發大水,韓琳家的生意一落千丈,有兩家店鋪和一間倉庫泡在水裡兩個多月,批發回來的上好的傢俱和木材,全都泡得發了黴,出了氣泡,有的還生了蟲,韓琳姥爺眼裡看著,心裡急著,嘆息聲一天比一天厚重。
老韓就是這時候冒出來的。
老韓有木匠手藝,接了兩家給新房打木門和衣櫃的活兒,滿縣城地尋木材。
那時天災剛過,一切待興的模樣,建材市場的大門還關著,要等城建局統一規劃重開,很多鋪子都還是鐵將軍把門,可新房的裝修是不能等了,早就定好的日子和吉時,不能因為房子未曾裝修而耽擱了。
主家連著加了兩次價,讓老韓儘管去找材料。
沿著臨街的門市一家家找過去,發現韓琳家的兩個鋪面開著,老韓一激動,當即就和韓琳姥爺簽了訂貨協議。
木材清出去大半,老韓在店裡瞧了瞧,發現還有些傢俱,便主動詢問起情況來。
一番瞭解後,老韓摸著後腦勺將燙手山芋攬了個囫圇:“鄉下好多人家都讓大水給淹了,政府的補助也只能管溫飽,大家都要重置家業,可花錢買新的又都捨不得,您看您這些傢俱,在城裡也賣不出去,不如去鄉下碰碰運氣,多少回點兒本錢。”
韓琳姥爺做的是高階傢俱生意,不懂底層的道道,但能回本兒也算一件好事,否則這些傢俱就只能扔掉,或者送人做個順水人情。
聽了老韓的建議,韓琳姥爺便放話讓老韓全權做主。
老韓尋摸來一輛貨車,將泡了水的傢俱一股腦地綁了上去,邀著周海萍,一起去了周邊的鄉鎮。
從天麻麻亮到剛擦黑,貨車滿滿當當的出去,空著殼兒回來,韓琳姥爺終於露出了笑臉。
為了感謝老韓,韓琳姥爺主動將木材的價格下調了些,原以為這中間的差價會被老韓自個兒揣進兜裡,沒想到老韓又摸著後腦勺憨笑,說要告訴給主家,人一定會開心,周海萍問他怎麼不自己賺了,老韓傳授生意經:
“這就兩家,我能賺多少,還不如給主家賣個實惠,好讓他們在親戚朋友之間幫我宣傳,多接幾家活兒才是正經事。”
周海萍對老韓的印象瞬間好起來。
不偷奸耍滑,不投機倒把,比起韓琳親爸,算是個穩重性子。
自那以後,老韓不管接了哪家的活兒,都從周海萍手上訂木材,倆人也很快熟識起來。
一來二去聊的多了,才知道老韓也是一個人帶孩子,兒子韓爍比韓琳還大三歲。
老韓妻子生孩子那年出了意外,好好一個人,癱在了床上,醫生說有過這樣的情況,能不能恢復如初不好說,配合著治了幾年,一點好轉的跡象都沒有,全身肌肉還開始萎縮,韓爍五歲那年,女人留下遺書,說不願再拖累老韓,自殺了。
打那之後,老韓就一個人既當爹又當媽地拉扯著韓爍。
周海萍心裡蕩起了漣漪,說不清是同情還是別的什麼,總之對老韓越發親近起來,有時倆人竟還會約著一同吃個飯喝個茶。
韓琳姥姥姥爺瞧著倆人這樣,起了念頭要撮合,又不知道老韓是怎麼想的,便趁著有一回周海萍出門進貨,拉著老韓探心思。
還沒等老人多說幾句,老韓就全撂了,還是一副憨樣。
“叔,我……我喜歡海萍,她能吃苦,心眼兒也好,是個過日子的好女人。”
“可我怕海萍看不上我,我……我配不上她……”
老韓說的是實話,周海萍哪怕生了孩子十多年,也還是一副小姑娘模樣,雖然打理著兩家店,可她絲毫沒有其他做生意女人那樣的粗嗓門和不修邊幅,不管到哪,不管什麼時候,周海萍都把自己捯飭得乾乾淨淨漂漂亮亮的。
再加上家境懸殊,女強男弱的格局特別明顯,老韓是真的發怵。
看著老韓有些畏縮,韓琳姥姥一臉慈愛:“其他的你別想,就說你想不想娶海萍,她年輕時候犯過渾,名聲不大好。”
“那有啥的,年紀小,不懂事,遇到壞人了,也不能怪她,現在海萍不是把琳琳照顧得特別好嘛,她是個負責任的媽媽,這就夠了。”
最後一句話正好被一腳踏進門檻的周海萍聽了去,心一下子就軟了。
帶著十二歲的韓琳,周海萍終於嫁人了。
婚禮是大操大辦的,依著周海萍的想法是兩家人一起吃個飯就成,但老韓不答應,非說周海萍嫁給她已經算是受委屈,如果連個像樣的婚禮都沒有,那就太不像話了。
熱熱鬧鬧的一天,還夾雜著有些人的拈酸含醋。
“沒人要了吧,才嫁個什麼都沒有的男人。”
“半斤對八兩唄,娶了她,以後家業還不都是自己兒子的,姑娘總是要嫁出去的。”
“哎呀,這有錢人家的心思,猜不透哦。”
“得個便宜閨女,以後彩禮還能撈一筆,這算盤打的,真精細。”
陰腔怪調的議論,灌了周海萍滿滿一耳朵,正要理論,卻被老韓搶了先:“從今往後怎麼編排我都行,說我老婆孩子可別怪我不客氣!”
恍惚間,周海萍告訴自己,嫁對人了。
好不容易去了塊心病,韓琳姥爺樂得當起了甩手掌櫃,將生意完全交了出去,自己奔著頤養天年去了,可人上了年紀,身體就由不得自己,周海萍和老韓結婚後的第二年開始,韓琳姥爺和姥爺就相繼得病,兩個病人,不管對經濟還是人力來說,都是巨大的挑戰。
醫院裡伺候病人,身故後辦理後事,都是老韓領頭撐著周海萍。
拖拖沓沓了兩年,送走兩位老人後,家底也被折騰得差不多了,正好競爭對手又如雨後春筍般地往外冒,建材店的生意一日不如一日,終於走了下坡路。
韓琳十六歲時,周海萍將兩個店面轉了手,折成了現金,娘倆一起搬進了老韓在城中村的兩層小樓,一住就是十多年。
搬進去那天,好多人看笑話,說老韓的算計落了空,本來是想著藉助周海萍孃家的東風飛黃騰達的,沒想到接手了一大一小兩個拖油瓶。
那些話,要多難聽有多難聽,韓琳記得清清楚楚,可當時周海萍只讓她忍著。
家道中落,已經讓人生了嘲諷的心,若是再起衝突,一家都要被置於風口浪尖上,她不願意老韓被人惡意中傷。
屋漏偏逢連夜雨,周海萍那頭歇了菜,老韓這兒也好不到哪兒去。
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很多人家裝修新房時都盯上了剛剛冒頭的全屋定製,手工打出來的木門已經不流行了,老韓空有好手藝,卻長時間接不到活兒,愁得額頭都擰巴起來了。
但就是這樣,老韓都堅持不花周海萍一分錢:“賣店面那些錢是你最後的安全感,我不能碰。”
周海萍一邊罵他犟驢一邊嘴角上揚。
韓琳記得特別清楚,十五歲上初二,那年冬天,老韓借了些錢跟人合夥倒騰蓮藕,當時周邊有藕粉加工廠在大量收購,原以為會穩賺一筆,沒想到老韓與合夥人被坑了個底朝天,收了一船壞的,加工廠一斤都沒留下,最後整船蓮藕都被倒進了運河裡,好不容易湊的錢盡數打了水漂,連韓爍開年的學費都攏不起來。
老韓怕周海萍知道會著急上火,偷偷和韓爍商量輟學一年,周海萍看到放寒假歸來的韓爍拎著大包小裹,連蚊帳被褥都捲了回來,這才起了疑心,問出了所以然,周海萍只覺得腦瓜子疼,火爆脾氣一下就竄上了囟門。
“這麼大的事你竟然瞞著我?咱倆是不是兩口子?”
“是兩口子我才瞞你,跟我你沒過啥好日子,我不能再讓你給我填坑。”
“那你就拿孩子的學習開玩笑?”
“這小子成績好,歇一年不打緊。”
周海萍胸口梗得慌:“你要讓韓爍停學,那琳琳就跟著一起停,兄妹倆誰也不吃虧。”
老韓這才不犟了,接受了周海萍的幫助。
打那以後,老韓摳門兒的毛病就落下了根。
用周海萍的錢還了債,老韓一門心思地只想著掙錢存錢,去工地打零工,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手藝不頂用,就只能另謀出路。
正好趕上城鄉建設發展的好時候,樓盤、商場開發不停歇,工地遍地開花,老韓拼著一身力氣,趕場似的做工,水電工、泥瓦匠、油漆工……都學成了個半吊子,手藝不精,但什麼行當都會一點。
工資一到手,還沒捂熱乎,轉臉就到了周海萍的口袋裡。
老韓說,有周海萍把著經濟大權,他心裡才有底,多一分錢都不敢亂花。
起先周海萍不太好意思收,扭扭捏捏的,一來不習慣掌心向上,二來怕韓爍會多想,沒有親媽在身邊的孩子,大都格外敏感,周海萍怕韓爍覺得有了後媽,親爸就變了樣,可時間一長,周海萍發現韓爍完全沒和自己離心,甚至還暗戳戳地站在自己這頭,有時候她和老韓拌嘴,韓爍總是數落自己親爸。
不光對周海萍,對韓琳也是如此。
韓琳升高中那年,韓爍讀大學,揹著父母,韓爍用兼職掙來的錢給韓琳買了一個手機,沒有血緣關係的兄妹倆,經常隔著幾千公里的距離聯絡感情,有時是韓爍揪著韓琳講數學題,有時是韓琳纏著韓爍問他有沒有給自己找個嫂子,就好像親兄妹一般。
日子久了,周海萍漸漸咂摸出味兒來,老韓是隻顧著埋頭苦幹,所有好都在日積月累的沉默中顯山露水,韓爍是另一種進階的好,用實際行動在昭示著,他已經把周海萍母女倆算進了他和老韓往後餘生的歲月裡。
韓琳滿十八歲的那天,周海萍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帶她去派出所改了姓。
一家人,整整齊齊的才好。
那天的陽光很濃烈,周海萍站在派出所門口,回想起自己的半生,才發覺那個曾經傷害過她的男人早已不見了蹤影,就在她和老韓徐徐漸近的感情中,漏進來的全是生命的溫暖。
日子突然就順風順水起來,韓爍和韓琳相繼大學畢業,韓爍被保送直博生,韓琳和幾個大學同學一起創業,也算小有成就。
兄妹倆都在城裡買了房子,想把老韓兩口子接過去住,卻都沒能如願,只能隔三差五地往回打錢,可老韓摳摳索索半輩子,哪還奢侈的起來,次次韓琳打回來的錢,老韓都妥帖地存起來,周海萍笑罵他守財奴,老韓嘿嘿笑,不言語。
周海萍也沒想到,這次因為韓琳要結婚,老韓竟然下了這麼大本錢。
整天忙忙叨叨的,沒個閒時候,還總拉著周海萍給意見,生怕哪裡不周到,讓韓琳在婆家落了下風。
臘月二十八,韓琳大婚。
儀式開始前有一場彩排,一切都很好,流程特別順暢,到了見真章的時候,司儀舉著話筒喊著讓父親將新娘的手交到新郎手中,老韓突然就崩潰了。
韓琳看著面前那個已經微微駝背的老頭雙手顫抖,手心裡還捏著一團溼漉漉的紙巾,交出韓琳的手之後,老韓飛快地從司儀手中拿過話筒,扯著嗓子衝女婿說:“好好對我閨女,她性子嬌氣,是我慣的,有什麼受不了的,你來跟我說,我替你教訓她,你自己不能上手。”
臺下鬨堂大笑,韓琳卻淚流滿面,她知道,此刻的周海萍肯定也如她一樣。
韓琳突然想起,早上韓爍揹她上婚車,快三十歲的大男人,一直念念叨叨地囑咐:“受委屈了就回來跟哥說,哥拳頭練過,硬邦邦的。”
這下所有人都知道,他們是真心實意的一家人。
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