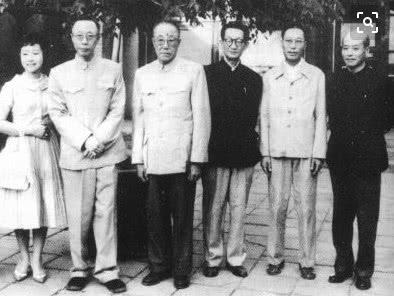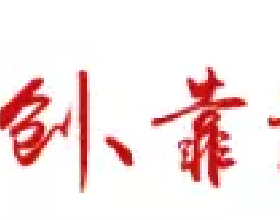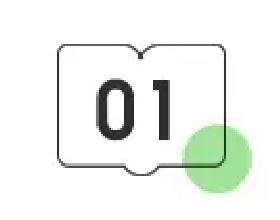1950年6月,被蘇聯紅軍俘虜了5年之久的溥儀,趁著房間裡其他人都不在的空當,一把拉過侄子毓喦:“我決定立你為太子。”
此時溥儀自身尚且難保,他立下的繼承人含金量自然也高不到哪去,可毓喦依舊被這個事實驚住了。他滿腦子想的都是,古往今來,無數人為了爭奪太子地位自相殘殺。如今,這個大帽子“咣噹”一聲砸自己頭上,看來自家祖墳必定是冒了青煙。
想到這裡,毓喦恭恭敬敬跪在地上向溥儀磕頭,喊他“皇阿瑪”。在溥儀的帶領下,兩人鬼鬼祟祟地向著想象中的“列祖列宗”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禮,隨後溥儀又面容嚴肅地強調,毓喦要和他一樣,以恢復清朝基業為畢生目標。
已被幸福砸暈的毓喦,此刻就算溥儀要求他上天摘星星也敢去試試。他不知道的是,就是因為這種完全服從的態度,才被溥儀選中做了他的繼承人。
溥儀身邊有三位近親侄子,分別是毓嵣、毓嶦和毓喦。溥儀在《我的前半生》曾多次提及三人,還親暱地稱呼他們為小秀、小瑞、小固。
毓嵣和毓喦都是道光皇帝第五子勤親王的曾孫,毓嶦則是出名的“鬼子六”恭親王奕訢的曾孫。
三人均在十幾歲便投奔了身在偽滿洲國的溥儀,在溥儀的監督下讀書。溥儀脾氣刻薄寡恩,因為在日本人手底下沒有安全感,又犯有很重的疑心病,動輒就對這幾個侄子嚴厲責罰,或者命他們互扇耳光。
三人中,溥儀原本最看好的人是毓嵣,他頭腦靈活又擅於待人接物,綜合素質要比毓喦強上一大截。
可是毓嵣自主意識比較強,隨著時間流逝,他對溥儀的崇拜感越來越淡化,完全瞧不上他為了復辟認日本人作父,甚至在某些方面敢於公開違抗溥儀旨意。
溥儀一向尊崇“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則,按照這條理念,他在戰犯收容所內和幾位愛新覺羅家族的成員經過反覆磋商,最後決定選最聽話的毓喦為“皇嗣”。
毓喦雖然身為愛新覺羅近支成員,但由於父親獲罪被革爵,加上母親早逝,家境連一般人都不如,只好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
恰逢溥儀在日本人統治下過得膽戰心驚,迫切需要一些家族成員時刻在身邊陪伴。他一手操辦了“讀書班”,將近親侄輩網羅過來,想要培養一批對自己死心塌地的親信,毓喦就是在這個時候被挑中來到“御前”讀書。
別看這些侄子們個個出身尊貴,但在溥儀眼裡他們就是不折不扣的奴才,動輒打罵不說,還要強行干預他們的婚事。
毓喦在溥儀身邊陪伴了6年後,姐姐菊英給他介紹了一位在日本人開辦的學校裡念過書的姑娘當未婚妻,溥儀知道後立刻表示反對。他對日本人已經到了神經過敏的程度,親弟弟溥傑的婚事被日本人插手,娶了位日本妻子,雖說是被強迫,但溥儀由此遷怒溥傑,兩人彆扭了很長一段時間。
聽到毓喦的未婚妻說不定也與日本人有瓜葛時,溥儀立刻要他退婚。毓喦對溥儀那是絕對忠誠,儘管內心不捨,依然二話不說退了婚。
溥儀對毓喦的獎勵就是親自為他“賜婚”,命人從北京為毓喦尋了位妻子,在雙方只見過照片的情況下就定下婚事。即便如此草率,毓喦還是對溥儀感激不已。他腦子裡全是舊社會思想,皇帝指婚那可是天大的恩澤。
毓喦在新婚當天都沒回家,兢兢業業為溥儀服務。他有一項重要的任務別人替代不了——替溥儀打針。
溥儀在晚上睡覺之前,每天都需要注射男性荷爾蒙激素。據他自己說,小時候在宮中常常被宮女把玩男根,結果得了嚴重的陽痿。據說注射激素可以治療此病,因此他常常寫條子要人到天津、北京等地購買此藥。
溥儀對注射器和注射人要求極高,注射器必須消毒徹底,注射人員必須是絕對可信賴的人才對。經過反覆篩選,他選中細心忠誠的毓喦擔此重任。
為了完成任務,毓喦在洞房花燭夜的時刻,也是苦熬到晚上12點,給溥儀打完針後才與新婚妻子共度春宵。
1945年日本人潰敗,溥儀逃到瀋陽機場時被蘇聯紅軍俘虜。不論是在蘇聯的5年拘留生活中,還是被押送回國後,毓喦都對溥儀不離不棄,幫他洗衣服給他打飯,不枉溥儀立他為繼承人。
誰知回國後不久,這位最老實巴交的侄子,居然寫條子給溥儀,稱自己打算向管理所舉報他。
事情的起因在於溥儀那隻走哪帶哪的黑箱子。溥儀逃亡時,帶上了很多貴重珍寶,為了躲避搜查,特意命一位心靈手巧的侍從李燾在裡面做了個夾層,把珠寶藏匿其中。
由於夾層做得巧妙,這些珠寶巧妙躲過了各種檢查。溥儀將黑箱子看得十分重要,可能在他的想法裡,萬一將來還有復辟機會,這些珠寶可以作為活動經費吧。
而毓喦經過一輪輪的學習,思想上有了很大進步。雖然溥儀是他名義上的“皇阿瑪”,但他下定決心,向所方檢舉溥儀藏匿珠寶的事情。
管理所所長經過慎重考慮,決定裝做不知道此事,讓毓喦寫個條子給溥儀,希望溥儀自己能想明白這事並主動交待,否則他被動交出珠寶的話,對其思想改造毫無用處。
溥儀收到條子果然驚懼惶恐,經過了10天的慎重考慮後,他主動上交珠寶並承認了錯誤。這起事件在他的改造之路上是一個里程碑,從此,溥儀原本端著的皇帝架子徹底放下,開啟了真正的思想改造歷程。
1957年1月27日,毓喦等13人被免於起訴直接釋放,臨走前,他看到默默無言的“皇阿瑪”,走上前耐心安慰他,溥儀只“嗯”了一聲,便不再說話。
毓喦返回家中時,家裡場景十分淒涼,妻子馬靜蘭在9年前就已經去世,兩個兒子恆鎮、恆鎧跟著他的叔母生活,暫時棲居於堂妹家裡。屋子裡唯一的傢俱是一張木板床,兩個孩子只能睡在磚地上,穿著打扮連街上的乞丐都不如。
毓喦這時也沒找到工作,厚著臉皮在堂兄家裡蹭飯。沒有經濟來源總歸不是辦法,為了應急,他咬牙將溥儀送的懷錶和白金錶鏈賣掉。
在堂妹的幫助下,毓喦在西城區業餘學校裡謀得了一個代課老師的職務,每月十幾元的工資只夠吃鹹菜和窩頭。因為表現優異準備進一步轉正時,領導看完他的履歷表卻愣住了。
當上級領導得知毓喦竟然是跟隨偽滿大漢奸溥儀20幾年的立嗣之子後,他的轉正夢想隨之破滅。
後來毓喦輾轉來到天堂河農場工作,他邊勞動邊掛念著溥儀,工作了一年多後,他聽說溥儀已經特赦並回京,立刻來到溥儀的五妹家裡去見他。
看到正在椅子上坐著的溥儀,毓喦犯了難,該怎麼稱呼他呢?“皇上”、“上邊”、“皇阿瑪”?怎麼叫好像都怪怪的。突然毓喦靈機一動,喊了聲“大叔”,溥儀開心地應答後起身與他握手,還連連招呼毓喦趕快坐下。
可別小看溥儀的這些舉動,在以前,他是唯我獨尊的皇帝,對待毓喦連個笑模樣都沒有,更別說喊他坐下喝茶了,從小細節可以看出,溥儀的改造非常成功。
一個星期後,毓喦再度去探望溥儀,得知他在崇文門內的一家旅館集中學習。毓喦好不容易才上到二樓,迎面跑來的竟是自己的兩個兒子。
原來,就在毓喦外出工作期間,溥儀已經喊小哥倆來玩了好幾趟,他這裡有吃有喝,其他一起學習的人員也常常給小哥倆糖吃。
在溥儀的前半生,他兇殘多疑,認為所有人都是自己的奴才,絕少有溫情流露的時刻。自從特赦後,他再也不掩飾心中的好惡,對小孩子的喜愛之情噴薄而出。
溥儀自己沒有子嗣,他在心中把毓喦當成了親兒子,毓喦的兩個孩子就是自己的孫子。於是溥儀給兩個孩子好吃的,還陪他們一塊做遊戲,也算是開始享受天倫之樂。
溥儀的變化之大簡直令毓喦感到驚詫。有一年春節過後天氣寒冷,毓喦得了重感冒引發高燒,獨自一人在薄薄的木板床上哆嗦。
恰巧溥儀前來看他,見狀立刻扶著他走出衚衕口,倒了兩次車看醫生。他深知毓喦生活窘迫,所有看病的錢都是自掏腰包。回家後毓喦反覆想:“這還是以前的那個溥儀嗎?他的變化簡直太大了。”
1961年,溥儀當上了文史專員,每月可拿100多塊錢的工資。薪水雖然微薄了些,但溥儀很高興自己擁有了正式工作,總算可以發揮餘熱。
到了吃飯時間,溥儀帶毓喦前去食堂吃午飯,誰知毓喦卻出了好大的醜。
當時屬於三年自然災害,毓喦身為重體力勞動者,每月口糧卻由60多斤縮減到30多斤,飢餓已經成為常態,臉上、身上都出現了浮腫。
一聽說吃飯,毓喦立刻露出了饞相。溥儀見狀笑呵呵地說:“今天讓你吃個飽。”
“我是一個大肚漢。”毓喦抻著脖子衝溥儀喊。
溥儀買來十分豐盛的菜餚,引來大家的紛紛側目。烹對蝦、溜肉片、奶油菜花,還有5個花捲,都被毓喦餓狼似地填進肚中,溥儀只是吃了幾口菜和半個花捲。
眼見毓喦沒有吃飽,他又去視窗買了兩個花捲和兩樣菜,自己卻餓著肚子,這次款待令毓喦終身難忘。
1964年初,溥儀發現尿中帶血,經診斷後在膀胱中發現了癌細胞。也許他的內心對死亡是恐懼的,但從表面上絲毫看不出來,還樂呵呵地參加各種社會活動,毓喦的婚事他也記掛在心。
說起毓喦的婚事溥儀就有些愧疚,毓喦的第一次婚姻是他給強行指定的,在此之前小兩口連面都沒見過。
毓喦自打妻子去世後,再婚一事始終阻礙重重,這也是沾了溥儀的“光”。只要對方聽到他和溥儀關係密切,婚事便會告吹。
好在張雲訪不嫌棄他的過去,主動與毓喦結合,也算了卻了溥儀的一樁心事。
溥儀今生最大的遺憾在於無子,他平生喜歡小孩,曾想過繼毓喦的一個兒子,後來因為輩分等種種原因只能擱置。
1967年,毓喦前往人民醫院探望重病的溥儀,他察覺到溥儀臉色很難看,眼睛中透露著茫然,還隱隱犯著呆滯。在毓喦起身離開時,溥儀執意送他到門口,毓喦走出去很遠,溥儀那消瘦的身子還在門口張望著。毓喦心裡“咯噔”一下,擔心這是二人最後一次見面。
1967年10月17日,毓喦得知溥儀去世的訊息後,把自己關在屋裡足足哭了一天。他與溥儀相處了30年時間,前20年是在惶恐中度過,即便被立為“太子”,見到溥儀也是膝蓋發軟。溥儀特赦後,二人才開啟了真正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既像父子又是知己。
1980年5月29日,毓喦參加了溥儀的追悼會,他恭恭敬敬地對著骨灰盒三鞠躬,內心為溥儀做了祈禱:“願您在天之靈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