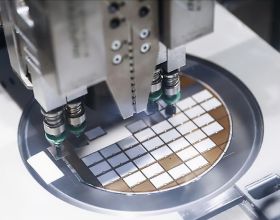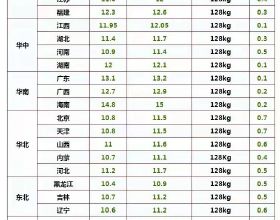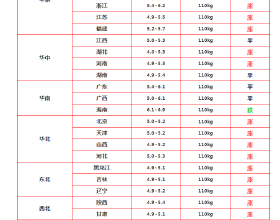黃 海/文
我出生落地的屋子,早已不復存在,曾經居住的人也零散飄落。這屋子決定了我的家世身份,影響到我的性格養成。
我的先輩隸屬京山縣孫橋黃家大莊園,但並不和黃家大莊園同房頭,我的先輩在黃氏家族五個房頭中的麼房。家族裡那些風雲人物,我都沒見過,這個家族新中國成前我沒出生,新中國成立後只知道兩個和我同輩分的人被鎮壓,其中最為流傳的是黃熙楚,他在抗戰期間,積極抗日,也是做過一些好事的。最值得講一講的,就是救美國飛行員的故事了。這位美國飛行員是美軍空軍飛虎隊隊長克萊爾.李.陳納德屬下的莫浩南少尉。他在對日空戰中飛機毀在官橋鋪境內,跳傘後的飛行員被黃熙楚所救,並送往老河口軍用飛機場飛回美國。特別是在縣文化館一般人馬在那裡造就了一個“四百年罪惡之家”黃家大地主,這個家族才在我心中名聲鵲起,我所知道的家族史也就是當地的傳說和文化館的宣傳。
黃家人的興衰在黃家嶺歷經了二十多代。
明代中期有兩戶黃姓人從江西遷入湖北,一戶定居在鍾祥的柴胡,一戶定居在京山的官橋鋪,這一家主人是黃家在黃家嶺的第一代世祖,經歷了四代單傳,第五代繼承人黃振邦娶了三個太太,生了五個兒子,並且五個兒子都有功名,黃家就興旺發達起來了。大約在十六世紀中葉,黃家就已聲勢顯赫,家資豐厚。主人黃振邦飽讀詩書,寫得一手好文章,並且樂善好施。此後黃家立為五大房頭,興旺了四百餘年,傳承了二十多代。
黃家在第5代發家後,以後幾代都有人為官:巡撫、武都尉、陝西錢糧主管等等。優厚的俸祿與豐厚的地租,激發起黃家買田出租的慾望。黃家土地阡陌縱橫,地跨鍾祥、京山、天門、應城等縣,多達十萬餘畝。黃家一個房頭的田產就有26600畝,是四川大地主劉文彩的3倍。黃家在孫橋、石龍、楊集、三陽等地都設有多座糧倉。
黃家人的大莊園夢想在第9代身上終於變成現實。這位第9代孫,人稱武舉三大人,他身高2米,膀圓腰粗。他為保國安民立下了功勳,於是,皇帝賜假一年,讓他回家省親,興修大莊園。他早在三年前就請北京的建築專家繪製了圖紙,從江西運回了上等石料,從湖南購進了湘杉,從全國各地募集了各類能工巧匠一百多人。在黃家嶺周圍開了18個窯場,燒製了各類磚瓦。
1835年8月正式動工,每天工地上車水馬龍,人聲鼎沸,接號上工,鳴鑼開飯。先建正屋,三年建成,接著又做側屋,歷時五年竣工。建築面積二十畝左右。正屋房間無人計數,並排建七個大朝門,其中最大的朝門內有天井18個。民間傳說黃家建了48個天井的大莊園,是把正屋和側房大大小小的天井都算在內了的。門上雕龍畫鳳,刻有百鳥朝鳳,獅子滾繡球;門棚上各雕刻著一曲戲劇,各種不同身份的人物惟妙惟肖;大門口還有石鼓墩、上馬石、拴馬環;門兩側有二龍戲珠雕塑,龍口中的石珠用手滾得動,落不出,還有石馬槽,每個馬槽長五尺,寬兩尺,兩頭雕有石猴守槽,可供拴馬;屋上裝飾著各類花卉,有斗大的空心花飾,有如寶石的綠瓦屋脊。這精美絕倫、恢弘軒昂的建築群,集當時國內建築、繪畫、雕刻工藝之大成,展示了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人們稱之謂京山的大觀園。
可惜的是:1930年,正屋被楊集磨棋嶺的一夥土匪給燒燬了。建國後只留下了側屋,共有5個天井,50多米的進深。即使僅剩的側屋,在“文革”時期作為階級教育基地時,參觀的人們也沒有不嘖嘖稱奇的。
我字輩為楚,我們這一輩是這一字輩收尾,所以我們的名字楚字放在姓名末尾。在我們這一輩後面,還確立了十六代字輩:“在福源遠,志安澤長,繼啟先緒,為善必昌”。但現在知道的人可能極少了,按字輩分改名字的更少了,怎樣好聽就怎樣樣改,更是在“階級鬥爭為綱”的時期,黃家的後輩們都怕戴上剝削階級的孝子賢孫帽子,惟恐劃入了階級敵人之列。
黃家祠堂位於楊家嶺,黃氏家族一年一次的在這裡舉行黃氏宗祖的祭祀活動, 對於黃氏家族來說,鄭其事地騰出這一天,一年一度。
祠堂前近百米長的鄉道,紅毯鋪地,彩旗獵獵,綿長的祭祀隊伍,比春節玩龍燈還壯觀。前後人頭攢動,在那些香燭的煙霧裡,有過去、現在、未來,生命在此無數次地繁衍、延展。祭祀後,祠堂三百桌長宴,一條熱騰騰的長龍,那些先輩們在酒氣中穿梭,空氣被古老靈魂浸潤。所有的黃氏宗族人,被一種力量招喚而來。
對於多數人來說,祖輩的精神根系,有植物一樣的生長力量。
黃家祠堂毀於日本鬼子,侵略者用八輛大卡車拉著八根柱子,毀掉了壯觀的黃家祠堂,用到修築清官祠的工事。
這個家族有富也有窮,土改時我家定為自由市民,複查時我五叔是當時的村長,由於他的提議,父親劃為工商業地主,這個家庭成分影響了我的半生,我的青蔥歲月就在那歧視、屈辱中度過的。
五叔一生都是窮困潦倒,我沒見過嬸孃,他家只有一個大我幾歲的堂兄,堂兄在冬天也是赤腳上學,十八歲時找了個女朋友,有一次他爬上樹為女朋友摘柿子,不幸從大樹上落下來結束了年輕的生命。從此五叔就孤身一人在世上度過了一生,晚景十分淒涼。
我父親在官橋街上黃金地段擁有一棟很像樣的房子,在那裡做生意。那是一座“天井式”民居。古樸的八扇大門、雕龍刻鳳的石墩和厚重的青石門檻,顯得肅穆莊嚴。“毫不利已,專門利人”的楹聯和牆上的“毛主席語錄”,承載了歲月的風華。一進大門是前堂,一扇平時不開的龍鳳門作為門壁與天井、正堂隔開,門壁上的各式木雕竹刻在文革時已被削平了。那三進兩出八間的屋子曾是我的人間聖殿,歲月澱積的深厚文化營養層,把我培育成苗,然後移栽到風雨如晦的曠野山谷。
在這裡,我熟悉了小街人的鄉土生活,也熟悉父母親的生意生涯。這屋裡,我感受到了先祖受到的敬仰與追崇。過年過節敬神拜祖,焚香化紙,充滿了誠摯。他們祈求安穩的現世,充滿敬意,這更讓人感動。我也領略了農村人婚喪嫁娶習俗的親和。
父親做生意,也種了部分田,由於是工商業地主,做生意的老宅沒有分給別人,我們安居在這老宅裡。小街大都是生意人,但他們都有田地,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稅率定的很高,很多人放棄了做生意,轉入種田,我父親沒有,他堅持下來了。接下來的公私合營,讓父母成了公家人,成了職工。小街人也分成的商品糧戶口和農業戶口兩個陣營。
我家老宅在公私合營後成了公家的,說是入股分紅,卻從來未有過,我們居住在少數幾間房裡,其他房充作公用,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落實政策才歸還我們,姐姐全家在此居住,後姐夫也落實政策全家到了孫橋居住,留下這老宅無償的讓別人居住,借住人不但不修理,而是下瓦賣錢,折椽為炊,最後終於倒塌了。
我們離黃家嶺看似很近,卻又遙遠,黃氏家族分了五個房頭,我的祖輩是麼房,除共有一個祠堂外,這個房頭可能不怎麼發達,不然我父親怎麼會沒讀過書?據他說他字墨算盤全是自學的,不說成材,但在當地也算是文化人。
隨著寒來暑往的歲月變遷,那些能舞弄筆墨的老族人和風雲人物早已化為黃土,能講述黃氏家族片斷歷史的唯一老人黃大存,他已八十多了,但按輩分他是我的侄輩人,好在他身體尚健,頭腦清晰,再加上他父親是黃家管家。最難能可貴的記憶力如此清晰,不知道他怎麼還儲存有些資料。
花開水流,歲月無聲。一不經意幾十年過去了。我一直紮紮實實,平平靜靜,沒有野心,沒有怨氣,波瀾不驚地做事為人。正正直直地做人,毫無卑屈地做事,雖無富貴,也貧賤驕人。這也許是利益於鄉風民俗的薰陶與浸潤。
無論多麼遙遠,過去的時光會留下一些殘跡,像我們的老宅一樣,留在記憶里根本不能剔去。
可是那些往事,無論是驚駭世俗還是平庸瑣碎,無論你莊重肅穆想起還是淡然地忘記,它們都毫髮無損,偶爾復活的甦醒,在你的夢想裡,記憶裡歡愉的重現一下,然後迅速消失。
我何不審視昨日的自我,更加滿懷激情地融入今日這沸騰的大海,風雲齊匯的天空。
2021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