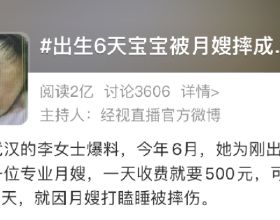安徽的小巷裡,一片鑼鼓喧天的熱鬧景象。陸家最美的小姐,今天就要出嫁了。
坊間許多人戲稱這位陸英小姐叫“小林黛玉”,父親是鹽官,家住揚州,生得貌美,滿腹才情。但陸小姐看似要比林黛玉幸運得多,她嫁的人是洋務派張樹生大人的孫子——張武齡。
郎才女貌,門當戶對,街上的人紛紛拍手叫好。就是這樣的熱鬧聲中,一位滿頭銀髮的老嫗,像是一位冷眼旁觀的看客,說了一句話:“月盈則虧,水滿則溢”。
她渾濁的雙眼,彷彿看透了這位小姐的命運,而這句話,許多年後,倘若陸英真的想起了,恐怕也會覺得一語成讖。
轎子搖搖擺擺,陸英年輕的面龐和頭上戴的紅花一樣嬌豔,她就這樣走向了她一生的桎梏和枷鎖,也走向了她今後充滿未知的命運。
婚後,陸英覺得自己無比幸福。張武齡正如她所料,是一位溫潤如玉的翩翩君子,對她關懷有加,無微不至。很快,他們就生下了第一個孩子。
粉雕玉琢的女兒,名叫張元和。年輕的小夫妻抱著這個可愛的女兒,今後的日子好似充滿了希望。旭日的暖陽,在正午時分,短暫地穿過了重門緊鎖的大院,照到了一家三口的頭上。
很快,陸英就生下了第二個孩子,但還是女兒,接著第三個,第四個,接連出生,但全都是女兒。陸英此時並不知道,這四個被眾人指點非議的女兒,就是此後風華絕代的合肥四姐妹。
雖然張武齡說生男生女一樣好,可人言可畏,陸英就像賭氣一般的,又懷上了第五個孩子。這才不過是她嫁到張家的第五年,算起來,陸英每年都在生孩子。
此時的她21歲,一個女人最年輕美好的時光,她全在接連的懷孕和生產之中度過了。而她讀過的詩書,所愛的一切文學與美,她全部無法再觸碰。
她是張家的女主人,她要做的是綿延後嗣,要做的是掌管家務。或許只有在深夜,她懷抱著四個女兒時,能把年少時讀過的詩教給她們,權當是為自己做一場美夢。
但陸英或許沒想到,就是這些她認為聊勝於無的文學薰陶,讓這四個女兒都先後走上了做文化的道路。
陸英生下了她的第五個孩子,這次是個男孩。陸英十分激動,她終於爭了口氣,給張家生了一胎男孩。
但好景不長,這個孩子很快就夭折了。最大的女兒現今剛剛六歲,最小的女兒才不滿一歲,丈夫外出忙事業,莫大的院子裡,沒有一個人能與這位曾經的“民國第一名媛”感同身受。
她就這樣守著空空的大宅子,獨自祭奠著死去的孩子。
於是外面關於陸英的傳聞越來越多,說她命硬,剋死了兒子。說她肚子裡沒貨,只能生女孩。
陸英就在這樣的一片非議聲中,生下了十四個孩子。民國1921年,陸英最後一次生產,這一年她36歲。
孩子落地後,陸英一直覺得牙疼,於是張武齡帶著妻子來到了醫院拔牙,沒想到的是一次簡簡單單的拔牙,便要了陸英的命。
拔完牙回到家後,陸英血流不止,於是張武齡又帶著陸英來到了一家更高檔的醫院,這次醫生的診斷是,陸英得了敗血症,時日無多。
陸英回到家中,靜靜地等待著自己的死亡。一層層的簾子,掩住了她蒼白消瘦的面龐。她曾經是風華絕代的大美人,但就在這樣安靜的,陰森的大房子裡,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陸英死前小兒子要來看她,她用虛弱的嗓音說:“狗狗,不要來,媽媽這裡有病菌的。”
她叫女兒大毛,二毛,叫兒子大狗,二狗......就是這樣一位溫柔的母親,最終還是死在了尚在美麗的年華,她甚至至死都沒有見孩子們一面,因為怕自己身上的病菌傳染給孩子們。
幾十年後的張愛玲曾寫過,男人的一生至少要有兩個女人,一個是紅玫瑰,一個是白玫瑰。
張武齡將這兩朵玫瑰都娶回了家,白玫瑰枯萎在了張家大院,溺死在了血泊裡,這朵紅玫瑰,還正在怒放。
21歲的韋均一,正在女高讀書,彼時,她剛剛遇到張武齡。
張武齡此時改了名字,他嫌棄這個充滿封建色彩的名字,他為自己取名張冀牖。他們的初識,是張冀牖的任務,卻是韋均一的初戀。
陸英死後,張冀牖來不及悼念亡妻,就在家人的逼迫下,開始尋找能為他續絃的女人,於是張冀牖找到了韋均一。
張家是書香世家,從小就在文化的薰陶中長大。而張冀牖自己卻不甘心只讀一些之乎者也的舊文章,於是他也乘上了新文化的東風,就是這股東風,將他吹到了韋均一的面前。
韋均一才思敏捷,容貌俏麗,還會唱崑曲。各方面都完美地符合張冀牖的要求,所以她牽起了張冀牖的手,走過那條陸英走過的路,來到了張家大院。
韋均一畢業於上海愛國女中,是當時著名影星上官雲珠的堂姐,所有的一切都奠定了她與張家的不合。
她初來乍到,本想與丈夫張冀牖一起讀書寫字,吟詩作畫,閒下來再一起唱唱崑曲。但沒想到,實際上的婚姻生活帶給韋均一的只有責任。
21歲的她被迫照料陸英留下的十個兒女,而作為長女的張元和,才僅僅比韋均一小了七歲。
21歲的她,並沒有遇見想象中的詩和遠方,等待她的是張家燃不盡的燈油,是這十個兒女哭喊不休的聲音。
於是原本嬌媚可愛的韋均一,像是突然發了瘋一般,開始折磨這十個孩子。她整個人性格大變,率先開始針對的就是陸英的大女兒張元和。
那時的張元和已經十四歲了,相比於其他的孩子,她已經早早有了自己的想法,而無論是自己在新學堂學到的知識,還是父母親曾經對自己的萬般呵護,都讓她無法忍受這位繼母對自己的虐待。
而原本愛護自己的父親,開始變得越來越忙,越來越忙,忙得好似沒時間見她,沒時間見弟弟妹妹,沒時間掏出一絲絲的愧疚給他們和屍骨未寒的母親。
一個是好風憑藉力,扶搖直上九萬里,一個是埋於泉下泥銷骨。張元和本該肆意發芽的少女生活卻被許許多多的恨與遺憾填充。
她不能恨父親,不能恨那個或許發自真心,或許流於表面曾給過她們一些愛的父親。她只能把怨恨悉數加在繼母身上,連同著幾個弟弟妹妹的怨恨,她一把火燒了,燒到這個新來的氣焰囂張的繼母頭上。
韋均一與張元和的關係變得勢同水火,二人從不能坐下好好說話,甚至連見面都不能見,因為一見面就會橫眉冷對,開始爭吵。
矛盾最尖銳時,韋均一懷孕了,就在所有孩子跪在她面前恭賀她,給她磕頭時,韋均一對為首的張元和上來就是一巴掌。
她大罵:“你們是在祭拜死人嗎?是咒我還是咒我的孩子?”雖說韋均一受的是新式教育,但對於舊禮儀她不可能不懂,所以這一切都是她的故意針對。
對於這一切,張冀牖雖看在眼裡,但卻絲毫沒有干涉。
於他,陸英和韋均一,甚至自己的這些兒女,或許都只是他事業上的一些需要罷了。曾經的翩翩少年,就要可嘆停機德,堪憐詠絮才的陸英來配。
現在的大教育家,新文化學者,自然就需要韋均一這樣敢說敢做,洋氣十足的新妻子來配。
自己傑出的事業,惠及了兒女,給了兒女衣食無憂的生活,他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男人,是當代的道德標杆。
周國平的《風中的紙屑》曾寫道:“家裡養的花自殺了,遺書裡寫道,這一生衣食無憂,唯獨缺少愛與自由。”
張家的深宅啊,捧出了這麼一個好人才。但卻將那些花朵,活活悶在了外人看來光鮮亮麗,卻不透氣的玻璃房子裡,由得她們相愛相殺。這些張冀牖是管不了的,他也不想管的。
此時已經身為教育家的張冀牖,還讓韋均一當上了樂益女中的校長。而這所學校,正是張家四個女兒就讀的中學。
相比起六個小弟弟,張家幾個年紀較大的小姐,因為與繼母年齡差得不多,繼母出任校長,無疑是讓她們本就絕望的生活雪上加霜,這位繼母在家和學校之間,“無縫銜接”的管控,讓她們覺得無比窒息。
元和甚至認了宿舍的舍監阿姨做乾孃,只因為那位女士在元和生病的時候給她熬了一碗紅糖,陪在她身邊。
這一切韋均一都看在眼裡,恨在心裡。元和的這一做法,就等於向外宣告了她對繼子女不管不顧。於是她與這四個女兒之間的關係每況愈下,更加惡化。
不久後,韋均一生下了自己的孩子。或許在這一刻,她能跟陸英有著片刻的相同感受。抱著懷裡可愛的孩子,能想到那些每天被她惡語相加的女孩也不過才十幾歲。
想起這深宅寂寞,她們的母親也經歷過。
但是韋均一不是陸英,陸英從呱呱墜地開始便被教導三從四德,怎樣做個好女人,做個好妻子。
韋均一是新時代的女性,她手不釋卷的是莎士比亞和普希金,不是孔孟老莊陳舊的書卷。
所以韋均一沒有那所謂為人母后的“仁慈”,有了自己的孩子後,韋均一就一心撲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再不理會陸英生下的那些孩子。
這時轉折出現了,四姐妹裡最小的一個妹妹,名叫張充和。因為自小體弱多病,早早地被陸英抱到了親信的李家養育。而這位張家小女兒,一回到家,竟與繼母十分投緣。
充和起初不知道姐姐與繼母的矛盾,見繼母擅長崑曲,充和就向這位繼母求教起來。或許最開始,韋均一也對同為陸英所生的充和十分提防。但說到底,她們之間左右不過差了十多歲。
青蔥年華的充和,與三十出頭的韋均一,二人不像是母女,倒十分像一對興趣相投的姐妹,短短的時間內,橫亙在韋均一和張家姐妹之間的堅冰彷彿出現了裂痕。
充和自小在別處長大,當充和還是七八歲的孩子時,她的姐姐們就知道這個妹妹和她們不同。她們承認小妹妹的學問根基更紮實,也更有自信,就連充和寫的詩歌也更新穎且富於原創性。
這一切或許都奠定了,她與韋均一的投契。她們坐談,談崑曲,談學問,談韋均一曾經驕傲與輝煌的一切。那時,那種歷經滄桑的新鮮與活躍,彷彿重新照進了韋均一的生命中。
與惡龍纏鬥已久,自身已成為惡龍。
或許韋均一在這深宅與當家主母的枷鎖中,掙扎太久了。將她本身豐滿的羽翼,磨損得髒兮兮的。她失去了少女時代眼睛裡的光,只想透過權力的碾壓,得到眾人的臣服與尊重。
但她忘了,這些女孩也都是飽讀詩書,上過現代學校的女青年。她們雖然在舊式家庭中長大,但思想要比其他同齡人先進千倍萬倍。
韋均一是現代女性,卻拿起了舊家族的重拳。張家姐妹在舊家族成長,卻始終堅持著現代那種反壓迫的剛毅。
看似諷刺,但這一切都是一場無可奈何的悲劇。
好在充和的出現,就像她們之間的一座橋。充和寧靜的童年,帶給她的是深度的思考。她可以理解姐姐們,也可以理解這個繼母。充和用自己的方式破冰。這是一種高階的智慧,也是一種高尚的善良。
不久後,充和考取了中國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而二姐允和,在這時嫁人了。
允和作為四姐妹中最具反抗精神的孩子,嫁給了著名的語言學家周有光。允和從小就有著一股衝勁,相信自己能夠戰勝生活中的一切困難。教室關了燈,自己就在昏暗的月光下苦讀物理生物。
這些剛剛傳入中國的先進知識,允和手不釋卷。她不認為這些東西晦澀難懂,反而看到了科學的魅力。
允和與韋均一的關係,在曾經也算得上是針尖對麥芒。嫉惡如仇的允和遇上了強權勢重的韋均一,二人自然是爭執不休。
但現在,作為母親角色的韋均一,輕輕地撫摸著允和潔白的頭紗。她彷彿霎時間的,看到了從前的自己。自信,陽光,充滿了生機與活力。這種丟失已久的東西,變作了一束光。
從張允和的眼睛裡照向了韋均一,她此刻,彷彿找回了當時捧著課本,坐在愛國女高的長椅上,揹著那頁《草葉集》的自己。
韋均一真的找到了平衡,在當家主母和真正的30多歲的韋均一的平衡,在對待姐妹們,母親與知己之間,角色的平衡。
在這一刻,居住在張家大宅裡十多年的韋均一突然領悟到了,曾經陸英心裡的感受。那種為人母的仁慈,她也終於不吝惜地給了陸英留下的這些孩子們。
不久後,與她矛盾最尖銳的元和也出嫁了。命中註定般的,元和嫁給了一位崑曲大師,當時名滿中國的顧傳玠。這對爭吵了十多年的母女,最終在咿咿呀呀的崑曲聲中,帶著微笑和解。
造化弄人,實在有趣。當初,元和聽著父親與繼母新婚時,一起唱曲彈琴,心中是何等悲涼。
現在,元和彷彿也能夠理解當初的他們了。新婚燕爾,錦繡年華,元和自己,要比繼母幸運很多。
和解二字,說難也難,說簡單也再簡單不過了。或許很多時候,就在那一剎那間,放下了自己許許多多的執念,將眼前的事物,代入到自己生命中不曾想起的角落,輕輕地,便與偏執的自己和解了。
韋均一人到三十了,這大好年華,她實現了和自我的和解,和命運的和解。
她太過於不幸了,四個姐妹三十多歲時,正在叱吒於自己的領域,韋均一卻在這深宅生兒育女。但她也太過幸運了,她真真實實的領悟了一些真諦,讓她此後的生活,竟有種寧靜而安詳的慈悲。
後來,三妹張兆和嫁給了著名的文學大師沈從文,四妹張允和嫁給了德國漢學家傅漢思。
葉聖陶說:“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
她們確實幸福了一輩子,陪丈夫走過風風雨雨,在自己的領域有了一番成就,成為了堪比“宋氏三姐妹”的“張氏四姐妹”。
她們對於自己的繼母,是有複雜情感的。
恨,或許有吧,但隨著時間與彼此的和解,早已煙消雲散。
愛,談不上,終究不是親生母女,韋均一代替不了她們心中最愛的母親陸英。但她們最終,還是能夠相互理解了,她們理解了那位對她們橫眉冷對的冷酷女人,也曾與她們一樣,笑顏如花的綻放生命的光。
她們與繼母,繼母與她們,本身就是互相折磨,互相傷害,但彼此扶持,共同成長的良師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