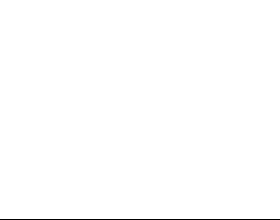人到中年情最弱
秋水
不知天生愚鈍、感知笨拙還是生小出野裡的原因,亦或是對父母依賴性太強吧,總之,從我有記憶開始,就始終覺得父母親是中年人,是能夠擔得起生活所有重擔的中年人,雖說母親生我這個家中老四的時候才28歲,父親32歲,但我印象中父母沒有年輕過,我也從沒有想象過父母親青春的樣子。
為生活而奔波,為孩子而操勞,這就是他們的人生動力;天塌下來他們能撐著,地陷下去他們能扶著,這就是他們的力量;每天面朝黃土背朝天,偶然得病一包頭疼粉,這就是他們的韌性;給兒子找個好媳婦,給女兒嫁個好人家就是他們的人生理想。除了衣食之憂,他們的生活目標和軌跡似乎很清晰。雖然我不知道中年的父母內心是什麼滋味,但我知道父母親就是我們的一片天,我們就是父母的全部世界!
可是當自己被歲月推到了中年的列車上時,我才發現自己的中年居然是如此的脆弱凌亂,顛覆了“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的傳統觀念,三十歲變動單位,事業上還是菜鳥一隻;四十歲時,生活也是一團糟,與年齡不符的天真幼稚成為別人的笑柄;將近不惑之年,依舊想著詩和遠方,逆天而行:用半生努力換得的是眼前的苟且。自己的中年如一瓶老窖,裝滿零星的歲月,只合自斟自飲,稍不留心就粉身碎骨,一切全無!
其實,我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中年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反正有父母在,我始終感覺自己就是一個孩子,任性是難免的,頂嘴也是常有的事,甚至都沒有感覺到哥哥他們早已進入了中年,因為父母就是我們的大樹,我們隨時可以依靠,我們就如一隻只外出覓食的小鳥,困了、累了就回到父母這棵大樹上棲息。父母就是我們的一把巨傘,我們只管享受藍天白雲,一旦天有突變,他們會隨時為我們遮風擋雨。生活中我們沒有什麼真正的壓力,一切都按照周圍人的生活軌跡按部就班地進行著。
2015年11月28日下午,突降的災難讓我頓時束手無策,面對中風的父親,我猛然間感覺我的天空塌陷了。也許就在那一刻,我才猛然意識到我已經真正地步入了中年:父母這棵大樹正在慢慢老去,已經扶不起我們沉重的生活了,父母這把巨傘也已慢慢破舊,很難遮住狂風亂雨了。
但是當我想給父母撐一把傘的時候,發現自己手裡居然沒有傘,面對狂風暴雨只能陪著父母在風雨中煎熬。
每天在學校除了上班就是獨自在房子流淚,週末回家就是陪著父親笑,暗夜中還是獨自流淚。喜歡仰望星空的自己終於明白自己的生活原來很清晰,家和學校就是我的一切。
整整半年多的時間,我將自己泡在淚水中,試圖用淚水清洗傷口,可是淚水只是鎮痛劑,悲痛如極地冰川般堅固,自己除了隱忍別無選擇!無助中我也終於意識到自己已無枝可棲,無路可退!
於是選擇了置身茫然,寂寞荒野,埋頭工作。偶有閒暇,我便“躲進小樓成一統”,將自己按進了古典誦讀中,起初只是想用聲音麻醉自己,遠離熱鬧,暫得片刻寧靜,用文字溫暖自己。不知不覺中感覺自己又似乎觸控到了先賢孤寂的靈魂,體味到了“古來聖賢皆寂寞”的沉重,感受著“悲憤出詩人”的倔強,想象著“獨愴然而涕下”的無助······
我沒有閒情淚眼問花,更無力念天地悠悠,也不渴望絃斷有人聽,我學會了對著文字自言自語,胡言亂語。雖然自己駕馭文字的能力很蹩腳,但卻願文隨心走,無須譁眾取寵,不用矯揉造作。當我開始用文字為自己照亮現實的時候,我終於有了時間仔細回味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所有的愛恨情仇都開始在一個又一個的夜晚變得愈來愈清晰:有些暗香穿透歲月的空曠依舊縈繞在心田;有些冷酷歷經溫情的滋潤終究無法變柔軟;那些欣喜過的期待早已被塵封成為永遠的回憶;那些曾經被辜負的愛卻永遠是自己靈魂的故鄉……
一邊在孤寂時自我擎燭,一邊在閒暇時撿拾歲月,如悲情的祥林嫂,似喋喋不休的八斤老太,目光越來越低,心越來越窄,世界越來越小,將自己揉碎在塵埃中,低眉俯首中常有傷痛,輕描淡寫中總是憂傷,學會了在漆黑的夜晚用一生也不可能實現的夢想來為自己的孤寂療傷。但心與生活貼得更近,筆與靈魂更自由,愛與恨更清晰。
人一旦不會做夢的時候,可能會活得更清醒。生活本就一地雞毛,中年更是一身無奈,生活留給中年的的是想哭的時候必須笑,是無可奈何的灑脫,是每天拼盡全力在原地的奔跑,是羞於提及的苟且······“破帽遮顏過鬧市”就是中年的我的生存狀態。但我依舊會記下風輕雲淡時的小確幸,會寫下陽光細碎時的小溫馨,會回眸激情點綴時的小興奮······
我堅信,自己依舊深愛著這個世界,深愛著深愛我的人,如同我的父母一樣用執著吟唱著愛。既然我無枝可依,遠方就是我的依靠,既然我無路可退,愛就是我的歸巢!
(2021年10月21日)
秋水,本名魏飛,槐芽中學教師。品味經典,汲取先哲智慧;默默寫作,與靈魂對話;用心誦讀,傳遞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