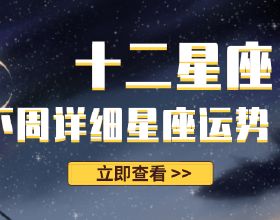作者:蘇枕書
京都有眾多大學、研究所,稱得上學問之都。曾聽一位老師說,有不少大學教授在北部的高尚住宅區安家。他們的太太多在附近私立大學擔任秘書、教務之類的行政職位,又或在某間大學教一兩門課,所謂的“非常勤講師”(part-time instructor),作為優雅的兼職。而在半個多世紀以前,有一位京大助教授的妻子卻堅決拒絕了“教授之妻”的身份,讓丈夫獨自來到京都工作。這就是京都大學法國文學專業出身的作家高橋和子。或許應該強調,高橋是她婚後所冠夫姓,在那之前,她姓岡本。
高橋和子在日本不算知名作家,人們提起她,總不忘補充一句“丈夫是作家高橋和巳”。然而高橋和子是二戰結束後、日本學制改革之初非常罕見的、考進國立大學的女生。比高橋和子晚生16年的上野千鶴子在考大學之前,還被母親說“女兒念個短期大學就足夠了”,因為當時大學畢業的女生不容易結婚,也非常難找工作。那麼,上野千鶴子的前輩高橋和子又經歷了怎樣的學生時代?與高橋和子同樣生於1932年、同於1950年考入京大文學部的東洋史學者小野和子曾回憶:
我入學那年,1500來個學生裡,女生只有28人,其中文學部有15名。因為是新學制剛開始的時候,真的只有非常少的女生考進來。我想著好不容易才考進男女合班的學校,就不要有自己是女生的意識了,於是一路走了下來。(小野和子、上野千鶴子、伊田久美子對談《女として、研究者として》)
1954年,小野和子本科畢業,順利透過公募選拔考試,進入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擔任助教,隨後晉升講師、助教授,在中國史、女性史研究領域奉獻一生,如今依然健在。高橋和子這年三月提交了本科畢業論文《波德萊爾論》,也順利畢業。不過她並沒有像小野和子那樣走上學術道路,同年11月13日,她與高一屆的師兄高橋和巳結婚了。
1954年春,剛剛畢業的和子(左二)、和巳(右一)與同學
高橋和巳本科時留了一年級,因而與和子同年畢業。不過隨後他升入研究生院,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同時,也進行文學創作。為了維生,他在大阪一家夜校打工,教國語課,新婚夫婦便搬到了離工作地點比較近的小公寓。和巳一人的收入難以維持家計,和子也打很多工,做家庭教師,教她很擅長的英語和法語。
那間公寓非常狹小,六疊的居室內有一疊被抬高,是戰後日本復興年代新建樣板間的常見設計,為了安置嬰兒床。和巳則在那裡堆滿了書籍。他一週要去京大兩到三次,其餘時間白天都在家裡伏案工作,晚上去夜校教書。不過夜校的工作只維持了不到一年,1955年春天,和巳辭去工作,夫婦二人沒有繼續在大阪租房住的理由,又搬回京都,住進了和子的孃家。
1955年,搬進和子孃家的和子夫婦
和子是京都人,父親是公務員,母親是家庭主婦,雖不是名門貴族,但也算得上中產之家。而和巳的出身要貧寒得多,他生於大阪,父母祖上都是香川鄉下的農民。父親多病,家裡兄弟姐妹眾多,母親是虔誠的天理教徒——天理教信眾多為貧苦百姓。家人甚至一度不想讓他考大學,因為沒錢交學費。日本傳統家族制度為長子繼承製,長子之外的兒女並無財產權,對貧寒的大家庭來說,讀大學過於奢侈。是和巳流著眼淚哀懇,受到觸動的長兄向母親許諾以後一定掙錢給弟弟唸書,家人這才放他去考試。先是1948年4月考入舊制松江高等學校文科乙類,次年舊制高校廢除,他重新考入學制改革後的京都大學文學部。後來評論家們屢屢稱經歷了戰時與戰後教育方式的鉅變、新舊學制的變革,使得和巳有著與戰後一代人全然不同的“憂鬱”,被本能的反思折磨,既對戰時的國家暴力感到恐怖,又無法接受戰後過於迅速的轉變。
比和巳年輕一歲的和子似乎沒有這種新舊學制更替的“憂鬱”,因為她是從新制高中考進新制大學。她與和巳初見,是1953年夏末。那時她忙著找工作,四處投簡歷,當時戰後復興期的就職黃金時代尚未到來,大學生找工作非常不容易。她去大阪的NHK投簡歷,碰巧遇到了同樣來投簡歷的和巳與他的同伴。這位同伴是和子同專業的師兄,他向和子介紹:“這是中國文學專業的的高橋和巳。”
多年後,和子依然感慨初遇的奇緣,若不是與這位師兄認識,若不是碰巧同一天出來投簡歷,若不是認識了和巳,那麼她的生命歷程恐怕要改寫。和子在回憶裡明言對和巳的一見鍾情,因為他是一位“非常俊美的青年”,很高的個兒,極清瘦。並遺憾他成名後的照片已是中年模樣,臉上長了肉,“很少有人知道,我的丈夫是那樣的俊美青年”:
那是融合了美貌與哲學性的純粹的容顏。眼睛清澈澄明,彷彿超脫了世間的一切。這裡用了“哲學性的純粹”的形容,若是理學部等專業出身,則可以說是“數學性的純粹”。反正不管是什麼專業,沉浸於某種抽象性思維的人,若碰巧長得美貌,就會出現那樣的容顏。當時人們稱大學是象牙塔,符合象牙塔居民形象的有幾種型別,而我說的正是其中一種。(高橋和子《出會い》)
正與和子談戀愛的“俊美青年”和巳
和子在女高時代就幻想過自己以後要嫁給作家,據說是因為迷戀太宰治小說裡作家之妻的形象。《維庸之妻》裡的作家酗酒、欠錢、出軌,而他溫柔忍耐的妻子來到丈夫欠錢的酒館做工還債。為何會主動代入這樣悲慘的角色,和子也認為自己過於極端,或許只是文學少女中二時代的幻夢。而和子對和巳樣貌與才華的傾倒,則無疑是因朦朧的少女之夢有了切實寄託的物件,儘管她很快在婚姻生活中體會到和巳對她的粗疏與剝削。
“剝削”是與她隔了幾十年的我擅自使用的詞彙,她一生都沒有用這樣激烈的詞彙形容過和巳與她的相處,而是靜靜描述婚姻生活裡的細節,男性佔絕對主導地位的文學評論家、作家們絕對不會關心或提及的事:和子為和巳謄抄小說文稿,整理口述筆記,處理各種工作雜務;和子在外打工回來,和巳徑自拿了和子新得的工資,開心地說可以去泡溫泉了,隨後獨自離去,絲毫沒有想到應該帶上和子;和子在外打工,不事生產、專事創作的和巳在家酗酒、大睡;和子與和巳約好一起吃晚飯,和巳拿著家中僅剩的晚飯錢獨自去了酒館……
和子寫過兩本關於和巳的回憶錄,在晚年的日記裡也時不時提及和巳。而和巳的二十卷全集本中,討論了中國古典文學、讀書啟蒙、學園鬥爭、理想破滅、戰後思潮……無數宏大與細微的問題,提到和子的部分卻很少,這使得“和巳眼中的和子”頗難考察。和子曾回憶,和巳對於他們二人的婚姻十分欣喜,認為這是“中國式知性與法國式知性的結合”。我相信這是和巳說出來的話,非常符合他理想主義者的思維模式。
1956年,就職不順利的和子重新回到京大,考入文學研究科法國文學研究專業的碩士班。這一年,和巳提交了碩士論文《顏延之與謝靈運》,升入博士班。兩年後,和子碩士畢業,畢業論文題目是《莫利亞克論》。經歷了研究生院訓練的和子確認自己比起做研究,更憧憬文學創作。當時的日本,京大碩士無疑是社會精英,按說並不難找工作。而和子卻因已婚女性的身份處處碰壁,有一次考過了神戶某法國商船公司的筆試,到面試環節,考官說:“已經結婚的話,從事去外國的業務是不是有困難呢?”她當時如何作答?
“而那時候,我非常看重我的丈夫。”晚年的和子在日記中淡淡回憶,當時和巳已去世多年。
求職失敗的她只好繼續打工養家。這一年,和巳自費出版了小說《舍子物語》,並參加了吉川幸次郎、小川環樹主持的“中國詩人選集”譯註專案,負責《李商隱》一卷。
圖說:研究生院時代的高橋和巳(右三),在恩師吉川幸次郎先生(右一)的研究室,左前戴眼鏡的先生是後來對和巳“三顧茅廬”的小川環樹
1959年,和巳修滿博士課程的學分,提交了博論《陸機的傳記及其文學》,“滿期退學”,沒有拿博士學位。這在博士號非常金貴的年代是常事,當時很多教授都沒有博士學位。不過和巳顯然無意走學術道路,並沒有主動找教職,而開始在文學刊物上連載小說。立命館大學文學部長奈良本辰也欣賞和巳的才華,將他招進立命館擔任非常勤講師,教授現代中國語和文學概論課。和巳算是進入了學術圈,但他遊離於組織之外,很少參加教授會,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文學創作上。這在今天恐怕是很難想象的事,但當年奈良本辰也給了他很大的支援,允許他不參加行政事務,期待他在學術、創作領域都有收穫。
和巳沒有讓師長等待太久。1962年,他的小說《悲之器》獲得第一屆“文藝獎”,意味著他正式被文壇認可,真正進入了作家的世界。和子陪他一起出席頒獎典禮、出版紀念會,被尊稱為“和子夫人”。“作家之妻”的夢想實現了,更妙的是還得到了30萬日元的獎金。
在這之前,他們毫無存款,每個月都為吃飯苦惱。和巳頻繁去當鋪,坦然地跟催債的人說“我沒錢”。和子回憶:“1955年辭去夜校講師,到1960年擔任立命館大學非常勤講師為止,他沒有掙過一分錢。因為自己要做作家,所以毫無理由靠做無聊的事賺錢。”和巳終於靠不無聊的事賺了錢,《悲之器》很快被TBS改編成電視劇,NHK也找他寫廣播劇,電視大學找他開“現代小說的課題”的講座,和巳一時成為文壇、學術界的明星。
和巳在文學上的成功讓和子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她渴望去文藝生活更豐富的東京,開始嘗試練習小說,並接觸到文藝圈的種種名流,拜會了一直敬佩的作家遠藤周作。也給幾個文學獎項投過稿,但都落選了。
1964年,和巳辭去立命館大學的工作,決心到東京專心從事文學創作。次年,夫婦二人買下鎌倉的一棟舊樓,搬離了京都。在和子的文章裡,不止一次提及對京都的厭惡,認為那是男尊女卑的封建世界,男人們無視藝伎和酒吧媽媽桑之外的一切女性。她沒有明說“男尊女卑”的具體情節,而和巳則評價過“京都是文學的不毛之地”,認為這裡的學問雖然有遠遠凌駕於東京的部分,但在文學創作方面近於空白。並有一句耐人尋味的玩笑:
京大極嚴格的實證主義學風與文學青年的氣質非常不合。如果讓太宰治到京大中國學專業來唸書,恐怕在他文學創作方面取得成績之前就已經自殺了。
種種證據表明,和巳是純正的文學青年,他選擇中國文學專業的原因與倉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迷戀中國傳統學問的前輩不同。和子回憶雲:
他曾明確對我說過:輕薄之徒都去唸了法語,我是要去學中文的。他用了這樣的表達,而如今我想的是更為宏大的理由。比起風起雲湧的文學之海——那是強烈的近代式的自我的產物、會將他不確定的“自我”愈加深化擴大,他更想把不確定之自我固定於悄然流淌著悠然壯闊的思想的中國文學中。(高橋和子《いっしょに住んだ、いろいろな住居》)
新婚之初的和子曾拍過一張和巳夜讀的照片,穿著舊和服,執細毛筆在燈下以朱墨圈點漢籍。這是被“京大極嚴格的實證主義學風”薰陶的和巳,到底與他玩笑說的太宰治不同,已熬過漫長的試煉,因此不會輕易自殺。
新婚之初,和子用鏡頭記錄下的和巳,正在燈下點讀漢文
1966年,和巳被明治大學文學部聘為助教授,擔當六朝文學、日本文學的講義與日本文學的演習課。這份工作只做了一年,因為在1966年末,即將退休的恩師吉川幸次郎決定請他回京大文學部中文專業擔任助教授,並請小川環樹親到鎌倉,“三顧茅廬”地請和巳回京都。
這種稀少的“指定接班人”式的榮耀,在京大中國學領域的其他師徒之間,已有不少佳話。然而對和巳來說卻充滿矛盾,一方面他在文壇出道,得到東京方面文藝界名流的諸多支援,比如著名的編輯、《文藝》雜誌的總編坂本一龜。他對和巳寄予厚望,曾經是三島由紀夫的伯樂(他還有個非常有名的獨子,即坂本龍一)。還沒有寫多少作品就回京都,等於是背叛了東京的文藝界。因而坂本一龜大怒,說他回京大等於“坐上了安全晉升的傳送帶”。另一方面,當時苦於神經衰弱的和子根本不想回到“男尊女卑風氣嚴重”的京都。
1967年正月,和子直接給吉川幸次郎電話,非常強硬地說,擅自把好不容易來到東京的和巳拉回京都,我覺得很困擾。我不會去京都,我要跟他分開住,分開住可能導致離婚。
“以中國倫理護身的大學者說:夫人,請不要說可怕的話。”
——和子這樣回憶吉川幸次郎的反應。這大概是世上所有關於吉川的回憶裡最冷漠揶揄的片段。
在“京都中國學”的傳統與魅力之前,和子的抵抗與東京文藝界的挽留與反對黯然失色。換言之,京都中國學的風氣浸染在和巳骨血裡,他走得再遠,都不能逃離這種咒語般的召喚。和巳曾剖析自己對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的感受與身處其間的撕裂感:
寫一頁文章,好比在肉體上釘一枚五寸釘。做學問雖辛苦,但可以收穫切實的積累之感與進步之感。與之相比,創作中時常有直面虛無的勞作,然而其中也有無可替代的自由天地。一旦嘗過這樣的滋味,作為自由的代價,就會被刻上一生無法磨滅的罪惡烙印;想要從當中完全逃離,恐怕是不可能的。(高橋和巳《樂園喪失》)
和巳不久便答應恩師回京大工作。未受儒家倫理洗禮、代表“法國式知性”的和子確認過這點,立刻在這年春天獨自去法國散心,並一直住到了九月末。妻子的出走令和巳非常震驚,沒有人幫他打包書籍,也沒有人幫他用報紙包好杯盤碗盞,得獨自去京都找房子……這一切都令他痛苦。
就在和子漫遊歐洲的時候,和巳受《朝日Journal》之邀,以特派員身份訪問了中國。他們第一站到香港,隨後是廣州、上海、南京、天津,最後抵達北京。這是和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來到中國,是他早已在古典詩歌中想象了無數次的國度,雖然眼前的風景已與古詩裡的有所不同,但他懷著深切的愛眷和好意看待這一切。並買了當時流行的軍裝、軍帽作為紀念,有些羞澀地穿在身上。
1967年4月24日,在北京機場,離別之際唱起中文歌的和巳
回日本後,他寫下了《新長城》,在《朝日Journal》上連載了四期。這年六月,他入職京大文學部,成為助教授,借宿於京大農學部東側的北白川追分町六號。
1967年4月22日,高橋和巳在長城上
1969年10月,高橋和巳在京都病倒,很快回到鎌倉。雖多番就醫,卻未確診。次年四月中,因腹部劇痛住院,最後在東京女子醫大消化器疾病中心確診為結腸癌。和子向和巳瞞住病因,期待手術可以痊癒。術後的和巳確實大有好轉,但這年12月,癌症復發,癌細胞轉移至肝部,和巳再度入院。
和子往返於東京、鎌倉之間,無微不至地照顧和巳。種種權衡之下,她決定向和巳隱瞞病名,只有極少數至親知道。
去醫院的途中,她給和巳買各種好吃的。甘慄、雜煮、豆腐、煮蘿蔔、壽司……有時是從家裡煮好蔬菜鍋帶來。病程進展迅速,敏感的和巳覺察出死亡臨近,卻仍想著等出院了,跟和子一起搬到陽光充足的屋子裡去住。臥病時最愛看旅行、園藝、釣魚之類的雜誌。
“病好了的話,想一整年都不工作,想去釣魚……若是病好了的話……”
和子記錄下他的心願,在病房裡當著他的面聯絡了好幾家不動產公司,詢問一些房子的具體資訊,彷彿離出院搬家的夢想更近了一些。
春天來了,和子隔三差五買來花束。桃花枝,白色鬱金香,白水仙,大捧雪柳枝,繡球花。季節悄然變換,和巳的生命逐漸透明。
“想在院子裡種樹、養鳥,一直休息到四十四、五歲……誰也不見,靜靜過日子……”去世一個多月前,他向和子描述理想。
去世前一天,他痙攣、呼吸困難、極度貧血,陷入漫長的昏迷。埴谷雄高與坂本一龜來探望,帶來了康乃馨與芍藥。他們是東京方面給了和巳最多支援的前輩、摯友。
1971年5月3日深夜,和巳去世。1973年7月,坂本一龜主持的《文藝》做了高橋和巳追悼特集,和子公開了《臨床日記》,從1970年12月21日和巳病發住院,記錄至臨終,最後一段是:
時近深夜,呼吸突然拉長,氣息逐漸微弱,乃至氣絕。十時五十五分。不知道自己的病名,夢想著不可能的時間,丈夫的生命就這樣結束了。是安詳的樣子。
像夢一樣,和巳結束了四十年的生涯。就在前一年11月25日,人們才經歷了三島由紀夫的自殺。和巳在文學界固然沒有三島由紀夫的盛名,但他一度也被視為與三島齊名的文壇雙星,有過交流與對談。小川環樹在回憶文中直指和巳的死也是某種形式的自殺,死於理想與現實的衝突,死於意欲承擔知識人責任的重壓。他後悔自己的“三顧茅廬”,而一切已晚,這是和巳不同於學院內學者的宿命。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和巳敬仰的恩師們,引用這句儒家經典惋惜他。
1969年9月6日,與三島由紀夫對談的高橋和巳
學者戴燕在《高橋和巳初論》中提到,1990年代初,她訪學京大文學部之際,邂逅了《高橋和巳作品集》。她驚訝雲:
高橋和巳曾在京都大學的中國語學文學研究室、這個始建於1906年的日本最著名漢學研究及教學機構裡任過教職,可是,他的名字卻從未出現在我們熟悉的中國文學家的系譜裡。他又是享譽一時的作家,可是,當他的同代人大江健三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他的小說,即使在日本,也幾乎無人問津。
這篇文章也是中文世界很難得的對高橋和巳學問與人生的介紹。我知道和巳,是在《吉川幸次郎全集》中讀到一篇短短的《高橋和巳哀辭》,也用過他翻譯的《魯迅文集》。真正產生興趣,卻是在讀到和子撰寫的回憶錄之後。和子對京都、京大露骨的反感與憤怒在我看來非常新鮮,喚起我追索舊事的好奇。和巳對母校有信仰般的崇拜,毫無抵抗地回到了她的懷抱。而他很快發現,這信仰充滿幻象,精緻的學問之下分明有身份制社會的殘滓。他不贊同暴力,也無法置身事外,因而只有割肉剔骨的“解體”一途,併發問:
學問到底是什麼?
很多年後,和子依然有對“把高橋捲入政治的、喜愛熱鬧的年輕人們”懷有憤怒。而她自己的文學創作在和巳去世後,卻迎來了井噴式的發表與出版,陸續獲得芥川獎候補、泉鏡花獎、女流文學獎……她真正成為了夢寐已久的作家,而不僅是“作家之妻”。
她本名和子,日文訓作たかこ。或許是不想與和巳的名字重合度太高,出道後的署名都是“高橋たか子”。成為作家、獲得聲名並沒有安撫她的創傷與失落——和巳的死對她而言無疑是巨大的創傷。
昔日和巳面對內心極度的痛苦時,習慣反覆唸誦《論語》“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而儒學本來就不為救人,和巳被“中國式的倫理”(和子語)所困,並未得救。具備“法國式知性”的和子選擇了怎樣的解救方式?
1974年夏,她前往法國、義大利散心。11月,經遠藤周作介紹,認識了天主教東京教區的祭司井上洋治,每月去上兩次宗教課。1975年,她去北海道女子聖衣會生活一週。8月5日,在東京目黑區某修道院,由井上神父施洗,皈依天主教,教名瑪利亞·馬達肋納。擔當教母的是遠藤周作的夫人順子,一位慈愛溫柔的“作家之妻”,比和子年長五歲,今年年初以93歲高齡去世。
走上信仰之路的和子依然保持活躍的創作,並開始翻譯法國文學作品。1979年,她在東京接受堅振禮。次年9月,獨自前往巴黎,住在聖嬰耶穌愛德教育修道會,並在巴黎神學院典禮音樂部學習管風琴。
去巴黎後,她暫時不再寫作,因為再多的創作,再多的獎項,都無法給她安慰。她在京都衰病的老父請她每年務必回日本兩次,因而1982年至1984年,每年二月和八月都會回一趟日本。此外時間全在巴黎修道院學習管風琴,每日祈禱、彌撒、閱讀、住極樸素的窄室,潛心過隱修生活。據她回憶,那是一生中最安詳幸福的歲月,“拋下以前的一切,成為無名之人”。她喜歡典出《斐理伯書》的“se dépouiller de soi-même”,“空虛自己”,她翻譯成“像落葉一樣漸漸捨棄自己”。
她年輕時喜歡好看的衣服,迷戀俊美的青年,喜歡喝酒、吃好吃的;由“作家之妻”蛻變為“作家”;又捨去浮名、遁入靜寂,可以說這是她一生經歷的三個重要階段。1984年夏,她回京都後,父親病重。她陪伴在側,在9月送別了父親。
雖說決意減少創作,但往返巴黎、日本的幾年裡,她還是寫了一些小說,並獲得第十二屆川端康成文學獎、第三十七屆讀賣文學獎。
高橋和子撰寫的《追憶高橋和巳》(構想社,1977年)內封
1987年,她賣掉鎌倉的舊家,全額捐給經濟困難的北海道女子聖衣會,用的是高橋和巳的名義。她輾轉於幾個修會之間,想要正式成為修女。因為在巴黎很難解決簽證問題,她考慮回日本的某間修道院。“因不習慣日本的環境,辭去該修道會。”她在文章裡簡單總結,雖不知具體何處不習慣,但可以明確的是,她曾經想逃離京都,和巳去世後則要拼命逃離日本。她想追究和巳之死的責任,發現敵人不是某個人,而是整個日本的環境與文化,沒有人可以負責,人們以集體的名義成功隱身。
高橋和巳生前與老師貝冢茂樹有過一次對談,由日本人的性格論及“逃往何處”。日本是島國,無處可逃,故有某種自然的向心力。貝冢想逃去古代中國,又或美洲大陸。高橋沒有說他的答案,不知是否預知到未來面臨的絕境。
1990年,和子的母親老病交加。她回到母親身邊,以獻身般的熱情照顧母親——也許這是她新的修道之途。
照護與送別,似乎成為了和子的宿命。2000年,她的母親高齡去世。三年後,她住進了神奈川湘南地區茅之崎的付費養老院,那裡可以看到美麗的海岸。她時常去海邊散步,沉迷於週而復始永不停歇的海浪。潮水退去,沙灘被撫平,留下無數細小的白色微泡。她喜歡這短暫的瞬間,彷彿世界消失、神靈顯現。
她對養老院的生活很滿意,令她想到在巴黎修道院的歲月:
在修道院裡,人們超越了生和死的界線。而在這裡,大家都在等待著共同的死。超越了血緣、利害的關係。(2004年1月16日)
這一次是她準備送別自己。她加入日本尊嚴死協會,準備好葬禮時穿的衣服——從前在巴黎穿過的修道服,事無鉅細地規劃死後的細節。如何處理藏書,如何處理和巳與自己的手稿、作品,如何處理環繞身邊的每一件雜物。
除了在巴黎修道院的那幾年,每年5月3日,她都會獨自紀念和巳。擺出照片與白色牌位,以庭中野花數朵作供。他先走出去很遠,她後來選擇的信仰告訴她,他們死後還會相見。她紀念的不是文學或學問世界的人們心中的和巳,而是作為她丈夫的和巳。她不滿世人對和巳的種種解讀,忍不住寫點什麼,有時遭遇惡評,以為她要獨佔和巳,而不管他們也把和巳推上了孤獨的舞臺。
養老院時代,她寫了好幾本書,包括她去世當年,由私淑弟子、著作權代理人鈴木晶整理出版的《臨終日月》,是從2006年寫到2010年的日記。開篇說:
現在我74歲,但我是沒有年齡的,總覺得自己才46歲。啊不,那就48歲吧,是1980年決然去巴黎的年齡。因為從那時起,我就不在了。
高橋和子晚年及去世後出版的日記
高橋和子晚年及去世後出版的日記
2013年7月12日早晨,和子突發心臟病,倒在養老院的臺階上,平靜去世。收到訊息的鈴木晶按照和子生前的安排,聯絡了東京四谷的聖依納爵天主堂,並遵囑低調舉行葬禮,儀式結束後才聯絡各大報社。
她葬在富士靈園,是早先和巳去世時,植谷雄高推薦的地方。墓園可以看到富士山,園內覆蓋著火山灰,“乾燥且清潔”。
當時墓石上只寫了高橋和巳的名字,是埴谷雄高所書。後來她想著,若當時請埴谷把自己的名字也寫上去呢?但那時還沒有想到自己的死。墓園管理者告訴她,舊石上已不能再刻新字。她想,“那就葬到沒有我名字、只有高橋和巳之名的墓裡去吧。無名很好”。
或許是鈴木晶的安排,現在富士靈園高橋夫婦的墓地用了嶄新的墓石,鐫著“高橋和巳/和子”的字樣。
看來她選定的送別自己的人,也相當可靠。
如果我不先讀和子的文章,而是先讀和巳全集,恐怕會沒有批判地接受和巳,歎服他的才華與痛切的自省,感慨他的早逝與不運。幸有和子文章裡的憤怒與傷心作為“先入之見”,才能看到更豐富的和巳與和子,並嘗試理解和子對和巳的複雜情感。
若和巳不早逝,順利在他所說的“保守主義的樂園”裡繼續當助教授、教授,那和子與他最終很可能分道揚鑣。和巳被深深信仰的母校背叛,僅工作兩年即辭職,旋即病重。他人生的最後部分全然屬於和子,是和子包容、撫慰、接受滿身瘡痍、虛弱無助的他。和子對京大(包括京都)當然有怨望,而他們的無情卻意外促成她與和巳最後的深情與感情的圓滿,這其中充滿矛盾。
和子走向宗教、逃往巴黎,屢屢批判日本國民性中的“幼稚”,要與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徹底切割,和巳之死帶給她的創傷固然是重要原因。而和巳早年在婚姻中的粗疏,對她的漠視與任性還沒有來得及清算,他就報之以至為折磨的病死,沒有誰能安慰她,因而她的憤怒與悲傷如此清晰。
閱讀和子的書籍與和巳的全集,不難想象他們十多年的婚姻生活裡,除了瑣務、勞碌、衝撞,一定也有許多智識的碰撞與溝通,有不少共同話題。在修道院生活多年的和子,不知是否會時常想起《創世紀》說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高橋和子撰《高橋和巳其人:二十五年之後》(河出書房新社,1997年)封面
2003年,和巳忌日當天,和子寫了一首短詩:
開啟窗扉,格子窗外
南天竹嫩葉搖曳
只是這些而已
在我生命裡,微風拂過
不願見今日之日本
因而一直將自己幽閉
窗戶,忽而開啟一看
嫩葉與微風,只是這些
是從與不想看到的日本
全然不同的地方來的風
灌注於我
或許可以揣想,晚年的和子得到了解救和更大的自由。
《高橋和巳全集》由吉川幸次郎、埴谷雄高監修,河出書房新社出版,校訂、排版、裝幀無不細緻精心,題簽是吉川的書法。全集編得這麼好,足知恩師與知音對高橋和巳的賞識。全集每卷之首都附有月報,請各界人士撰寫關於和巳的逸話、感想。知名或不知名的男性們筆下往往不會有和巳作為丈夫的一面,因為他們自認活躍於公共領域,他們眼中的和巳也是公眾人物。很少有人提起和子,或許是不知該怎麼談,又或許是恪守“女主內”的傳統。
當中有難得的一篇出自女性之手,作者是NHK廣播劇的負責人齋明寺以玖子(《ラジオドラマの縁》)。她比和子小四歲,也是京大法國文學專業出身。1963年夏,齋明寺為邀請和巳撰寫廣播劇一事拜訪了高橋家。她寫和巳在家裡穿和服,美麗的夫人稱呼他“和巳”。那天,和巳笑眯眯地告訴齋明寺:“我家夫人,也寫小說喔。比我更有才華啊,她寫的東西我可喜歡了。”
齋明寺感嘆,當年高橋和巳已確切預見了日後夫人在文學方面的成功。這些很少被旁人記錄的和巳夫婦相處的片段,在氣氛莊重的和巳全集裡微微閃現,與和巳身後和子的許多追憶文章呼應。由是我們確信,除了和子顯露在水面上的孤僻、憤怒、不可解的神秘,那底下應該還有無限深沉的情感與能量,不知道單用“愛”是否可以概括。
(本文為作者原創稿,轉載請留言獲得授權。除特別註明外,文中圖片均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