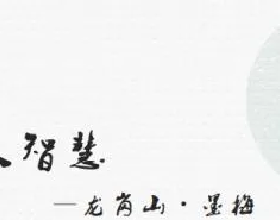1
認識江凱,是在我進入骨科實習的第三天。
跟著老師出了兩天門診,第三天,我們回了住院部。簡單的早會過後,老師去做手術了,他沒帶我,而我也樂得清閒,轉轉病房,偷偷懶。
那時我剛離開學校,醫院陌生的環境令我膽怯又欣喜。我帶著好奇推開了一扇扇病房的門,可那景象,只用三分鐘便摧毀了我。病人們被病痛封印在床上,他們孱弱的身軀甚至支撐不起簡單的呼吸,而我的心,也因此苦澀地戰慄。
就在這個時候,我見到了那位“特殊”的病人。他住在走廊末尾的病房裡,和別人不一樣,他的病房門大開著,我還未靠近,就聽到了他念書的聲音。我在門前駐足,見到一個年輕男人立於窗前,一邊讀書,一遍轉著脖子。剎那間,我竟愣住了,不知該不該敲門打斷他。
在這個失神的空當裡,倒是他發現了我:“怎麼啦,小醫生?”
“沒事,我轉轉病房。”我走進去才發現這是一間單人病房,心中頓時燃起了一種沒來由的窘迫,這促使我瞟了一眼掛在床尾的病人資訊,就匆匆往外走。
“歡迎歡迎,常來呀。”他倒是挺開心的,語氣裡還帶著笑意。在門闔上的間隙裡,我看到他收起了手裡的書,書的封面印著莎士比亞的側臉。
嚯,還是個生病的“藝術家”。
2
我和這位“藝術家”的第二次見面是在第二天的上午,我躲在廁所裡打遊戲,正到賽點時,卻聽到老師在科室裡叫我。我著急往外走,和走廊裡的患者對上了眼,是他。
“小醫生。”他露出了一個燦爛的笑。
我一時想不起他叫什麼,可不知怎的,頭腦一熱,把手機塞給了他。
“幫我打一會兒啊!”
我這一忙就忙了整個上午,到他的病房取手機時,已是中午。我推門而入,這次,他坐在床上,依舊看著書,只不過書的封皮換了個顏色。
“怎麼樣?”我問他。
“挺好的,剛輸完液。”他看到我,又笑了。
“我是問遊戲。”
“哦!”他恍然大悟,把手機遞給我,“不好意思,輸了。不過這個遊戲挺好玩的,你們現在的年輕人都玩這個嗎?”
他的語氣讓我覺得親切,於是我也逗他:“對呀,那你們‘老年人’都看什麼書呀?”
他把書合上,向我展示封面——《世界名畫全鑑》。這輩子都沒看過幾幅畫的我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尷尬,換了個話題。
“小醫生,你上午著急忙慌地跑了,出什麼事啦?”
“沒事,老師叫我去打水。”
“打水?”他看著我身上的白衣,“你不是醫生嗎?”
“我只是個實習生。”我坐在了窗邊的椅子上,再次看著他的資訊牌,“而且,我還是個懶惰的實習生……江凱?你的名字蠻好聽的嘛。”
“哈哈,你怎麼稱呼呀?”
“我姓王。”
“王醫生好!”他向我敬了個禮。
我看他是逗我逗出樂趣了:“你得什麼病了?”
他的眼神突然黯淡了,我意識到自己問了個不該問的問題,可見他這麼生龍活虎的,能有多嚴重呢?
“也沒什麼。”他像是聽到了我的心聲,也像是安慰他自己,“那個病名我也沒記住,總之我是頸椎疼,下下週做手術。”
他嚴肅的樣子,把我嚇住了。
他猶豫了一會,一臉為難地開口:“小醫生,我有個不情之請,你能不能聽一下?”
我第三次看向他的資訊牌,他才二十九歲。
“醫生說我的病挺嚴重的,可能癱瘓,也可能死在手術檯上……”他看向窗外,突然問了我個問題,“小醫生,你說,如果我真的只有兩星期的生命了,為了一份渺茫的生機,把最後的時光傾注在這間屋子裡,值得嗎?”
我啞然。
他笑了:“也對,這個問題對你來說太難了,畢竟這本就是個無解的問題。可是,我雖不知道這值不值得,卻清楚地知道自己不願意……”
“你要我幫你什麼忙啊?”彷彿被人扼住了喉嚨,我喘不上氣,卻也想著,他說什麼我都要答應他。
“那……”他的表情又窘迫了起來,“你以後能不能每天都借給我你的手機,讓我打會遊戲?”
3
或許是覺得沒人會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又或許他的話為他的笑容染上了一絲悽美的壯烈感,我同意了,況且這本就是個小要求,只是有點出乎意料罷了。也因此,在每個下班的夜晚,我去找他拿手機時,都會和他聊一會。
“其實我不該讓你玩。”
“因為你年輕我才拜託你的……我覺得你能理解我。”
“可你每天拿著我的手機,我好無聊啊。”
“你認真上班啊,玩什麼手機。”
“你不懂……”
就這樣,每日與他閒談幾分鐘,變成了我的固定日程。
然而變化發生在第七天的傍晚,我早早結束了工作,來看他時,他還在打點滴。
他突然變得陌生了,我反應過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病”的樣子。夕陽西下,在橙紅色的光暈裡,空氣中漂浮的塵埃都是晶瑩的,可躺在其中的他無法被染色,是蒼白的。
年輕、強壯、還有他標誌性的笑容,無論哪個充滿生機的字眼,都會被“病”這一個字輕鬆擊潰。他看到我,做了個起身的動作,我趕忙按住他,小心翼翼地。一個男人,這一秒我卻怕壓碎他。
“你的手機在窗臺上,你自己拿吧。今天下班早呀!”
“早晚都一樣,都是打雜,無聊死了。”
“我才無聊呢。”他瞟了一眼吊瓶,“輸液最無聊。”
我坐下:“那我陪你聊一會吧。”
“其實醫學不是我想學的,我小時候想學藝術。”他專注地看著我。很難得有人有時間,有心思聽你講話,我忍不住想多說一點:“可是‘唱歌跳舞’這些詞好像本身就帶著貶義一樣,家長總覺得這就是浪費時間……他們總說,你能靠這個吃飯嗎?這些只能當愛好,閒下來玩一玩就行了!”
他被我模仿大人的樣子逗笑了:“藝術是最美的東西,沒人能給它下定義,可是你爸媽說的也沒錯,這是兩碼事。”
“錯了,大人就是看不起藝術。”
“那你會什麼啊?”他話鋒一轉。
“我唱得也就那樣。”我很窘迫,“但我喜歡啊。”
他笑了,我有點生氣。他說:“你還小,還不懂生存的意義。我為什麼說你爸媽說的沒錯,是因為事物的好壞也不是他們評價的。”
“那是誰?”
“就是生存啊……因為生存是最難的卻也最必須的事情,所以利益就成了衡量價值的標準,可你太小,不懂這兩個字的重量。”
“為什麼?”我想反駁他,但總說不到點子上。
“沒有為什麼,但你會懂的。”
病中的他更像個“大人 ”,我想,可能是因為大人沒有幻想了,總是悲觀的。
我放棄了和他爭論哲學問題,繼續傾訴自己的煩惱:“我覺得我對醫學沒有別人的那種信念感,看到病人我很難受,我害怕,所以我總是偷懶。不上手術,打打雜,其實我心裡還挺輕鬆的……我很不負責任吧?”
“有點。”
“我和你說,現在的醫生都是碩士博士,除了這個還要規培證,執業醫師證……把這些都拿到手,我已經三十歲了,這不是我最怕的,我最怕的是我已經看到十年後的自己了。你說,我是不是不適合當醫生?”
“不是,其實你挺善良的,只不過……”
“那天你說,誰也不知道值不值得,可是我們卻知道自己願不願意,你是對的。可我很害怕,因為我不願意。你說只不過什麼?”
他想了半天,還是沒找到一個合適的詞:“只不過你還是太小了。”
我是無法說服他了,果然誰都不能理解我。我站起身,對他大吼了一句:
“生存就是生計嗎?生活就是活著嗎?”
4
我後悔了,我不該兇他,所以第二天,我早早就去給他送手機。但他卻說不要了。
“你是不是生我的氣了?”
“所以說你還小啊。”他揮了揮手裡的書。他的意思是遊戲的樂趣已經體驗夠了,現在要抓緊時間看書。
他的書還挺有趣的,從莎士比亞的悲喜劇到古希臘神話故事,從《特朗斯特羅姆詩歌全集》到《唐詩三百首》,不過他最愛看的,還是那本畫集。
我問過他的職業,他說他是一名詩人,我也問過他的家人朋友,他說他不願拖累他們,也不願意看到他們為自己哭。這莫名增添了我那無用的責任心,陪他聊天成了我自願並期待的工作。
其實我知道,我也是發自真心地想對他講話,對只認識幾天的人吐露心事,這不是奇蹟,只是因為他要死了。這句話很殘忍,但很真實,我利用這段時間,同時也珍惜這段時間,這不是悖論。
醫院的科室很多,輪轉起來,每個科室只分到兩星期,而我已經在這裡呆了十天了。那天,我像往常般來看他,我對他說我要去其他科室了。他當時正看著一幅名為《大碗島星期天的下午》的畫,畫裡的人們在公園玩樂,溫柔的色彩下,畫裡的人那麼悠閒,那麼快樂。
《大碗島星期天的下午》
他說:“我想去公園。”
我沒明白,但他也沒來得及讓我明白,就捂住臉哭了起來。我嚇了一跳,手足無措。在他的抽噎聲裡,我聽到了這句話的下半句:
“我從沒想過會有一天,這麼小的事情都變成了奢望。”
那瞬間,我突然就懂了他讀書的目的。這些詩句,這些畫,是他在這個小房間裡與世界聯通的渠道,他不僅能打破空間的壁壘,飛到世界各地,還能掙脫時間的桎梏,回到過去。
他只哭了一下,再對著我笑時,眼神裡浮起了一層淺淺的羞怯。他的笑不再壯烈了,它破碎了。
原來靈魂可以比皮囊更早崩潰,他老了,他的靈魂被折磨老了。他對我說著“好好學習”之類的祝福話,我乖乖點頭,我確實太小了,我的靈魂太小了。
我推門離去,在門闔上的間隙裡,又窺視了他一次。他明明還是看著書,可是一切都變了。
只有窗外的落霞沒變,它依舊紅著,恬不知恥地紅著,灼痛了我的眼,讓我也哭了出來。我覺得對不起他,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生命。
窗外的落霞
5
第二天,我鼓起勇氣對老師說,我要轉科了,希望能在離開前看一場手術。就這樣,我人生中第一次進入了手術室。
它比我想象的更神聖,更莊嚴,可它沒我想象的那麼恐怖。換鞋、穿衣服、洗手、消毒、連手術檯旁的站位都是講究的。綠牆銀刀,白色手套與鮮紅的血,只需要兩個小時,就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這不是奇蹟,我用肉眼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我在臺尾站著,全程只是幫老師搬了一次凳子,可當手術結束,老師囑咐我去通知病人家屬時,我是真的、真的欣喜。
當天下午我又參與了一臺手術。在老師的指導下,我還握著持骨鉗,用力把一截錯位的骨頭拼回原位。原來一塊斷骨都能有這樣摧枯拉朽的力量,只不過拽了十分鐘,我背後的衣服就被汗水浸透了,我咬緊牙關,身體都顫抖了起來。
生命很脆弱,但也很堅強。
那天我下班很晚,我很想對他炫耀“我是把生命的重量握在過掌心裡的人”。可他的窗黑著,我想他睡了,就沒去看他。事實上,那之後的每一天我下班都很晚,而我再也沒見過他。
6
我不是放棄了夢想,只是有某種偉大卻難以形容的東西把我所謂的追求襯托成了無病呻吟,靈魂和軀體的意義都以某種實實在在的方式震撼了我。
其實那之後我有回去過,我想對他說我喜歡上了醫學,也想對他說我會努力珍惜每一天。而最重要的是,我要和他繼續那場未完成的“哲學辯論賽”,我要告訴他:生命確實很重,但稱量的工具一定不是利益,評價的標準應該是——你曾經歷過。
只有看過的書你才能評價好壞,也只有自己過過的日子,你才能知道它的意義。
可那時他已經不在那間病房了。江凱,這個名字去了大城市更好的醫院,他的家人為他辦了手續。
“或許不光是他改變了我。”
我這樣想著,心裡多了一絲慰藉。他的病床恰巧空著,我不累,卻想歇一下。我坐在他的病床上,透過窗,正好能看到院子裡的小花園,稀疏的草坪裡有幾顆樹,橙色的陽光穿透葉子的縫隙,在地面上打出了無數金色的瑣碎,那些金光裡,幾朵小野花頑強地開著。
夠了,把這裡想象成花園,足夠了。
因為認真實習,我已經很久沒開啟遊戲了,既然又回到了故事的起點,那就讓我再偷一下懶吧。
我點開遊戲,落日依舊燃燒著,再次燒紅了我的眼。
他改了我的遊戲簽名:“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我懂了,我抬頭望著溫暖的霞光。
我真的懂了,值得,就是不要問值不值得。
題圖 | 圖片來自網路
配圖 | 文中配圖均來源網路
(文/星月燁,本文系“人間故事鋪”獨家首發,享有獨家版權授權,任何第三方不得擅自轉載,違者將依法追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