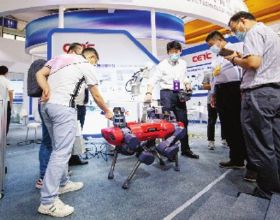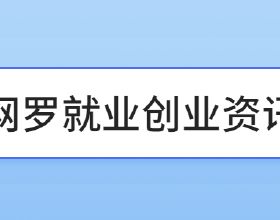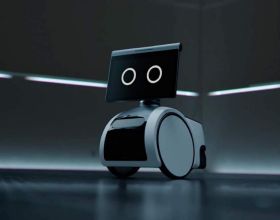《人日思歸》是一首廣為傳誦的名作: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
先說一點題外話。前段時間在日本社交媒體上有一個關於京都人說話方式的話題引發了熱烈討論。例如在商務會談時京都人突然指著你戴的手錶說:“這塊表看起來真高階”,其實他不是在誇你的表,而是在提醒“時間差不多了,長話短說吧”。而如果去你家做客的京都人喝了你上的茶,特意強調“這個玉露茶很好喝”,他有可能是在暗示“待客應該用比玉露茶更高階的茶”。語言上的弦外之音,就像是對了個暗號,看對方接不接得住,以此判斷對方在教養水平上是否同類。
有文化的地方的人歧視沒文化的地方的人,古今中外有之。關於這首《人日思歸》,也流傳著一個關於地域歧視和文化認同的故事。
唐人劉餗的《隋唐嘉話》記載:
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云:“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雲:“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隋唐嘉話》是筆記,故事未必可信,態度卻深可玩味。《人日思歸》這首詩作於585年,是隋文帝開皇五年,也是陳後主至德三年,其時南北尚未統一。那時的北方兵強馬壯,掃平天下在即;而南方自晉室渡江之後到宋齊梁陳,領土漸小,力量漸弱,陳最小最弱,眼看就要亡國。不過,這毫不影響南人在文化上,特別是詩文創作上對北人的歧視。從東晉到陳,在文學上特別是詩壇上,南朝所出人才、理論、作品遠過北方。南朝梁的庾信到了北朝後,“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犬吠,聒耳而已。’”庾信自己從南入北,在北朝生活和創作了二十八年,認為北人能入眼的除了溫子升《韓陵山寺碑》,也就是薛道衡、盧思道還稍微寫得兩筆,其餘的都如同驢叫狗叫瞎吵吵。這段話說得刻薄,鄙夷態度躍然紙上。當然,此記載也來自唐人筆記(張鷟《朝野僉載》卷六),或也只是小說家言。
從南朝來的庾信已在開皇元年(581年)去世,和薛道衡一起被庾信提名的盧思道也在開皇三年(583年)死去。北朝文士的代表,數得上的就剩下了薛道衡。開皇四年(584年)舊曆十一月,薛道衡出使南朝陳,在開皇五年(585年)的正月初七寫下了這首《人日思歸》。要知道,此時離開皇九年(589年)隋滅陳已經不遠了。可是就是在這樣懸殊的政治和軍事實力下,陳的文人們一看到“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照樣毫不客氣地嘲笑隋的使臣、北方最負文名的薛道衡:
“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這是什麼話呀?誰說這個北方佬懂作詩?”
這謎一般的文化自信,是從晉室渡江以來幾百年積累起來的。
“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這兩句詩,怎麼就讓南邊的文士們如此嘲笑呢?句式上,這兩句巧妙利用時間關係做成了對仗結構,不失工整;意思上,就像每天數著日子過似的,結合後兩句看,也把度日如年的盼歸心情表現出來了。語言直白和淺俗,或許是它被嘲笑的最大的原因吧,但《紅樓夢》裡王熙鳳說的“一夜北風緊”,其淺俗比薛道衡的這兩句更有過之,又為什麼能讓有“詠絮才”的才女詩翁們相視而笑大為稱讚呢?
試著解釋一下原因,鳳姐兒的“一夜北風緊”,是“即景聯句,五言排律一首”這個大題目下的第一句,它的好處在於“這句雖粗,不見底下的,這正是會作詩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多少地步與後人”。一個開頭說出來了,後面還有十幾個人要聯句,以一句粗話開頭,正是給後人留了很大的餘地。但是,對於薛道衡的這首五言絕句來說,一半的篇幅就寫了兩句淺俗的大白話,佔篇幅太大,而包含的意思(如果不與後兩句結合起來看的話)又太少,佔用了詩歌的一半卻好像僅僅只是點明瞭時間。後面若不是有巨大的筆力和才氣,若不是有極其精巧的詩思和高超的發想,這首詩就很難再扭轉過來了。
當然,陳的文人們聽到薛道衡念出“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這兩句時,未必知道他只將此詩作成最短的絕句,但在那個時代還沒有所謂排律一體,詩歌體制一般較短,五古長詩一般限於十韻之內,像這種開篇即對仗的體式的話則通常更短一些。這一開頭的兩句粗話,確實很難說是“會作詩的起法”。所以這樣看來,“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雖說刻薄,也不是全無道理。
然而,在這樣兩句粗話之下,薛道衡發力了:“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反轉發生了,腐朽一下子化為了神奇。這個反轉是如何形成的呢?大雁,春華,都是新春的眼前之景,不新奇。新奇的是這即景的立意:大雁有一到正月就迫不及待地飛回北方的習性,哪怕北方還冰天雪地,大雁卻急著回到北方的家,而作者想到自己回北方是要落在大雁的後面了;南方因為氣候溫暖的緣故,花兒開得比北方早,新春已有不少花開,對薛道衡這個在南方過春節的北方人來說,一定會對花開得早這一自然現象更敏感,比一直在這裡生活的南人有更新鮮的體會。在這種心理背景下,薛道衡說花開得早又算什麼呢,我的歸思在花開之前就已經生髮。更顯出了歸心之迫切。
此詩中的大雁和春華,不僅是新春的實有之景物,而且還成了作者的歸思的一種比喻,也可以說是一種參照物或者對照物。我覺得這兩句詩已經超出了我們常說的“情景交融”的層次,而是讓思歸這種抽象的情在和雁與花的對照下變得有了具象:大雁奮力北飛,花兒爭相綻放,都好像成了歸思的一種外在的、直觀的形象,同時又是歸思與之“爭先恐後”的比較、競賽的物件。
這兩句詩還好在它的詩法。歸的是人也是雁,而發既是花發又是思發,同時如果再強為解釋一下,發還有出發之意,在生髮、花開的意思外又還可以翻出一層歸心。“歸”和“發”每個動詞都作用於兩個名詞,而“人歸”與“雁歸”、“思發”與“花發”之間形成了時間上的前後關係、對比關係,形態上將無形的歸思化為有具象的雁歸和花開的比喻關係,再細究一層更有因果關係——因為看到雁歸而想到自己不能歸家,因為花開得早這一點新鮮的細節也會引起故鄉之思,等等,多重的關係使得這兩句詩充滿了豐富的張力。詩歌本就短小,五言絕句又是詩歌最短小的形式,然而,它可以透過新奇的立意和語句的多重關係與相互作用形成一個無限大的天地。
而這兩句詩的好裡,恰恰有南朝詩人們刻苦摸索過的詩歌技法。例子可以舉出很多,比如剛才說過的那個南朝入北朝,瞧不起北方文人的庾信,他備受稱道的名句“霜隨柳白,月逐墳圓”,其實就是這樣一種用特有的句式、精練的動詞和詞語排列順序而造成的多重關係:霜凝結在柳上使柳變白,卻似乎霜是隨著柳色變白而漸顯白色的;月亮漸漸變圓,照著同樣圓的一座孤墳,似乎月亮是為了追逐模仿這圓形的孤墳而變圓的。霜色和月光因為本身都是難以狀寫具體形象之物,有了“柳”和“墳”這兩種意象的相互修飾、參照,形象相互生髮,就變得極為新警而鮮明瞭。
而我以為,從南朝到唐代的詩歌裡最具特色、最傑出的一點,即唐人所謂的“興象”,其實就是詩人重新安排物與物之間的關係,而讀者能透過詩人建立的物與物之間的關係認識詩人的情感和心靈。
所以,當薛道衡寫出了“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南朝的文人們就一下子認同了他,喜曰:“名下固無虛士”,就是因為這兩句詩顯出了立意的新巧、構思的聰明,更在短小的詩句中精心煉字造句,製造物與物之間的多層次和多元的關係,表達多層次的豐富情感,讓詩歌雋永、耐尋味,這些南朝文人們以為只屬於他們的詩歌的暗號,薛道衡對上了,才得以讓南朝文人們承認他名不虛傳。
還有一點值得說的是這首詩是通篇對仗的。在近體詩的形成中,南朝詩人,特別是齊永明時期的詩人們在聲律對仗上的探索可謂功不可沒。但是五言四句的形式本是出自樂府民歌,本是以古體見長的一種詩體,其實從唐代的創作來看五絕中也是古絕遠比律絕多,後人總結出的“五絕調古,七絕調近”也正說明了這一傾向。但是在南朝詩歌律化的過程中,對仗的作法也影響了五絕,例如南朝梁何遜的非常著名的《相送》就是通篇對仗的:“客心已百念,孤遊重千里。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薛道衡這首《人日思歸》的通篇對仗,應該說也正是南朝人在探索並認可的形式。
只是那時候南朝人還不知道,對上了他們詩歌的暗號的北方人薛道衡,作為詩風南北融合的唐音的先驅,實際上已經預示了詩歌中心將要回歸北方並南北融合的先兆。“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詩國高潮即將到來。
(作者:鄧芳,系日本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特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