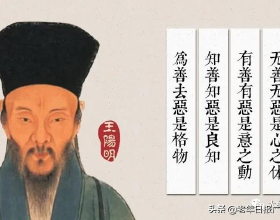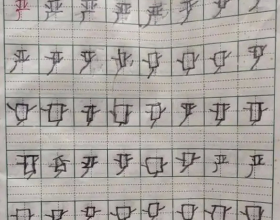百年新紅學最大的成就就是以胡適先生為代表的幾代紅學家運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方法考證出《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的祖父是江寧織造曹寅,《紅樓夢》是以曹家為原型以“自敘”體方式創作的一部小說。
新紅學派的紅學專家“大膽假設”是夠大膽了。但“小心求證”卻出了問題,幾代紅學大師歷經百年就在曹雪芹二十幾條經不起考證的證據上來回求證。卻忽視了《紅樓夢》的成書過程正是清朝政府嚴厲鎮壓反清復明思潮的社會大背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時期採取的“文字嶽”政策是中國歷史上最嚴厲的時期。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有較大“文字獄”11起。
而雍正在位只有十三年,卻有殘酷而大規模的“文字獄”近20 多起。
乾隆在六十年的帝王生涯中,竟創造了130多起酷刑“文字獄” ,創造了比此前中國歷史上“文字獄”總和還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蹟。
南山案是發生於清聖祖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文字獄。由左都御史趙申喬舉發翰林戴名世(人稱戴南山)的作品《南山集》“狂妄不謹”、“語多狂悖”,而且戴南山在《南山集》的《與餘生書》中引用了方孝標的《滇黔紀聞》的南明永曆的年號。康熙五十二年二月,戴名世因此被斬,被牽連入嶽者多人。
再如發生在雍正朝著名的“清風不識字”案。
在這個案子中,被害人叫徐駿。他是崑山名門世家出身。舅爺是清初大儒顧炎武;父親徐乾學考中過探花,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書;二叔徐秉義也是探花出身,官至吏部侍郎;三叔徐元文考中過狀元,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雍正八年(1730年),徐駿在一篇奏摺裡,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字,惹惱了雍正皇帝。雍正皇帝當即將徐駿革除職務,隨後又進行抄家。這一抄家,就抄出了他詩集中的《無題》詩。全文是:“莫道螢光小,猶懷照夜心。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這本是徐駿在夜深人靜時隨口而吟的一首應景之作,調侃風吹書翻的場景。辦案人員卻認為徐駿是在諷刺清朝統治者沒有文化,還要偏偏裝出有文化的樣子。經過審訊後,辦案人員形成了報告:“刑部等衙門議奏,原任庶吉士徐駿,狂誕居心,悖戾成性,於詩文稿內,造為譏訕悖亂之言,應照大逆不敬擬斬立決,將文稿盡行燒燬。”雍正皇帝批准了這份報告,於是徐駿被處斬,丟了性命。他留下的詩集文稿,全部被燒燬。
我們再看乾隆時期,從1751年(乾隆十六年)起,“文字獄”突然死灰復燃,一個空前殘酷的“字禍”高潮突兀而起,七十 多起“文字獄”一個接一個暴發。
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江西千總盧魯生與守備劉時達合 謀,編造了一個指責乾隆帝錯誤的奏稿,假託是孫嘉淦寫的,意圖藉此制止乾隆勞民傷財的首次南巡。乾隆十六年(1751年)六月 ,“偽孫嘉淦奏稿”流傳到雲南時被乾隆帝發現了,由此在全國追查偽稿作者。到當年十一月,僅四川一省即逮獲傳抄偽奏稿犯二百八十餘人,湖廣、江西為數更多。乾隆十八年(1753)二月,乾隆帝下令將所謂正犯盧 魯生使用最殘酷的凌遲處死,劉時達斬決。
此事處理完畢後,乾隆帝仍然坐臥不安,疑神疑鬼,一 時懷疑偽稿是曾靜、張熙餘黨所造,一時懷疑出自那些讀書失志的文人之手,懷疑可能是被殺掉的川陝總督張廣泗的親 友故舊流落怨望,造謠生事。於是乾隆創造性地提出,要提高“皇權專制”,就要對文化思想厲行統治;而將一切禁書統統燒燬。乾隆獨創了借“蒐集古今群書”而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查辦禁書,欲將一切“反清文字”作 品的舊刻新編之作者、出版者、收藏者一網打盡。
乾隆時的文字獄,有不少案件,是因為向清朝統治者歌功頌德、獻書獻策,不過,因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諱,也會遭到殺身之禍。
目前公認的《紅樓夢》成書時間,就在文字嶽最嚴厲的康、雍、乾時期,並且滿書的反清思想和文字,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作者實名著書發瀉對朝廷的不滿情緒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們不用從《紅樓夢》中去找過多的反清句子或內容,就憑小說第一回我們幾乎家喻戶曉的“滿紙荒唐言”這一句來看,這是對滿清政府的極大汙辱!一句中性詞性質的“清風不識字”都招來殺身之禍,那“滿紙荒唐言”將會給曹家帶來怎樣的災難?
其實新紅學派考糾出曹雪芹是江南織造曹寅的孫子,是《紅樓夢》的作者,證據不外乎袁枚根據明義的說法,自稱自家的陏園就是大觀園。而明義對曹雪芹家世的說法根本不是肯定性語言,用的是“蓋”,即大概或可能的意思。因此,明義的說法不能成為證據。
胡適先生髮現的最直接的證據只有一條。就是《四松堂集》中在“揚州舊夢久已覺”下面的一條小注:“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十二個字。《四松堂集》本來沒有曹雪芹是曹寅之孫的說法,這個說法來自《四松堂集付刻底本》(供刻印用)加的一條箋註:“雪芹曾隨其先祖寅赴織造之任”。
這短短十二個字先不說是誰寫的,是否是真的,就算是真的,也漏洞百出,邏輯混亂,嚴謹的學者也不可能引以為證據。
曹寅逝於1712年,而胡適紅學考證的曹寅之孫“曹雪芹”最早生於1715年。既然“曹雪芹”生於曹寅去世以後,他又怎麼會“隨其先祖寅赴織造之任”?況且曹雪芹寫的是《金陵十二釵》,也不是《揚州十二釵》,由此可見,這條貼箋也是錯誤的。這一點胡適先生也是認可的,他只能說人家弄出了個“小錯誤"。既然人家弄錯了,那我們還能引用成證據嗎?
總之,要從清初政治背景出發,去研究紅學才是正道,不要在《紅樓夢》“自敘"體小說上再做無用功了,如果不考慮當時的政治背景去研究《紅樓夢》的真實作者,只能是“痴人說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