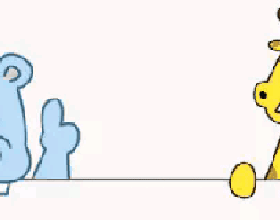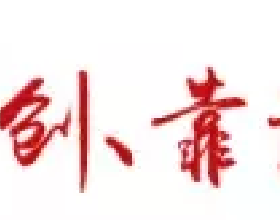鄺海炎
日本作家裡,我最喜歡谷崎潤一郎,這人雖長得彪形虎目,文章卻出奇的敏秀細膩。他不但是一流的作家,還是一流的文學評論家。近日,我讀完他的《文章寫法》一書,真想掐一把大腿暱叫:“親愛的死鬼,谷崎潤一郎!”
谷崎這種名家談寫作方法,當然免不了“六經注我”。最欣賞的寫作風格還是簡潔含蓄。他在這方面力推的典範是志賀直哉。
志賀直哉短篇小說《萬曆赤繪》的開頭是:據說京都的博物館中有一封萬曆的美好花瓶云云。一般來說,要誇獎花瓶可以用“可觀的”“華麗的”“藝術的”等更亮麗的詞,但志賀為什麼用“美好”呢?谷崎開啟他的媚眼:但無論用哪一個,終究不如用“美好”一詞所包含的寬廣和深厚,這用語除了適切道出這花瓶的美之外,同時也擁有暗示全篇內容和趣向的寬容度。從簡單的用語裡窺見作家手腕的高下,這就是谷崎文學評論最引人入勝的地方。
志賀的另一本小說《在城之崎》寫了主人公去做溫泉療養,看到了蜜蜂死骸的心情——一邊是蜜蜂進進出出、忙忙碌碌,一邊卻是“一隻從早晨中午到黃昏,每次看到的時候都在同一個地方完全不動地垂頭趴著,又給人一種已經死掉的感覺。三天之間,一直保持那個樣子。看著那個時給人一種非常靜的感覺。”這後面,緊接著就是一句“好寂寞”。谷崎認為,要是其他作家,可能就是“我好寂寞”,主語“我”一出,“寂寞感”就弱多了。
這裡蘊含的文學原理類似王維的“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漢語詩歌為什麼罕見第一人稱單數?美國學者溫伯格解釋說“透過消除詩人的獨立意識,讀者的體驗既普遍而廣大,又即刻而直觀”。因此,看到有人將“但聞人語響”翻譯成“we hear only voices echoed”(我們只聽到人語的回聲),他毒舌道:“某某不僅生造了一個敘事者,而且讓他們成群結隊,如同一場家庭郊遊。他用了we(我們)這個詞,整首詩的基調一下子被毀了。”
不得不承認,每個人的文學眼力見有差異,外行見某字只看見模糊一團,入行的才看清字的骨架輪廓,內行如谷崎則不但能看見字的骨架,更能看見肉身,進而在字的基本義外還能感受到字的溫存、紋理,以及曲線美觸發的遐想。日語與漢語接近,谷崎自己是文章高手,對志賀的高明文筆也就惺惺相惜。因為主語的缺席或省略,使得主體弱化,乃至環境“物我合一”,志賀筆下的事物就變得真切細膩了,甚至彷彿有了一些“卡夫卡的色調”——細節的“真切”和“整體的”荒誕。
谷崎的敏秀細膩,不只表現在對語言差異的洞察上,也表現在能辯證地看待語言發展。他重視語言的音樂性,因此拈出了“五種調子”,其中流暢的調子、簡潔的調子、冷靜的調子、飄逸的調子,都好理解,有音樂性嘛。可“粗糙的調子”就讓人費解了,但別急,且聽“死鬼”慢慢解釋——有一種看似“惡文”的文章,“寫作者特別避開流暢的調子……刻意寫出生硬粗糙難走的凹凸不平的路那樣的文章……因為,如果寫得滑溜溜太流暢的話,讀者會被那調子所吸引而一口氣讀下去,恐怕來不及深入體會一句一句的意思……這是粗糙派的想法。”中國一現代散文大家也在1930年前後反對音樂性,進而追求散文的“澀味”。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吧。
【來源:遼寧日報】
宣告:此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若有來源錯誤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權益,您可透過郵箱與我們取得聯絡,我們將及時進行處理。郵箱地址:[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