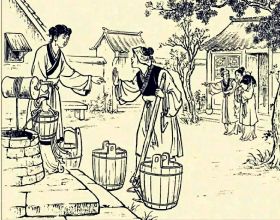張家場有個財主,名叫張守仁,儘管家財萬貫,卻總是想盡辦法撈取不義之財,人送外號“張不仁”。
這天夜裡,張守仁正睡得香,忽然聽到有人敲門。他穿衣起身,來到院子裡,生氣地喊道:“誰呀?大半夜的敲啥敲!”話音剛落,一陣陰風吹過,院門竟開了,張守仁不由得打了個冷戰,抬頭一看,只見兩個身影站在門外:一個又瘦又高,臉白得像窗戶紙;另一個又黑又矮,手裡還拿著條鐵鏈子。
這不是黑白無常嘛!張守仁嚇得兩腿一軟,跪倒在地,連磕三個響頭,說:“小民不知是二位爺駕到,多有得罪,還請見諒!”
白無常開口說:“你也莫怕,我們是來跟你打聽個人的。”原來,他們是奉閻王之命,到張家場來索一個叫“張不仁”的命的,可他們在村裡轉了兩個時辰,也沒找到張不仁,所以來問問。張守仁聽完,嚇得渾身發抖,他的外號就是“張不仁”,難道黑白無常是來索他的命的?他強裝鎮定,賠著笑臉說:“二位爺一定是弄錯了,我打小在村裡長大,我們村並沒有叫張不仁的。”
黑無常不耐煩地說:“閻王爺交代下來的差事,怎麼會錯?他說張不仁為富不仁,就住在張家場最闊氣的房子裡。我看,這裡就是!你是不是張不仁呀?”
張守仁哆嗦著說:“小民名叫張守仁,不是張不仁。我只是借住在這裡。二位爺不如回去問問清楚吧。”白無常和黑無常嘀咕了一下,轉身走了。
張守仁連滾帶爬地回到屋裡,搖醒了老婆,說:“快走!”他老婆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就被他拉著出了門。
就在張守仁家這棟十分闊氣的房子隔壁,還有一間老屋,雖年久失修,但尚可住人。進了老屋,張守仁心裡才踏實了些,跟老婆把剛才的事講了。倆人都不敢回家了,打算暫時住在老屋裡。
第二天夜裡,張守仁又被敲門聲驚醒了。他心驚膽戰地去開了門,果然又是黑白無常站在門外。看到是他,黑白無常也吃了一驚,白無常問:“怎麼又是你呀?”張守仁忙說:“這才是我家。”
白無常說,他們回去請閻王爺查過了,沒有勾錯,那個該死的人就是張家場的張不仁。可他們在村裡轉了好久,還是沒找到,這才又來打聽。張守仁還是咬緊牙關說:“二位爺,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我真沒聽說過張不仁這個人。”
白無常也犯了難:“不可能啊,張家場的張不仁,咱們聽得清清楚楚,這到底是咋回事呀?”黑無常也急得上火:“再找不到這個人,黑白無常的顏面何在呀!”
白無常轉了轉眼珠,說:“有了。咱再回去問問閻王爺,這張不仁的老婆叫什麼,再來找,就錯不了了!”說完,兩個人又一陣風似的走了。
張守仁兩腿一軟,跌坐在地。要是黑白無常問清了他老婆的名字,那就鎖定是他了,再也別想跑了。這時,他老婆也跌跌撞撞地跑出來,一個勁地問他現在該怎麼辦。
張守仁盯著老婆半天,突然一拍腦門:“有了!”說著,他回屋簡單收拾了點東西,拉起老婆就往外走。老婆問他去哪裡,張守仁小聲地跟老婆說起了自己的主意:黑白無常一再說是要找張家場的張不仁,那夫婦二人現在就離開張家場,去別的地方,這樣黑白無常就找不到他們了。
老婆遲疑地問:“黑白無常會那麼傻嗎?”張守仁說:“他們兩回都問到我了,卻不知道我就是張不仁,一看就不聰明。聽我的吧,沒錯!”
於是,兩人一路向北,走了一天一夜,總算離開了張家場的地界,來到了鄰鄉,見天色已晚,便尋了個破廟住下來。但兩人心裡還是不踏實,怕黑白無常會追來,心驚膽戰地坐著,不敢睡覺。生生等了一宿,直到天亮,黑白無常也沒來,張守仁心花怒放,興奮地跳起來說:“看看,我的主意好吧?還黑白無常呢,我看該叫他們黑白雙傻!”
接下來,兩人尋到附近的村子,在村中租下一個閒置的小屋,隱姓埋名地過起了日子。
不知不覺,兩個月過去了。這天,張守仁去趕集,忽然聽到有人喊他:“守仁叔——”他扭頭一看,竟是堂侄大寶。大寶追上他,驚訝地問:“守仁叔,你和嬸咋忽然就走了?我們還以為出啥事了呢!”張守仁不想多說,擺擺手說:“這事兒一兩句話說不清楚。哎,你咋到這兒來了?”大寶說村裡的二黑死了,二黑舅住在這附近,他是來送信的。
張守仁心中一驚,忙問:“二黑?他才四十多歲,身子骨一向很棒,怎麼說死就死了呢?”大寶說:“這事兒說來也蹊蹺。據二黑的老婆說,那天夜裡,她睡得香,二黑啥時候出的門都不知道,等到天亮,就見二黑死在了院門前,估計是半夜出去小解時不當心摔了一跤,腦袋磕到了石頭上。”
張守仁轉著眼珠想了想,趕緊跑回家,高興地對老婆說:“咱可以回去啦!”
老婆擔心地問:“黑白無常不會再找咱麻煩啦?”
張守仁得意地說:“那兩個糊塗蟲,尋不到我,把二黑索走交差了!”
老婆驚訝極了:“這也行?”
張守仁擺擺手說:“陰曹地府裡冤死的人多了去了,閻王爺可曾管過?人收來了,也就不計較了。”
夫婦倆也過夠了這種清苦日子,趕緊收拾了一下,僱了輛車,回到了張家場。
到了家,張守仁開啟屋門,卻見屋角被人挖了幾個大坑,他藏在牆裡的幾箱銀子,全被挖走了。張守仁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直到這時,他才明白,這是中了賊人的調虎離山之計呀!那黑白無常分明是賊人假扮的,目的就是把他們夫婦嚇跑。張守仁捶打著自己的腦袋,呼天搶地地哭喊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