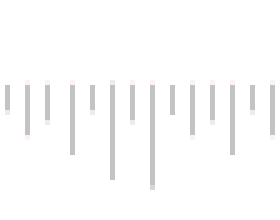四叔回來那一天,正好是當年的除夕。那年,我上初二。年前的期末考試,我終於擺脫班上的“墊底王”稱號,還拿了學校100米短跑的冠軍。
寧波老家過年要去土地廟燒香。我和妹妹拜完土地廟準備回去,發現一名黑黑瘦瘦的男子正盯著我們。他看起來很恐怖,頸子上有一條很粗的疤,一雙發亮的眼睛藏在亂蓬蓬的毛髮後面。
那人盯著我看。突然,他蹲下來,笑出一口黃牙,眼睛睜得大大的:“是聰聰吧?”妹妹被嚇得哭出聲來,他全然不理,又對我說:“我是你四叔啊,小時候還帶你打過麻雀呢,不記得了?”
四叔是個孩子王,他小時候帶我捉田雞,打麻雀,釣龍蝦……倘若有小夥伴欺負我,我都不敢告訴四叔,否則,欺負我的人一準遭殃。這些我都記得,可眼前這個人,怎麼也不可能和四叔聯絡起來。
那人笑著笑著突然一激靈,似乎意識到他等著我的真正目的:“聰聰,老家現在搬到哪兒去了,村裡現在都沒人居住,想回都回不了。”我攙著妹妹,在前面領著路,那人隔著很遠跟在我們後面。
我推開門,發現親戚們都趕回來了。一進門,妹妹哭著跑進廚房。大人們的吵鬧聲,掩蓋了我們兄妹的動靜,直到四叔把頭探進堂屋。
坐在桌子旁邊的爺爺“啊”地大聲喘了一下。那種聲音是我第二次聽見。第一次,是爺爺心臟病發作時。這一宣告顯更加劇烈。四叔站在門口不敢進來,全家人都在照顧爺爺,沒人管他。他們好像都不願跟四叔接觸,哪怕是一個短暫的眼神互動。
爺爺醒來已是深夜,四叔每隔一個小時都會給爺爺焐腳的暖水袋換一次熱水。爺爺醒來第一句話就問:“老四啊,在裡面想不想家裡人?”“想。”
爺爺閉上眼睛,沒有再問。四叔佝僂著背,頭貼在床頭。整個屋子很安靜,堂屋爐子上的熱水被燒開,沸水翻騰,“咕嚕咕嚕”地作響。
那天,四叔完成了10年刑期,出獄回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重隔10年,老劉家再一次團聚。
按照老家的習俗,有人生病,病因一定要請走。可這次爺爺生病,病因是四叔。爺爺護住四叔,堅決不讓走,親戚們都不好說,只能無可奈何。
三媽衝了出來,指著爺爺的鼻子罵:“就你家這玩意兒,你還護著呢?他遲早禍害死你們一家。他害著誰,我管不著,可就是別影響我們家劉暢。劉暢要是被人戳脊梁骨,你們誰也逃不了干係!”
三叔和三媽很少回家過年,今年回家好像是要跟爺爺商量土地劃分的問題。三媽口中的劉暢,是我堂哥,在縣城做公務員,這幾天要升職了。三媽怕兒子的競爭對手拿“殺人犯”四叔來說事兒。
四叔最終還是走了,在老家土地廟旁的一個棚子裡,跟一個拾荒者度過了一個春節。
爺爺有四個兒子,我爸、二叔、三叔還有四叔。1975年,奶奶作為高齡產婦生下四叔後,因大出血不治而亡。那時我爸9歲,所以四叔只大我20歲。四叔在農村是個活脫脫的“皮王”。長大後,四叔也是不按規矩來,家裡祖祖輩輩都是種田的料,他硬要出去闖。因為,家裡實在是太窮了。
1997年,四叔22歲,去了上海,找了安的活兒。本以為可以在上海安身,卻抹了黑——四叔“殺人”了,蹲進大牢。殺人,而是他老闆失手殺了人。
有一位賭客出幹,贏了大幾十萬,時,被守在一旁的老闆貼身保鏢逮住。掃客身上一拽,搜到一身的出千裝備。老槓個。其序女曰:曰/曰 上東大人的臉抹了黑——四叔“殺人”了,蹲進大牢。其實四叔沒有殺人,而是他老闆失手殺了人。
有一位賭客出千,贏了大幾十萬,最後準備逃走時,被守在一旁的老闆貼身保鏢逮住。捉人拿贓,在賭客身上一搜,搜到一身的出千裝備。老闆暴怒,順手撿起桌子上的匕首,捅死了賭客。
其實四叔知道,還有一位出老千的——就是那個賭桌的發牌員阿忠。他歪心太重,想狠敲一筆,就找到阿忠的出租房,直接挑明:“那個出老千的死了,他跟你是一夥兒的吧?現在老闆還不知道,他知道了,估計你也得死。我問你,你想不想活?”阿忠跪下說:“是他逼我的,我欠他錢,再不還,老婆就沒了!”
“你倆肯定不止一次吧,你弄了多少錢?”四叔問。“只一次,他就被逮了,他活該!”阿忠說。四叔心軟走了。臨走前說:“你當沒見過我,也別再出千了。”四叔敲詐沒成功,反而引火上身、阿忠給老闆出了個好點子,找個替罪羔羊,含沙射影地說四叔是個好角色,可以收買四叔替老闆坐牢。
這正中老闆下懷。他讓四叔替他坐幾年牢,答應每年給15萬。又恐嚇四叔,若不肯,就去把他的寧波老家攪得不安寧。四叔害怕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錢。15萬,在1998年的農村是啥概念?在全家每年收入都不過幾千塊的日子裡,15萬,猶如一枚重磅炸彈,炸醒了四叔對所有美好的渴望。
四叔同意了,法院判了10年。
為讓爺爺斷了念想,四叔寫過一封信:“就當娘生我的時候,我也死了。”當時全家人一致聯名,在劉姓族譜上劃去了四叔的名字。“此人,以後是死是活,與劉家毫無干係!”爺爺在回信中寫道。
四叔進去之後,鄉鄰們說我們一家都有殺人基因,跟我們劃清界限。後來,一大家子都離開了那個村子。父親和爺爺搬到現在居住的城中村北,每次逢年過節,大家都約好了來我家過。
那天下午,四叔從黃湖監獄出來。出獄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離監獄最近的銀行。
從出獄那刻算起,他開心了不到2小時。銀行櫃檯小姐說:“先生,存摺裡有50萬。”四叔反覆確認後,當場發了瘋。警察趕來時,他忽然清醒。畢竟當年也是違法的交易,最後他消失在夜色中。
四叔在外面漂泊了幾天,決定回來。他一路走一路問,直到蹲守在老家的土地廟,尋到了我。
城中村北由一條主巷貫穿,主巷上又分出四五條小支巷,我家在一條支巷上。四叔在離我家相距200多米的主巷口,買了棟房子,開始新的生活。
四叔坐過牢,跑遍人才市場也沒人敢僱他。那時,城中村北經常聚眾賭博。街道巷口、馬路旁邊,混跡著大量喝醉了發酒瘋的賭鬼。四叔眼光獨到,看中這個機會,想在城中村東邊小街附近開一家棋牌室。
四叔買房花了20萬,可一間棋牌室連房子帶裝修至少要50萬。苦思冥想,他決定賭一把。為了增加贏面,他做了他曾經最痛恨的事——出千。
四叔在安徽、江蘇等地買了一批“千術”工具。有一種出千工具叫做“錶針耳麥”,玩的時候戴上腕錶,腕錶裡有一種高科技的掃描裝置,能掃描出每張發的什麼牌或花色,然後在玩家耳朵裡放一枚針孔耳麥,無論是紙牌、麻將還是骰子,都能掃描出來。入了局的人想贏錢,簡直是天方夜譚。
購入裝置的第二天,爺爺來到四叔的家,隔著大門扯開嗓子喊:“老四,你趕緊把那玩意給扔了,剛回來就不安生,你是又想進去了嗎?”
三媽不知從哪兒跑出來,往四叔家的門上踹了一腳:“你們老劉家怎麼出了你這麼個作踐玩意兒!”“如果劉暢受你牽連,你看我怎麼對付你。”又瞪著一旁的爺爺:“趕緊勸住你小兒子,土地的事情也要抓緊,別一天到晚拖著,沒幾天了!”
三媽來的意圖很明顯。劉暢已經被競爭對手戳脊梁骨了,得虧工作能力強,要不然早被搞掉了。
四叔開了門,忙著在堂屋沏茶。爺爺死活不進去:“你出來好好找個正經活兒幹不好嗎?養活自己不就夠了嗎?你到底要搞麼事?”三媽氣得跺腳,“老四啊,你看在你三哥的分上,安生點!”
她走後,爺爺嘆氣道:“你張大爺的兒子,是城門口工地包工頭。你要是踏踏實實的,我豁出這張老臉,也讓他兒子給你留一位子。”四叔攙著爺爺進門,“撲通”跪倒:“老爹,你等我這一回。這次過後,再也不搞如果被逮,我也活該認了。”爺爺一急,柺棍抽在四叔的背上,氣呼呼地走開,發誓老死不相往來。四叔攛了個局,他自己當地頭(發牌員),和從小玩到大的哥們阿洲一起糊另一個大老闆。倆人壞心對壞心,一拍即合。阿洲負責找人,四叔負責熟悉,除錯裝置。於是,一場十賭九輸的局開始了。
短短一個小時,阿洲就贏了30萬.阿洲賭蟲上頭,止不住手。賭本達到45萬時,不知為何,四叔口吐白沫、鼻子流血,倒在地上。其實,是四叔演的。不演不行啊,不演賭局怎麼停得下來?最後四叔分得30萬,足夠開一家棋牌室。
出院後,四叔帶著幾瓶茅臺來到我家。他塞給我一個大紅包:“當零花錢,別給你媽。”酒過三巡,四叔老淚縱橫:“老大,我剛出來,汙名大得很,營業執照根本辦不下來,你幫我一下。”父親一直在喝悶酒,沒說話。“小時候我皮慣了,作業不寫,你幫我寫,書不會背,你追著哄我背,尿床沒褲子穿,你自己不穿也要給我穿。老大,這次算我求你。別的老四不敢承諾,以後老四不管是富是窮,你要是少個腎,我把腎給你……”父親的臉紅到耳根,整個手臂青筋都鼓鼓的。“老四,犯法的事再別幹了,曉得不?”他答應了。
四叔的棋牌室開了起來,其火爆程度不亞於一個小型商場。到2013年,四叔的棋牌室已經開到第3家。此外,他還有一家中型超市。三媽常跟三叔抱怨:“你家老四那麼有能耐,我們一丁點光都沒享到。你看他車子、女人換了多少個了?"四叔車子換了多少我倒是沒注意,但女人換得實在是勤。
我每天上學都要經過四叔家門口,四叔一見著我,就主動開車送我去學校。每次坐車,後座的女人都不一樣,不過她們大多年輕漂亮。我問四叔:“四叔,為什麼每次喊的‘四媽'都不一樣啊?”
後座的“四媽”被逗得哈哈大笑,四叔的臉上一陣紅一陣白。他讓“四媽”拿一堆吃的喝的塞到我書包裡,跟我說:“你好好學習就行了,大人的事小孩子別管,下次再考鴨蛋,看我不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