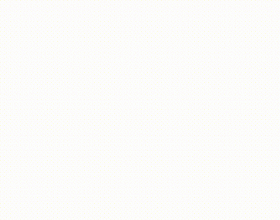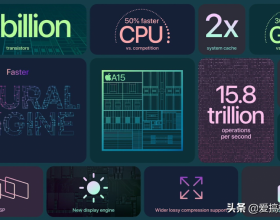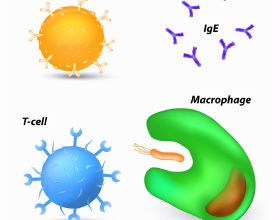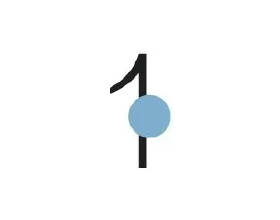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
隨看隨想
雅貝斯是法國詩人、思想家,文字與生命、思想的關係是他終身思考的話題。本文的主題也是如此。人在使用文字的時候,如何確定自我與文字之間的關聯?如何保證文字準確表達了自己的思想?雅貝斯用詩化的語言創造性地進行了闡釋。但是,他是確切表達了自己的意思,還是又開鑿了另一道深淵?只能由讀者自己評判了。正如老子所說:“名可名,非常名。”莊子亦說:“名者,實之賓也。”名實之間,究竟是言不盡意,還是言能盡意?值得深思。(楊贏)
假如某個字詞取你性命而去,意味著你還有一條性命可以奉獻。
任何字詞都是死亡對其自身的挑戰,那是死於自己名下的唯一機會;
是死於用其名字寫成所有書的唯一機會。
詞語從自己的詞語中攜死亡而去。
*
人藉某種相似定義自我,這種相似既是他的定心丸,又是他的希望所在。
你評論的這本書不是你讀的書,而是你擅自佔有的書,它只是和你讀的書相似而已。
他說:“書寫是否意味著承擔起一本書的終極閱讀,而閱讀這本書的必要性是我們存在的理由——先是精神層面的閱讀,然後才藉自己的字詞去閱讀它?”
“此時,首個字詞就會成為所有書屬意和期待的使者。它會像聚焦點一樣引人注目,併成為無數詞語透過尾隨其後亦能成為的可視、可讀之詞語的唯一機會。”
“有了這個字詞,紙頁永遠不會空白。”
“此即為何它會即刻引發我們的懷疑——懷疑在我們寫作的書中有一本已經寫就的書,其遽然出現暴露出沉默曾經統轄之地的無知。”
(“沒有沉默”,他在其他地方說過,“因為死亡中沒有無知”……其他地方,也就是說,是在我們沿著一條叵測小道走向字母的迂迴處。)
當我們關注某個詞語、某個句子的時候,當我們力圖清晰表達的東西變得含混、漸次暗淡的時候,就表明正有某件事情在暗中醞釀、組織和準備實施。
那可能是最讓我們擔心的一件事。
*
如今想來,這就是那件被回憶、被記住的事。這些話語,這一沉默,要將我們引向何方?或許就是在此。
男人和其他人的聲音。女人和她們的柔弱。街道像荒漠,回憶則像一臺吃角子老虎機,在某個好日子、某個千載難逢的幸運日子,一下子吐出相當於一個月、一年、一個世紀——或若干世紀——的硬幣,而且即付即用。我們所有的往昔——以及往昔的往昔——就像這饋贈的神奇銅幣、銀幣:某種很快便會揮霍一空的運氣。
我想起來了。其清晰度雖不能令我滿意,細節也不是很多,但我彷彿以同樣的方式重新經歷了這些瞬間,當然仍有所不同。彷彿這些瞬間雖然才發生在當下,卻長留在某一天、某一晚發生的事情裡。好生奇怪!於是,書與其書的往昔——或無數往昔——又有了一副真身,又找回了第一副軀體和忘得精光的話語——如果不是遺忘,也是短暫失憶——那些混亂的、一觸即發的話語,面對新的沉默,比古老的沉默還要古老,但卻是當下的沉默,伴隨著白晝無聲的地獄和黑夜深海般的背面。
如今想來,這就是那件被回憶、被記錄的事,可發生在哪兒?什麼時候?一個詞語的部落,一個詞語的家族及其子孫後代和直系尊親——以至於我們分不清父親和兒子,女兒和祖母。那些返老還童的字詞,雖歷經變遷,卻依舊忠誠於它們的目標,忠誠於字母古老的憧憬,忠誠於它們或沙啞或和諧的聲音,雖然重新調整,卻仍彼此相似。那些名字被人憎惡、畏懼、愛戀、悼念、受人歡迎或倍受冷落;
而我的名字除了書——在它的陰影下完成的書——以外沒有其他現實意義,它等著被已寫或仍在寫的書的陰影吞噬。
*
我是誰?或許是追隨飽經風霜之臉的瞬間之臉,或許是為了僅有的一張臉而被忘掉的所有的臉,但那是哪張臉呢?
與……相似並不意味著變成他者,而是某種程度上允許他者成為自己,意味著與之死去兩次,當然也透過我們的主觀聯絡兩次體驗其死亡。
此外,當我們千方百計縮小我們之間的差異時,潛在的相似會讓我們猝然感受到自身難耐的孤獨。
他說:“遺忘是相似的終結或開始。面具落下,那張迷惑人的臉便復活了。”
死亡像個藝術家,它雕琢生命的臉:我們的臉。
“啊,”他說,“我之所以要在我內心裡下潛得更深,是為了單獨面對所有我曾經的臉,它們在我的前額和麵頰上刻滿了皺紋。”
*
時間僅與時間較量,卻以永恆與自己較量。
時間的永恆或許僅僅是時間永恆地迴歸其廢止的時間。廢止成就了某種時間的永恆而無須共同的尺度:令人恐懼的無限。
一切書寫全都從容不迫,遵從著時間的節拍,沐浴於時間中——如乘火車或騎馬一樣——化為時間本身的書寫。
如是,也許會有書的某段時間誕生於它拒絕領受的時間中,只會更加擴充套件整個詞彙。
我們的一個眼神,一個最不起眼的動作都會創造出某種對抗時間的時間,但它們並不想罷手。
這是創造和聽命於創造的時間,最終會由史上忠實於瞬間的時間所擔當。
字詞的時間不是過去,不是當下,也不是即將到來的時間。它是溢位的時間,有如襯裡開線時會有某個部位從衣角里露出來一樣。
表達的時間。極端的時間。
這又像我們只在一本有瑕疵的、絕不會敞開的書之邊界上書寫,在過寬的紙頁的奢侈邊緣上畫滿了符號。
他說過:“哦,黑夜中更幽暗的黑夜!宇宙深處,字詞正綻放花朵。”
……
我們更擔心的是:這個允諾。
*
書與書之間,在這個虛空的間隔,某人喘著粗氣,坐立不安,他在呼號。他以特別的方式呼號,呼號,主要是求援,好像有誰馬上會聽得到,好像有誰能聽得到,好像誰都聽得到他的呼喚、他的呼號似的;
其實,此人無非是某人的記憶,是一道傷口;是某人如今已無記憶、無傷口、無未來的愛情:如纏在更緊的繩結中的一個繩結,如刻滿虛空的一片虛空,如冷漠空間裡逐漸衰竭的一絲呼吸,如火場數百公里外的一道煙圈,飄移的煙霧漸行漸遠,直到變為火焰的遺憾,哀嘆著自己的愚蠢和不幸。
(選自埃德蒙·雅貝斯《相似之書》,劉楠祺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
《中國教師報》2021年09月29日第9版
本文來自【中國教育新聞網】,僅代表作者觀點。全國黨媒資訊公共平臺提供資訊釋出傳播服務。
ID:j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