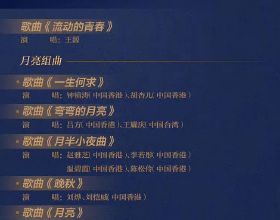【青年學者論壇】
作者:劉宇耘(山西大學文學院博士)
劉禹錫《望洞庭》雲:“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裡一青螺。”這首詩不僅被選入多種古典文學普及讀物,而且多次入選小學語文教材。201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語文教材將此詩前移到三年級上冊,表示其更當早點學習。瞿蛻園稱“此詩頗為古今傳頌”(《劉禹錫集箋證》),可知此言非虛。
那麼,此詩“可傳頌處”何在?當代諸家幾乎把目光都集中在秋月下的湖光美景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集體編撰的《唐詩選注》,於此詩的“說明”一欄中說:“詩人把秋夜的湖光山色描寫得優美動人,儼如山水畫一般。”劉學鍇先生品賞此詩云:“在明月的映照下,浩瀚的湖面與澄清的天宇連成一片,呈現出月光如水水如天的浩茫、靜謐而和諧的景象,也秀出詩人目接此景時內心的安恬愉悅。”(《唐詩選注評覽鑑》)。周篤文先生說:“此詩描寫了秋夜月光下洞庭湖的優美景色”“在皓月銀輝下,洞庭山愈顯青翠,洞庭水愈顯清澈,山水渾然一體,望去如同一隻雕鏤剔透的銀盤裡,放了一顆小巧玲瓏的青螺”(蕭滌非等編《唐詩鑑賞辭典》)。不難看出,認為《望洞庭》描寫的是月下湖光景物,已成為學術界共識。而且他們認為其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夜景,如瞿蛻園先生說,此詩“必至其地者尤知其賦物之工也”(《劉禹錫集箋證》)。
其實,若“至其地”,臨其景,反而會感到這種描寫是完全不合邏輯的。第一,“望”是遠視之義,漢代劉熙《釋名·釋姿容》雲:“望,茫也,遠視茫茫也。”月夜並非遠望觀景之佳時,因其看遠所得只能是一片朦朧,什麼也看不清,緣何詩題要名《望洞庭》?詩中也特意提到“遙望”,亦可證明詩人作詩之時的遠視視角。並不是說夜不能望,而是說夜望之景與白天不同,故古詩詞描寫夜望時,其詩題則要加“夜”字以明之,如江總有《三善殿夜望山燈》,李端有《早春夜望》,陸游有《江樓夜望》等,皆是證明。第二,“潭面無風鏡未磨”,顯然寫的是洞庭湖面的整體形象,但在月下所能看清的只能是區域性,即如查慎行《中秋夜洞庭對月歌》所云“鏡面橫開十餘丈”,緣何能看到廣闊的湖面像鏡子一樣平靜而透亮?第三,月下不觀色,這是基本生活常識,緣何能看到山水的青翠之色?第四,湖水在日光的強照射下才有可能反射出大面積的白光,月下的湖水只能是“層波萬頃如熔金”(劉禹錫《洞庭秋月行》)、“月光浸水水浸天”(查慎行《中秋夜洞庭對月歌》),緣何能看到如同“白銀盤”一般的色澤?且“白銀盤”更像是完整的湖面形狀,再次與月下的區域性視角產生矛盾。顯然這都是違背常理的。詩中的“鏡未磨”“白銀盤”“青螺”歷來被讚譽設譬精警,顯然是建立在現實視覺基礎之上的,而還原詩中場景,不但看不出其精警之處,反而疑點重重。問題何在?
筆者認為,此有兩種可能:一是作者根本沒有認真觀察過洞庭湖的景觀,像古籍中許多以“瀟湘八景”之“洞庭秋月”為題的詩一樣,像是在畫卷上題詩,只是從概念出發,憑空虛構,因此這類詩中就出現了“玻瓈萬頃清無滓,只有君山一點青”(元楊公遠)、“望中青似粟,約莫是君山”(元程文海)、“光浮夢澤千潭碧,影譙君山一點青”(清聶銑敏《蓉峰詩話》卷四)、“幾峰森列青崔嵬”(宋葉茵)、“一碧九萬里”(宋劉克莊)、“扁舟泛碧波”(明黎擴)之類的詩句。二是版本有誤,現通行的本子不是劉禹錫的原作。
劉禹錫《歷陽書事七十韻》序雲:“長慶四年八月,予自夔州刺史轉歷陽,浮岷江,觀洞庭。”可以肯定,詩人確實於秋天到過洞庭湖。在作者的集子中有兩首與洞庭秋景相關的詩,一是《望洞庭》,另一是《洞庭秋月行》。據卞孝萱《劉禹錫年譜》,詩人“離夔州時,於巫山神女廟,遍覽古今題詩”,“沿途遊覽名勝古蹟…至宣州宴遊”。從而可見途中行程鬆快、社交活動也豐富,而洞庭二首疏朗平和、意境悠遠的景色描繪,正符合詩人遊山玩水的心境。這兩首詩應作於同一時期,若是一寫白天景觀,一寫月夜風色,那麼上述疑點則可解答。前者突出的是“望”,詩人身在遠處遙望湖明山翠,全為日下之景。後者突出的是洞庭月色,詩人在月下游湖,故看到的是“孤輪徐轉光不定,遊氣濛濛隔寒鏡”。兩者皆為實景描寫,一脈相承。由此可以肯定,此詩違背邏輯的問題不在作者,而是版本上出了問題。
考《望洞庭》一詩的版本,大約有三個系統。一是別集、總集和各種選本系統,二是詩話系統,三是類書系統。在前兩個系統中,詩的首句都作“洞庭秋月兩相和”。類書系統如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十四、祝穆《事文類聚前集》卷十四、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五、清《御定淵鑑類函》卷二十四等,引此詩首句“秋月”皆作“秋色”。就一般規律而言,類書重在分類抄寫,對原文不作修改。而集部之書,由其文學性質所規定的價值取向,編撰者往往會根據自己的理解和判斷對文字進行改動,以符合其審美追求。因此關於此詩的第三句,在集部中就出現了好幾個不同的版本。筆者認為,類書中的“湖光秋色”比“湖光秋月”應更接近於原作,它所依據的應該是未改動前的本子。若據此改“秋月”為“秋色”,則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了,翠色、白銀盤、青螺皆為“秋色”的呈現,也皆是白天的景觀。“洞庭秋色”本是歷代文人所關注的美景,《楚辭·九歌·湘夫人》篇雲:“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張說《送梁六自洞庭山作》“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峰水上浮”,李白《秋登巴陵望洞庭》“明湖映天光,徹底見秋色”,清張英《廷瓚承命致祭衡嶽》“木落洞庭秋色好”等,皆可以證明。因此劉禹錫秋日經其地賦其景特意強調“秋色”之美,也在常理之中。
當然版本問題比較複雜,比如此詩之第三句,就出現了“遙望洞庭山水翠”“遙望洞庭山翠小”“遙望洞庭山水色”“遙望洞庭山正翠”等幾種不同的傳本,孰是孰非,這裡暫不作討論。我們關注的是這種違背常識的“改版”是如何出現的。這個問題至關重要,因為它普遍存在於古典詩歌中。從作者的角度考慮,寫景詩一般是詩人親臨其景、觸景生情的創作,因而多是實景實情的描寫。一旦形成文字向外傳播開來,讀者便會脫離開事物本身,僅從詩的文字出發,透過想象還原詩境,有時還會憑著自己的體會,對文字作適度修改,使其在虛擬的世界裡更具有美感和廣泛性。如賀知章的《回鄉偶書》,最早的版本第三句作“家童相見不相識”,而現在通行版本則作“兒童相見不相識”。“家童”指家裡的僕人,顯然對作者的身份是一種限定。而“兒童”是小孩,則是遊子還鄉都可能遇到的情景。李白《靜夜思》第三句,唐宋時的版本都作“舉頭望山月”,而明以後則出現了“舉頭望明月”版本,現在通行的則是後者。“山月”對作者所處之境是一個限定,而“明月”則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的。這樣的修改實際上是“意境再造”。就《望洞庭》詩而言,“秋色”本是實景的書寫,改為“秋月”則變為虛擬之景,秋天的皓月與青螺般的小山、明鏡般的湖面、銀白色的湖光組合在一起,使詩境具有了童話般的幻想色彩。這一再造的詩境,在讀者的冥想中更具有感染力,這也是後人選擇此一版本的原因。但這已背離了事物本身,也已經不是劉禹錫的《望洞庭》了。大量“改版”後的經典詩歌,其實都面臨這樣的問題。它們不再是詩人個體的原創,而變成了公共藝術產品,當讀者接受“改版”的同時,接受的可能只是語言層面的意義,卻無法深入作者的心靈世界。
《光明日報》( 2021年07月19日13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