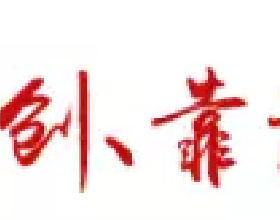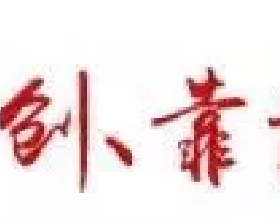魯北記憶:“牛事兒”散記
原創 李玉德
佇立故鄉西北灣甜水井臺上,背倚柳絲倒掛的垂柳,乍見夕陽西下,餘暉下西北灣冰涼的水紋也似乎有了暖意。西北灣四周掛滿餘暉的青草尖在夕陽的籠罩下,顯得有些迷迷朦朦。尤其是西北灣東邊靠近圩壕一邊的蒹葭挺挺的沐浴在餘暉裡,給人帶來一種悵惘的遐想。忽見一頭老牛,腳踏青草,身披霞光,闖進了畫面。牛背上還橫坐著一個玩童,正用一枚短笛信口吹奏著斷斷續續的曲子,愜意地隨晚風而來。鄉村的晚景在老牛的腳步聲中和晚笛的吹奏聲中,立馬生動了起來……
這應該是七十年代故鄉的光景吧!故鄉的這一光景時常浮現在我的腦海裡,如夢如幻。有時甚至懷疑這種景象的真實性。每到此時,總是有那麼點兒強迫性地去細理童年的時光。
故鄉的春景給人以希冀和憧憬,而故鄉的秋景卻給以收穫和欣喜。
到了秋收時節,魯北大平原上成片成片的高粱挺直了腰桿,就如同魯北的漢子,在夕陽的映襯下漲紅了臉,在鄰家玉米姑娘飽含深情的注視下,羞澀的低下了頭顱。旁邊不忍偷窺的穀子謙遜的象個教書先生,正低頭構思自己的華章……
秋收時節的傍晚,故鄉的田野顯得格外的生動。夕陽下,經過一天勞作的老牛車揹負著秋的收穫,在夕陽的注目下,託著長長的影子,向炊煙裊裊的村舍低頭賓士著,碩大的牛蹄叩擊著大地,如同交響樂中的節拍,沉穩而動聽。不知牛隊伍裡哪頭老牛打了一個響鼻,大道上的同伴似乎聽到了召喚,都在響鼻聲中加快了步伐……一時,鄉村的收穫聲,人們的歡笑聲,牛蹄對大地的叩擊聲,車輪的滾滾聲,匯成了鄉村最為生動的樂曲。此時此刻,此情此景,“老牛自知夕陽短,不用揚鞭自奮蹄”的畫卷從原野青紗帳深處一下子湧向了村口……
站在大隊三秋生產指揮部廣播塔上,拿著喊話筒的我,忘記了廣播,心靈被這一滾動的場景深深震撼了……
七十年代,正在讀小學的我被推薦為大隊三秋生產指揮部宣傳員。正是這一經歷,讓我有幸站到了村口高高的廣播塔上(借用村口幾株高大的楊樹塔建而成),居高臨下,目睹了鄉村秋收時節老牛晚歸這一動人心絃的場景。
也許,正是這一場景讓我和牛結下了不解之緣。起初,對牛的感知,只是一種膚淺的認識。只是站在高高的廣播塔上領略老牛晚歸的風景罷了。直到後來,對牛的興趣和進一步認識,還得從一部電影《青松嶺》說起,尤其是電影中中那激動人心的插曲!
長鞭哎那個一呀甩吔~
叭叭地響哎~
哎咳依呀~
趕起那個大車
出了莊哎哎咳喲~
劈開那個重重霧哇~
闖過那個道道梁哎~
哎哎咳咳依呀
哎哎咳咳依呀
哎哎咳咳依呀哎哎咳呀
要問大車哪裡去吔~
沿著社會主義大道
奔前方哎~
電影和歌曲讓我迷戀上了趕車,就時常纏著生產隊的車把式學趕車。那時候,馬車是不敢,而且也不讓練習的。但趕個牛車還是滿可以滿足一下好奇心的。當時,不但天天纏著車把式學趕車,還借了一把趕車的大鞭,天天學電影里老車把式張萬山抽鞭子。老車把式的鞭頭可有準頭了,只見老車把式鞭子一甩,蘋果樹上一個鮮紅的蘋果就應聲落地了。我也照葫蘆畫瓢,在我家的梨樹上天天練習……
練習的結果是,一個梨也沒抽下來,卻抽光了滿樹的梨葉子。爺爺見狀曾生氣地質問:“你和梨樹有仇呀!”
在練習趕車中雖沒多少進步,卻漸漸瞭解了不少牛的習性。牛雖然不會說話,但絕對能聽懂人言,懂得人情的。有句話叫做:“牛馬比君子,畜類也是人”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吧。比如人對牛發出的指令,“得,打,喔號,越依……”這些牛語,牛都不但能聽得懂,而且還按指令進行著準確的勞作。還有許多有“靈性”的牛,根本不需要主人發出指令,就可以自覺的從事自己熟悉的勞作。比如拉車走到熟悉的路上,即使主人不做指令,無論拐彎抹角,老牛都能安全的把車駕駛到目的地,絕對比今天A照的駕駛還要安全。過去曾說老馬識途,這老牛也同樣識途。
牛,也是會搗蛋的,也有犟脾氣。生產隊有一對梨花牛,一頭又會偷懶,還活道不好,常常幹著活就玩趴蛋的把戲。有一次在耕地中偷懶的梨花牛又玩趴蛋,扶犁的社員怎麼拉都不起來,忽然心血來潮,就用火燒牛屁股,儘管牛屁股燒掉了一層皮,牛卻仍然沒有起來。為此,燒牛屁股的社員還捱了批評。而另一頭牛那不僅活道好,而且腳步還快。每次給隊辦企業去塘沽送魚筐,其他生產隊的馬和驢都跑不過它,四隊的社員自豪的稱它為“神牛”。
人民公社時期,各個生產隊都有飼養處和專職的飼養員。因為牛是生產隊的重要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牛在農業生產勞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公社明令禁止宰殺耕牛。當然,也有例外,當年,我們生產隊的一頭老黃牛病了,經向上級請示批准宰殺。那個時候殺頭牛,不但是生產隊的大事,而且,在人們的潛意識裡是要造天譴的,一般人是不敢動手的。我們生產隊只有一個叫長恩的光棍漢敢對牛動手,但也不代表他心裡沒有忌憚。因為,動手之前他都要喝碗壯膽酒,而且把刀藏在背後,嘴裡還唸唸有詞,“人家不賣俺不買,人家不吃俺不宰”隨說著隨靠近牛,突然出刀,把刀一下子全部捅進了牛咽喉裡了,隨之,鮮紅的血一下子噴湧了出來……
可是,在這次宰殺老黃牛時卻遇到了意外。當飼養員從牛棚把牛牽出來時,老牛的孩子小黃牛跪爬著,哀叫著跟了出來。那小黃牛一步一跪,一步一爬的無助的哀叫聲,讓人心裡一緊一緊的。儘管有幾個老人出來做了阻攔,可宰殺的步驟仍照常進行。當把老牛牽到長恩面前時,老牛突然跪下了,同時,兩行熱淚從牛眼裡奔湧而出……
此時的長恩緊了緊腰帶,咬了咬牙,厲聲呼到,“把牛眼給我捂起來!”幾個人趕緊用一條破口袋片子捂起了老牛眼。長恩一看急了,又大喊,“捂住小牛的眼!”小牛在掙扎中,被捂起了眼睛……
在哀嚎中,老牛倒在了血泊裡……
他日耕作,依依田間。
今被宰殺,哀哀悽惋。
牛猶如此,人何以堪。
……
牛隻是不會說話而已,心裡明白得很。據我們村老人們講,在日偽時期,鬼子漢奸常常進村牽牛宰羊。為了防止鬼子漢奸把牛牽走,一聽鬼子進村,家家戶戶都會把牛牽到野外的莊稼地裡,指令牛伏著別動,這樣就躲過了鬼子的搶掠。時間久了,鬼子一來,只要把牛放開,牛就知道有了危險,便爭先恐後地跑出村子,自覺地潛伏進莊稼地裡,即使一天不吃不喝,也不發出任何的鳴叫。待鬼子離開後,主人們便會站在圩子牆上向野外發出呼叫,牛兒聽到主人呼叫,便會鑽出莊稼地,向圩子門湧來,並會用獨特的眼神在大街上尋找著自己的主人,見到了主人都會搖著尾巴向主人致意,毫無差錯地各進各家。
1978年冬,小崗村18位農民以“託孤”的方式,率先在土地承包責任書按下鮮紅手印,實施了“大包乾”。這一“按”竟成了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它改變了中國農村發展史,掀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小崗村也由普普通通的小村莊一躍而為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從此,貧窮落後的小崗村便成了學習的榜樣,一時,單幹風吹遍了全國。
隨著單幹風的到來,不僅吹垮了幾十年的生產隊公共積累,也吹垮了生產隊若大的牛家庭。
到了單幹風吹到魯西北時,已到了八十年代的初期。八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別寒冷。有一天,料峭的寒風吹打著雪花,直往人的衣領裡鑽。生產隊飼養處裡的十幾頭牛被一一牽出了屋外,拴到了場院邊上的木柱子上,要進行評價分配。牛,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命運,都不情願地邁著步子,鳴叫著,被牢牢地拴在了雪地裡。不管牛多麼不情願,但卻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由於戶多牛少,估價後分配,好幾戶人家才能分到一頭牛。在牛分配中,我家也和六戶合夥分到了一頭黑事牛(母牛)。長恩幾家子分到了那頭黃牛,也就是被長恩宰殺了母親的那頭。正當長恩屁顛兒屁顛兒地去牽小黃牛時,不知是有意無意,長大的小黃牛一頭把長恩撞到了牆上,一下子撞斷了三根肋骨,若不是被人攔阻及時,非給當場撞死不可。
單幹後,合夥的牛由於在飼養和使用中出現了種種矛盾。最終,人們都不得不把牛陸續的賣掉了。我家合夥的黑牛,最終的結局也和其他的牛一樣,終於也被賣掉了。記得,在黑牛被人牽走的那天上午,正路過生產隊飼養處的廢墟。黑牛見到廢墟,也許也和人見到了故土一樣,有一種別離的不忍,突然掙脫韁繩,跑了上去,然後慢慢伏下去,頭衝著村口,發出了一聲聲低沉的哞哞的叫聲……“哞……哞……”
老黑牛的別離,讓我們家終於連一根牛毛都沒有了。所有的輕重農活一下子全都落在了家人的肩上,一時間,人們又進入到了刀耕火種的原始狀態。一切的農活,耕耩犁耙,運肥運糧,一切都得靠人力勞作了。我們家兄弟姊妹七個,我是長子,當年二十來歲的我便擔負起了牛的使命。耕地,耩地,拉車,我就被理所當然地塞進了轅裡,開始了拉套生涯。當一步一步跋涉在田壟間,當艱辛的腳步邁得腿痠腰痛的時候,最大的夢想,就是有一頭能從拉套中替換下我來的牛。這只不過是一種夢想而已,疲憊的腳步依然要在田間跋涉。我不知道,這樣的日子何時才是一個盡頭。以致那個時段常常做夢,夢到自己變成了一頭耕牛。
為了擺脫這繁重的農業生產勞動,為了家庭能夠有一頭夢寂以求的耕牛,我以少有的勤奮,努力準備著中考。到了一九八二年,終於如願以償,步入了惠民師範這一神聖的求學殿堂。兩年的惠師生活轉眼飛逝。到了一九八四年,我從惠民師範畢業了。畢業分配後,人生的第一個改變,就是領到了工資。雖然,每月的工資僅僅是六十多元,但我第一個感覺就是現今的自己已經具備了買牛的資本。於是,我向所在的單位周劉聯中說明情況,暫借三百元的買牛款。單位領導非常同情和理解我的請求,經研究後很快答應借錢給我,所借款項每月從我工資里扣除三十元,以致扣完為止。一方面對校領導的關懷千恩萬謝,一方面興沖沖的跑回家,把一厚摞三百元的現金鄭重交到了父親手中,由父親擇日去集市買牛。當父親打聽到鄰縣無棣的耕牛比較便宜,便在深秋的一個無棣大集上,起了個大早,約上鄰居一個王姓大伯,揣好了錢,奔無棣縣城去了……
父親買牛的這天,人雖然在學校上課,心卻牽掛著牛事。於是,上午集中上完了全天的課程,請假後,跨上腳踏車,急急忙忙往家中趕去。雖然是奔波在鄉間的土路上,但胯下的腳踏車卻在腳下生風,二十幾裡的路程下來,身上早已冒出汗來。到家後見父親還沒回來,就隨便吃了幾口飯,又跨上腳踏車,向無棣的方向奔去。當我騎車走到十多里外的銀高鄉駐地時,便遠遠見到父親和鄰家大伯牽著一頭活蹦亂跳的小黑牛,沿著公路走來……乍見此情景,一種如夢如幻的感覺一下子襲上心頭。為了尋求一種真實的感覺,我迎上去一把牽過了小黑牛,任小黑牛在手裡蹦噠和衝撞著。正是這種蹦噠和衝撞,才讓我激動的心更加踏實。當父親確定我牽牛穩當後,在我一再催促下,風塵僕僕步行了幾十里路的父親和鄰家大伯終於騎腳踏車放心地走了。在寬寬的公路上,我獨自牽著小牛,任小牛在手裡撒歡蹦噠。想不到,走了這麼遠的路,小黑牛還依然那麼精神,待仔細看來,小黑牛全身上下無一點雜毛,黑得如綢緞一樣,在陽光的照射下熠熠發光,兩隻黑黑的牛眼在怯生生地審視著陌生的我,一對剛剛鑽出頭皮的牛角倔犟地挺立於黑毛之中,兩隻耳朵警惕地翻動。見到小黑牛如此可愛,我便上前去撫摸一下它的脊背,剛剛觸到牛毛,小黑牛便機警地一下跳開了,我趕忙抓緊手裡的韁繩……
當牽牛進村時,我故意放慢了腳步,仔細地回覆著鄉親們的詢問,感受著人們的眼神。畢竟,那個年代,家裡買上頭牛已是足夠可以炫耀一下的大事了。
小黑牛的進家也給全家帶來了欣喜,真不亞於家裡娶了一個新媳婦,全家上下一時全都洋溢在了歡樂之中。
小黑牛伴隨著我們家人的腳步一天天長大,在父親天長日久的訓練中學了一身的本事,耕耩犁耙樣樣精通。不但把我從勞作中替了下來,也大大提高了我家的勞動效率,為我家過上好日子立下了汗馬功勞……
儘管,我已離家多年,但那頭小黑牛的樣子依然清晰可辨。故鄉那片熱土上,耕牛勞作的身影時時浮現於腦海。每次回家的路上,多期望再能再見到田野里老牛耕作的身影,聽一聲耕牛的哞叫聲,還有那腳踏實地一步一步樸實的腳步聲呀!那一份牛耕時代的田園風光,只能去記憶裡尋找了……
過去,曾經有過形容農家幸福生活的一句話叫做,“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這既是莊戶人家對幸福生活的一種追求,也是對莊戶人家溫飽心態最真實最直接的的一種描述。在這幸福生活中,除了土地,家庭,子女和住房,再就是耕牛了,可見牛在莊戶人心目中的位置是何等的重要。
在過去年代,還流行過一句話,叫做“甘做革命的老黃牛”。這革命的“老黃牛”自然是指的“老黃牛”精神。因為老黃牛,在人們的心目中,總是那樣地勤勤懇懇、埋頭苦幹、忠於職守、任勞任怨。新中國建設時期,正需要這種“老黃牛”精神,而這種“老黃牛”精神,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涵之一。
可到了當今,“牛”的概念卻受到了顛覆。近年來,老黃牛在農業生產勞動中已逐漸的失去了作用,在勞動的場景中已逐漸淡化了牛的身影,那“老黃牛”精神也隨之成為了過去。現在一提到牛,人們立馬就會想到滿大街掛著招牌的什麼“肥牛”。在人們的眼裡,一提到牛,無疑就是一盤口中肉,桌上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