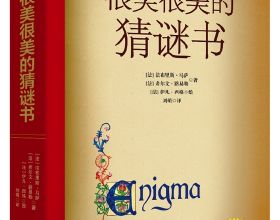舊日太平湖畔,“青睞”尋訪團與嘉賓傅光明合影 50年代,老舍在自家的魚缸旁 衚衕裡的孩子也來聽講 傅光明給“青睞”會員講解
眾所周知,北京城留存有數不勝數、積澱悠遠的文化遺蹟。為幫助居京或來京的朋友更切實、更深入、更系統地瞭解這座“文化中心”的深厚內涵,本報推出“北青版”京城文化路線。我們將以實地尋訪的方式,帶領讀者用腳步丈量這座古老又嶄新的城市,去閱讀、品味、感受並觸控它的肌理。我們期待,這樣一條線一條線地交織起來,將呈現出一幅既有溫度又有時代感的京城文化地圖。
一個作家的誕生與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絡,老舍先生自然也是如此。今年是老舍去世55週年,8月10日,我們邀請首都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傅光明教授,和“青睞”會員一起,在京城中尋蹤老舍舊跡,以此紀念、緬懷這位以“文牛”和“寫家”自喻的“人民藝術家”。
豐富衚衕19號
老舍紀念館,老舍迷熟悉的“丹柿小院”
老舍故居在疫情期間限流,參觀需要預約。院內人少,兩棵柿樹靜靜佇立,安靜的氛圍使大家說話的聲音都為之減低。
柿樹下的說明牌介紹詳細:1953年春天,老舍夫婦親自種下兩棵柿樹。每逢深秋時節,柿樹金紅,別有一番畫意。為此,胡絜青將小院定名為“丹柿小院”。這是老舍迷們喜愛和熟悉的小院。
老舍在此住了16年,很多人都知道他喜歡在院子裡種花種草種樹。他最喜歡菊花,住在這兒的時候,每年秋天都要搞菊展,把自己養的菊花擺在院子裡,請朋友來欣賞。這或許與他的母親關係密切。他的母親也是個熱愛生活、喜愛花草的人,老舍曾說:“將來我有了自己的小院子,我會在小院裡種滿花草樹。”所以,當老舍在北京擁有這樣一個家的時候,他實現了這個願望。
在傅光明的理解中,老舍的性格柔中帶剛,表面幽默,易於交友,實則內在有一條堅強硬實的底線。“他最後在那樣一種情況下選擇投湖自盡,與他外圓內方、剛硬堅毅的性格底線密切相關。”
老舍在《我的母親》中,曾寫下飽含至情、催人淚下的文字:“生命是母親給我的。我之能長大成人,是母親的血汗灌養的。我之能成為一個不十分壞的人,是母親感化的。我的性格、習慣是母親傳給我的。”
昔日居室改裝的展廳中,老舍先生的生平記述得清晰有序。“青睞”會員鬆散地圍繞在傅光明周圍,聆聽這位老舍研究者的講述。
老舍之有一番成就有其幸運之處。雖然他出身平民家庭,社會層次不高,也沒有高學歷,但他在1924年得到教會推薦遠赴英國倫敦,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講師。他作為小說家的生涯,即從倫敦開始,倫敦催生出中國現代一位大作家。
老舍在倫敦的住處,2017年傅光明專門去拜謁過。房子的外牆上掛著“英國遺產文化委員會”專門授予的藍牌子,那是曾在英國居住過,在藝術、文化、歷史、科學等領域有過傑出貢獻的英國人或外國人所能獲得的極高榮譽。傅光明解說:“老舍是第一個掛上藍牌子的中國作家,是第二個中國人。第一位是孫中山。老舍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就誕生在這間房子裡。”
一大面展板專門介紹抗戰時期的老舍。抗戰中老舍拋下小家,“妻子兒女全不顧,赴湯蹈火為抗戰”,在大後方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擊協會”總務部主任,主持“文協”日常工作,付出巨大,其中不乏人們所無法理解的艱辛和酸苦。為宣傳抗戰,他在這段時間寫過不少話劇,但並不擅長,他的本領仍在說故事。抗戰結束後,他和另一位文壇驕子曹禺接受美國國務院邀請,應邀訪美,訪期一年。
一年期滿曹禺回國,老舍留在美國。這段時間他和美國朋友合作,將自己的作品譯成英文,同時開始寫作《四世同堂》第三部。三年半後,新中國成立,應周總理邀請,那年12月9日,老舍從香港坐船在天津碼頭上岸,回到祖國。回國後老舍暫住北京飯店,家人還都在重慶北碚。1950年初,他買下豐富衚衕的這個小院。
在丹柿小院,老舍的勤苦有目共睹,他寫下大量謳歌新中國、讚美社會主義建設的作品,題材異常廣泛,最著名的莫過於《龍鬚溝》和《茶館》。傅光明感嘆:“《龍鬚溝》初稿老舍只花了大半天實地採訪便寫了出來,而且寫得非常快,由此可見他當時的政治熱情之高。”經典話劇《茶館》也誕生在這裡,這部戲北京人大都耳熟能詳,很多老舍迷甚至能大段背出其中京味兒十足的對白。
老舍這位“京味兒”作家,筆下流出過多少北京的風物和人情。其實“京味”兩個字遠不足以涵蓋老舍。但有一個地方很有意思,傅光明認為非常值得研究:“老舍的小說發生地幾乎都在北平,但寫作地都在北平之外,倫敦、濟南、青島、重慶北碚,主要在這四個地方。可見,老舍雖然身不在北平,但北平始終在他心底。他在散文名篇《想北平》裡說:‘我的血液是和北平黏合在一起的。’所以,從老舍的創作軌跡可以看出,故鄉始終存於他的靈魂、他的心血,同時也成為他靈魂和生命的一部分。”
傅光明還告訴大家,學術界對老舍有一種共識的評價,即老舍的創作可以1949年為分界線,簡單分作前期和後期。有一種觀點認為,老舍後期創作也有一個高峰,這是老舍非常幸運、並與眾不同的地方。“因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很多大作家,在後期基本上沒有與其前期藝術水準相匹配的作品,老舍似乎是個例外,當然,這主要體現在《茶館》上。”
丹柿小院每到金秋時節,有紅色的大棗和金色的柿子,果實飽滿豐碩,這彷彿和老舍的創作息息相關。傅光明覺得,自己研究老舍許多年,作為一個北京人,某種時候竟常有一種失語的感覺。“可能因為太愛老舍了,或者是對他比較熟悉,有時反而突然間覺得,似乎並不太能走近他,不太能瞭解他。我想這也說明了一個作家的豐富性。老舍的豐富有很多層面,並非輕易能解透。”
“老舍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難得的藝術天才,他是一個多面手,現代作家中似乎少有能與之比肩者。他幾乎嘗試了所有的文學體裁,但他卻以‘文牛’和‘寫家’自喻,他不說自己是作家,而是在文學土壤上勤苦耕作的牛。”這也正是為什麼閱讀老舍,不僅是現在進行時,對他的理解和研究更是將來時的重要原因。
老舍能給人一種勵志感。他特別喜歡“勤苦”這兩個字。在新中國成立後的16年時間裡,他作品豐厚,為了配合宣傳,有些作品一改再改,全是手寫。從這點上來說,老舍在丹柿小院的那間小屋裡,真的是一名異常勤苦的園丁。
護國寺小楊家衚衕8號
老舍先生名篇《四世同堂》的故事發生地
第二個打卡地,我們來到小楊家衚衕8號,即小羊圈衚衕5號。這裡是老舍先生的出生地,同時也是老舍最著名、篇幅最長、有抗戰文學扛鼎之作稱謂的小說《四世同堂》的故事發生地。
讓我們回憶一下,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對此地的描述:“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衚衕那樣直直的,略微有一兩個彎,而且頗像一個葫蘆。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蘆的嘴和脖子,很細很長,而且很髒。葫蘆的嘴兒那麼窄小,人們若不留心細找或向郵差打聽,便很容易忽略過去。進了葫蘆脖子,看見了牆根堆著的垃圾,你才敢放膽往裡面走。”
現如今的小楊家衚衕仍葆有著細而窄的葫蘆嘴,祁老太爺口中闊大且長有一棵大槐樹的葫蘆肚上,加蓋了一座二層小樓。衚衕改造後,這裡變化不小,傅光明第一次到這裡尋訪是在1993年,記憶中的破舊建築中還留存著老北京胡同的感覺。
老舍1936年在濟南寫下散文名篇《想北平》。他想念北平的點點滴滴:“好處不在處處裝置得完全,而在它處處有空兒,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氣;不在有好些美麗的建築,而在建築的四周都有空閒的地方,使它們成為美景。每一個城樓,每一個牌樓,都可以從老遠就看見。況且在街上還可以看見北山與西山呢!”在小羊圈的葫蘆肚兒,“青睞”團員們突然發現,閱讀老舍原來還可以懷念想念中的老北京啊!
這時,跑來兩個近旁院落的孩子,七八歲的陽光模樣。他們剛剛在開心地打著羽毛球,現在一頭一臉的汗。見我們一隊人馬出現在自己的領地,好奇地湊過來聽講。傅光明又讀起老舍的《我的母親》,讓大家感受大作家文句的簡短和有力,老舍文字的感人處每每在誦讀中更能夠體現出來。傅光明說自己特別愛讀老舍,很大原因在於其文字的內在張力。
長篇小說《四世同堂》第一章,開篇第一句:“祁老太爺什麼也不怕,只怕慶不了八十大壽。”傅光明請大家體會大作家的起筆:“我們常常說萬事開頭難,長篇小說也一樣。《四世同堂》是一部鴻篇鉅製,100萬字,頭開得如此隨意,老舍當初是怎麼構思的?”
大家議論紛紛之時,傅光明接著說:“實際上,老舍對於小說的整體佈局,起筆時應已有了比較成熟的醞釀。要把祁老太爺寫成一個什麼樣的人?把祁家寫成一個什麼樣的家族?我們國民的性格有多少層面附著在祁老太爺這樣的中國人身上?他都有了打算。老舍的深刻在於,他從來不做明面上的批判,而是在看似日常瑣碎、簡單隨意的描寫中,自然而然形成一種犀利的剖析和批判。”
看過《四世同堂》85版電視劇的朋友可能還記得,邵華扮演的祁老太爺在衚衕裡葫蘆肚子處說的那番話:“不礙事,咱們小羊圈有一個葫蘆嘴,嚴實。”他平生的經驗告訴他,不出三個月,亂子就會過去。他囑咐家人囤足三個月的糧食和鹹菜,自家小院門關起,大缸頂住,就“不礙事”。單這一段,傅光明做起了人物分析:“祁老太爺覺得國跟我沒有關係,抗戰跟我也沒有關係,我只要關起門來過自家的小日子。在這樣的描寫中,那種深入骨髓的國民性批判,是不是自然呈現了出來?”當然,他強調說,文學中這樣的描述、批判常需要我們去領會。
老舍的《四世同堂》故事精彩深刻,而實際上,他所寫的事並非親歷,而是來自夫人胡絜青的講述。那時老舍在重慶北碚,胡絜青帶著孩子千里迢迢從北平趕來。家人團聚後,胡絜青經常跟他講起日治下的北平。這些講述無疑調動起老舍的創作熱情,提供了豐富的寫作素材。
傅光明說:“這裡我們不妨替老舍設想一下,他構思這樣一部長篇小說,首先會想讓故事發生在什麼地方?發生在他最熟悉的地方是不是最合常情?我們知道,北京城西北角這一塊兒,就是這裡及附近一片區域,正是老舍青少年時期成長的地方,是他父親和母親的旗籍屬地。他的父母是滿洲正紅、正黃旗人。這是他最熟悉的地方,讓故事發生在了這裡,再自然不過。”
《四世同堂》是一部篇幅浩大的小說,在鮮明的抗戰主題之下,描寫了方方面面的人物、人情、人性,從很多描寫的人物身上都能體會到老舍文學和藝術的深度及廣度,儘管有些人物出場次數很少。“老舍是一位幽默作家,我們常常將他定義為語言大師、幽默大師,但對於他怎樣把自己深刻的批判融在作品裡,很多讀者體會得不深,所以今天這樣一個老舍之旅,可以說也是一種有意的引領,因為這種批判對於今天的我們,並沒過時。”傅光明道出這一次尋訪的深意。
傅光明建議:
“成立一個老舍讀書會吧”
老舍確實是幽默的,他的幽默體現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也體現在他的作品裡。在《我的理想家庭》那篇散文中,他曾自我調侃說:“我剛想出一個像樣的句子來,小濟就來搗亂,耽誤了我的構思和寫作,所以我到現在也沒有成為莎士比亞。”傅光明也是一位莎士比亞譯者,對於老舍談莎翁,他也有發言權:“老舍沒寫過像樣的文章談莎士比亞,但他談過莎士比亞寫了很多戲,只是寫得太快,原本他可以寫得更好。”我想,老舍對莎士比亞的這一評價也反映著他自己的創作觀吧。
前往下一處打卡地的路途上,傅光明講起老舍軼事。談到老舍曾經很得意地說過,他的《駱駝祥子》是可以朗誦的。語言常常跟著聲音走,在閱讀中能夠得到不一樣的體會。對此,傅光明深以為然,他說:“閱讀老舍不需要很高的學歷,他的文字非常口語化,頂頂俗白。單純從閱讀作品來說,讀魯迅,中學水準大概讀不太懂,說不準還會逆反,跟魯迅產生距離。但老舍不會,老舍那些最好的作品,隨時隨地抽出一章,隨手就可以讀,對於語境的前後關聯不用太過考慮。”傅光明自己愛讀老舍,那是他的一個享受。
接著,他講了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日本有個老舍讀書會,成立於1955年。讀書會每週日上午活動,內容就是讀老舍作品。傅光明與讀書會的創始者們大都是忘年交。2004年,他應日本老舍讀書會邀請,專門去講老舍。讀書會邀請嘉賓有兩個前提條件:一是主講人不會說日語,以保證隨時隨地用中國話與會員們交流。說什麼樣的中國話?那就是第二個條件,必須是北京人!說北京話!傅光明能從讀書會成員那裡感受到,他們特別享受這樣一種傾聽。
“由此我想,‘青睞’也可以成立一個老舍讀書會。我們來讀老舍,甚至可以表演,比如《茶館》;還可以做老舍文學尋蹤,我們都是北京人嘛!《駱駝祥子》裡寫的很多地名都是真實的,並非文學想象,我們大可拿著一本《駱駝祥子》,去尋覓祥子在北京的行蹤。”這是不是一個誘人的提議?反正在場的“青睞”會員們都躍躍欲試了。
有網友藉機提問:如何提高孩子的寫作水平?
這方面傅光明可謂經驗豐富,妻子和他的“引誘”式閱讀,使他們的女兒早早深諳文學之道。而他也記得老舍先生曾經反覆講到:文學寫作要遵循文學內在的規律。
這個規律是什麼?說起來有點玄奧,但有過創作體驗的人都懂得,規律不是簡單一兩句話能夠說清楚。寫作之路異常艱辛,它需要勤奮,需要廣泛閱讀,也需要一定的才華。傅光明感慨:“我們總說老舍是一位天才作家,但他也不是坐在那兒就文思泉湧,他的每部作品都有構思的艱難。我們有沒有想過,老舍以如此的天才,竟付出如此的勤苦,這才是他的成功之法?”
新街口豁口太平湖
老舍的生命在這兒畫上句點,走向永生
小楊家衚衕距離老舍生命結束的地方——太平湖,只有大約兩站路。“太平湖”,緊挨著新街口外大街西側的護城河。這是我們的第三處打卡地。
說是太平湖,湖其實早已不存在。大概在上世紀70年代修建地鐵時,這個不大的湖被填平,上面修建起廠房,如今成了積水潭地鐵車輛修理廠。
老舍投湖的地點在西邊的後湖,疫情期間,進入要掃碼測溫。傅光明沒有帶我們深入去找尋舊地,據說那裡曾經立有一個說明牌子,大家倒也不甚關心,只專心地聽著傅教授分析,老舍為什麼選擇此地結束自己的生命。
實際上,這個題目老舍之子舒乙先生曾做過研究,他曾經寫過:“太平湖悲劇發生十二年後,有一次,我偶然開啟一張解放前的北京老地圖,竟一下子找到了父親去太平湖的答案。太平湖正好位於北京舊城牆的西北角,和城內的西直門大街西北角的觀音庵很近很近,兩者幾乎是隔著一道城牆、一條護城河而遙遙相對。從地圖上看,兩者簡直就是近在咫尺。觀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她在這裡住了近十年,房子是父親為她買的,共有十間大北房。她老人家是1942年夏天在這裡去世的。我恍然大悟:父親去找自己可愛的老母了。”
傅光明的分析中,當然還有其他原因,很重要的一點,這裡是老舍作品中很多人物故事悲歡離合的發生地。
從老舍故居走到太平湖,距離不近,而他當時已經是67歲的老人。他家附近也有水,什剎海、後海、積水潭,都比太平湖距離要近。那一天,這位67歲的老人在湖邊坐了多久,沒有人知曉。而傅光明肯定,他一定坐了很久,想了很多,想來想去,最終沒給自己找到一個眷戀生命的理由。
在瞭解了老舍這番經歷之後,傅光明特別提議大家再來領會一下《茶館》結尾王掌櫃的自殺,是否能跟老舍最後的自盡形成藝術與真實的對應和吻合?都是那麼的悲、慘、痛!傅光明說:“或許老舍先生坐在這兒,腦海中有了一個藝術時空,扔著想象的紙錢,憑弔著自己的生命。”
同行的“青睞”會員們靜靜地聽著,彷彿跟隨著傅教授的思路,更多更深地理解了老舍,走近了老舍。傅光明說:“從地理空間上來說,老舍的生命終點距離起點很近,但他生命和藝術的豐富性遠遠超出。老舍自身已成為一個巨大的時空,是一個博大的藝術世界。對於老舍,到今天,還是讀不完的,尤其作為北京人,我覺得,我們要無限地深愛老舍,愛他寫過的北京。”文/本報記者 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