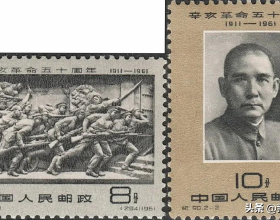小說《金枝》講述了父親周啟明在時代洪流的裹挾下,半推半就地成立了兩個家庭。半個世紀以來,城鄉兩個家庭在纏鬥不休中互相傷害、折磨。隨著父親的逝世,家族第三代的發展壯大,兩個家庭的敵對關係在歲月淘洗下變得溫情起來。過去的沉重陰影在歷史的回眸中,最終被定格為年輕母親的粲然一笑。
作者邵麗將時代變遷、女性成長、子女教育、城鄉對峙等多重主題雜糅進這部體量不大的小說裡,這是一項頗具勇氣的挑戰性寫作。令人欣喜的是,她以一貫對細節的精準捕捉和直抒胸臆的表達,在有限的篇幅內為讀者呈現了一幅生氣淋漓、緊貼現實的生活畫像。在傳統與現代、城與鄉、審父與自審、生活與藝術的多重視域的交織中,邵麗藉縱橫交錯的目光梳理了這段盤根錯節的家族秘史,於體量精巧的文字內創造出了無限豐富的閱讀可能。
15歲的周啟明在祖母的哄騙包辦下娶了素未謀面的穗子,半個月後,他離家南下追隨爺爺鬧革命。周啟明棄家逃婚、按程式離婚、與進步同志朱珠再婚等系列舉動,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可他對現代婚姻的合理追求也讓祖母和穗子被動陷入了無比難堪的尷尬境地。祖母守了半輩子的活寡,現在輪到穗子,苦命迴圈如斯。不久,祖母因愧疚心衰而死,活力漂亮的穗子變成了蠻橫潑辣的瘋婦。拘囿於時代,女性對傳統倫理的無法超脫讓人不忍責備,然而男性對現代自由的追求和實踐,也同樣無可厚非。人們夾雜於新舊之間的矛盾處境和糾結心態,讓這出悲劇顯現出了幾分歷史的必然。
在開篇的父親葬禮上,姐姐周栓妮出格失禮的行為暴露了鄉野文明粗魯野蠻的一面,而妹妹周語同哀傷有度的表現則凸顯了城市文明虛偽冷漠的一維,雙方的明爭暗鬥讓這場葬禮顯得莫名弔詭。雙方衝突的高潮爆發在葬禮後的飯桌上,面對周語同刻薄惡毒的言語侮辱,周栓妮以無所畏懼的頑韌擊潰了對方虛張聲勢的強大。在這股鉚足力氣向上攀登的生命韌勁的薰染下,周栓妮的子女們在學業、事業上集體超越了城市一支。這結果既是對費盡心力培養後代的周語同的尖酸諷刺,也是對城鄉二元對立的悄然解構。當週河開等農家子弟進入城市,他們身上那種超乎常人的頑韌堅強、吃苦耐勞的鄉土品質為其融入、紮根城市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他們的成功展現了城鄉融合所蘊含的無限可能和強大力量。
《金枝》分為兩部分,上部以周語同審父為主。周啟明處於情與義的糾結、個人追求與家族責任的衝突、私人身份與社會角色間的撕扯中沒有選擇的餘地,於是他選擇了躲。父親的“躲”使他成為了家庭中一個高懸虛置的“符號”,一個在場而缺席的存在。小說的下部轉向了周語同的自審。由於備嘗被父母忽略、疏離之苦,周語同情不自禁地以大家長自居,對家族第三代施以極端的干預和掌控。這實際上只是對父輩的矯枉過正而已。第三代在她恨鐵不成鋼的凝視下,依然我行我素地生活。當週語同援引栓妮子女的出息來自我安慰時,她就如同匆忙收束一場顧影自憐的獨角戲那般可憐又可笑。在審父與自審的過程中,作家丟擲了我們應該怎樣做父母這一現實問題。
據精神分析學說,藝術創作和夢一樣,都是被壓抑慾望的流露,藝術家可透過一種提供美和樂趣的純粹形式展現他的慾望。周語同隱約有邵麗本人的感情投射,由此作家得以開啟自我傾訴的閘門,釋放滯留於心中的創傷和苦澀。主觀的敘事視角使文字獲得坦誠向內、省思自我的意味與深度。而雁來小說《穗子》的嵌入堪稱神來之筆。該文從另一個視角再現了穗子家的故事,它的出現是對佔據話語霸權的周語同視角的挑戰和矯正。這組對立視角的並置,驟然打開了理解周家歷史的多維空間。
詩人奧登曾說:“一本書具有文學價值的標誌之一是,它能夠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被閱讀。”我們可以從《金枝》讀出人們困於傳統負載和現代追求間的矛盾處境、尷尬情態;看到城鄉在現代化程序中的差異對立及其融合的潛能;體味到女性在審父和自審過程中所實現的代際超越和自我更新;讀出作家在面向自我與藝術昇華間的兼顧和平衡。
作為一個複雜文字,它被閱讀和開啟的可能,遠未窮盡。
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