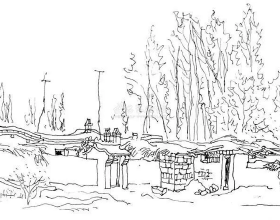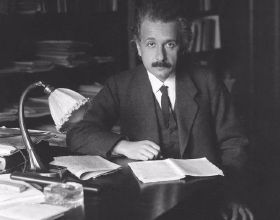作者:劉躍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漢武帝劉徹元光元年(前134)十一月,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郡國舉孝廉各一人[1]。五月,詔賢良對策,董仲舒應詔對策,提出了建立太學的構想,將儒家學說定為統治天下的思想。《漢書·董仲舒傳》載其《舉賢良對策》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2]
《漢書》顏師古注:“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此言諸侯皆系統天子,不得自專也。”[3]“歸於一”的“一統”觀念,並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孔子、孟子、荀子,甚至墨子、韓非子、李斯、賈誼等都從不同側面有所論及。《春秋·隱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下,《公羊傳》解釋說:“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4]所謂“大”字,有尊大、尊美之意,換言之,也可以說以一統為大[5]。“統”字,東漢何休釋為“始也,總系之辭”。他說:“夫王者,始受命改制,佈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系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徐彥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6]何休、徐彥等人的看法,均與董仲舒的思想密切關係。
董仲舒的意義,賦予這一傳統命題更豐富的內涵。他治《公羊》學,認為“王正月”不僅是承祖命而為,更是尊天意而為,從而提出了“天人感應”之說,將王者受命改制繫於“順天命”上,為君主治世預設了不可質疑的天命依據和權力話語。這一主張,順應時勢,自然得到漢武帝的賞識。
一、《春秋》“大一統”觀的思想淵源
《春秋》“大一統”觀的提出,有著悠久深厚的思想淵源。
《莊子·天下》篇將先秦文化分為六派:一是墨翟、禽滑釐,二是宋鈃、尹文,三是彭蒙、田駢、慎到,四是關尹、老聃,五是莊周,六是惠施、桓團、公孫龍。《荀子·非十二子》亦分為六派:一是它囂、魏牟,二是陳仲、史鰌,三是墨翟、宋鈃,四是慎到、田駢,五是惠施、鄧析,六是子思、孟軻。漢初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亦分六家: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到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分為九流十家。如果把各家之說歸類,發現其學派之不同,多與地域有直接關係。名、法兩家可以歸為三晉文化,陰陽、道德兩家可以歸為荊楚文化,儒、墨兩家可以歸為齊魯文化。《春秋》“大一統”觀與這三大文化系統密切相關。
三晉文化通常指西周到春秋時代晉國文化和戰國時代魏、韓、趙文化。戰國七雄並立,屬於晉文化的就佔其中之三。
從整體來看,“晉”或“三晉”(韓、趙、魏)是“中原古文化”與“北方古文化”兩大古文化區系的重要紐帶[7]。《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和《儒林列傳》載,魏國開國君主魏文侯,拜子夏為師[8],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禽滑釐等儒教名流、軍事幹將,先後彙集魏地,對於魏國的振興起到決定性作用。魏文侯雖欣賞齊魯文化,但也並非亦步亦趨。譬如齊魯文化倡導禮治,而魏文侯卻更醉心於法制。他堅持起用李悝為相,變法革新,促使儒、法思想的融合和轉化。李悝原本是子夏的弟子,卻是法家的始祖[9]。在三晉的土地上,還產生了申不害、韓非等重要思想家。兩人相距雖有一個世紀左右,但均強調法制,其主導思想一脈相承。《申子》,《史記》記載有兩篇,《漢書·藝文志》著錄六篇,均已亡佚。較完整的言論見《群書治要》卷三六所引《大體》一篇,講究帝王南面之術。《韓非子》五十五篇則是一套完整系統的法家理論體系。從本質上說,三晉文化多為秦代所繼承。《史記·張儀列傳》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10]
相傳秦人祖先乃帝顓頊的苗裔,女修吞食玄鳥蛋,生大業,從此開始了秦人的歷史。《史記·秦本紀》記載秦人的早期歷史,充滿神秘色彩,或曰起於東部萊蕪,或曰起於西陲禮縣。長期以來,秦國不與中國諸侯會盟,保持著戎狄遊牧民族的傳統習慣。秦人啟用商鞅變法以來,“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11]。從此,法家思想成為了秦國的統治思想。法家思想,崇尚武功,講求實用,追求一統,這些思想一直被秦人奉為主導思想。這種思想的重要特徵就是功利性,崇尚戰功,寡義趨利。由此功利性,又演變成一種強烈的排他性。其結果,必然又會制約秦人的更大發展。孔子早就看到秦人的這種不同尋常的特性,《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闢,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12]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荊楚文化。
楚國自春秋以來對外採取擴張政策,北上中原,稱霸爭雄,不可一世。戰國後期,楚國遭到滅頂之災。就在秦朝滅絕文化的時候,素以文化自負的楚人揚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13]對於這八個字的具體理解目前尚有很多分歧,一說是指三戶人家,一說是地名,也許這並不很重要,關鍵是“亡秦必楚”四字,沒有異義。陳勝、吳廣以及劉邦、項羽、蕭何、曹參等均是楚人。他們所立傀儡君主也是楚王后代,說明楚人對於自己國家被秦人所滅,心有不甘,伺機而起也在所必然。陳勝、吳廣、項羽、劉邦等推翻秦人統治的重要武裝力量均來自楚地。隨著楚人入主三輔地區,楚文化自然大舉西移,進入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構成了當時引人矚目的文化現象。劉邦被項羽封為漢王后,楚人從者數萬人。劉邦立國後,楚國的昭、屈、景等大族的西遷,更為三輔地區帶來了強勁的楚風。
荊楚文化以老子為軸心。1973年在湖南馬王堆漢墓出土了老子的《道德經》。1996年在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戰國中期的竹簡,也發現了八百多片文字簡,其中也有老子的《道德經》。這說明,早在戰國中期,《老子》一書已經定形。根據《戰國策·秦策上》、陸賈《新語·思務》及題名劉向的《列仙傳》等書記載,在戰國時期的齊地,道家的傳說非常盛行,像王喬、赤松子等昇仙故事,《淮南子》將其放在《齊俗訓》篇中[14]。《史記·留侯世家》記載,張良系韓人之後,自幼欲學赤松子,嚮往仙人境界,故後來有出家之舉。漢家王室成員如劉安、劉向等也逐漸接受了這種主張。劉向所獻所撰,多為這類“道術”之書。這說明荊楚文化的影響是非常廣泛的。
荊楚文化對於文學創作的重要影響突出表現在楚歌的盛行。這類作品,除《楚辭》之外,還有《孟子·離婁》裡面記載的《孺子歌》(又叫《滄浪歌》),《說苑·善說》記載的《越人歌》,《莊子·人間世》《史記·孔子世家》記載的《接輿歌》等。公元前350年前後,屈原來到人世,開創了荊楚文學的新紀元。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荊楚文化一時式微。隨著秦末楚人陳勝、吳廣、劉邦、項羽的崛起,楚歌再度盛行。其後,楚歌形式多有分化,漢代詩歌、辭賦乃至經世致用的文章,依然沉積著楚歌的因素。
統治階級的思想,往往也就是統治思想。西漢初年,隨著楚人西移,道家思想,尤其是黃老思想在帝國核心地區流行開來。《老子》《莊子》為道家思想淵藪。《莊子》五十二篇見於《漢書·藝文志》著錄,賈誼已經多次徵引[15]。但在西漢時期,這部書的影響還不足與《老子》相比。黃帝思想在西漢初年非常流行。《漢書·藝文志》道家類著錄的《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等著作,大約就是這樣書籍。
據《史記·曹相國世家》記載,漢高祖劉邦六年(前201),立長子劉肥為齊王,以曹參為齊相國。當時天下初定,齊王接受膠西蓋公的建言,推行黃老之學。孝惠二年繼蕭何之後,曹參入為丞相,又將黃老之學推廣到全國。黃老之學的核心,就是所謂無為貴靜之說,亦即《老子》所謂“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16]俗語所說“蕭規曹隨”,殆即此意。
從西漢前期政治鬥爭看,所謂黃老之術,究其實質,是一種戰略戰術,不僅僅是為安息天下民眾的一種手段而已。呂后所以採取這種無為之術,主要是出於政治目的。孝惠、高後時,公卿皆武力功臣,推廣黃老無為之術,可以有效地抑制他們的政治野心。由此看來,黃老之術不僅僅是一種修身養性之術,而是一種權術[17]。黃老思想一直影響到武帝即位之初年。司馬談著《論六家要指》,表面看來對六家之說各有抑揚,但明顯傾向於道家。
儒家文化以孔孟為代表。除《論語》《孟子》兩書外,影響最大的是相傳孔子所作的《春秋》。《春秋》後來又派生出《公羊傳》《榖梁傳》《左氏傳》等三傳,形成西漢頗為興盛的“魯學”和“齊學”。魯學主要興盛於西漢前期,《詩》有魯《詩》,《論語》有《魯論語》等,強調禮治,重視王道,在學術史、政治史上,均有重要影響。與魯學相比較,齊學可以說異軍突起。一方面,稷下學宮為儒學的儲存與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另外一個方面,齊地瀕海,齊人善於想象,敢於創新[18]。在戰國後期,齊人敏銳地意識到天下終將走向統一的趨勢,結合陰陽五行學說、黃老學說,乃至法家主張等,提出了一種包容百家的大一統理論體系,為西漢前期的統治者,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武器。
楚漢相爭之際,劉邦引兵圍魯,魯中諸儒講學誦習之聲不斷,禮樂絃歌之音不絕,於是劉邦對儒生心存好感。公元前204年,酈食其向劉邦建議,欲立六國後人以樹黨,劉邦也接受了這個建議,並派人刻印。而張良預設八難,從形、勢、情三個方面分析了不可立六國之後的道理,頗有振聾發聵之勢。史載,劉邦正在吃飯,聽到張良的鞭辟入裡的分析,顧不上吃飯,大罵豎儒敗事,從此不再信任儒生。
問題是,沒有規矩,就不成方圓。劉邦消滅項羽之後,主張簡易。結果群臣飲酒爭功,乃至拔劍擊柱。此時距酈食其事件不過兩年時間。劉邦的困惑,最終由來自魯國的叔孫通給予圓滿的解決。叔孫通對劉邦說,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朝廷中有學問的人,因秦舊制,制禮作樂,從此群臣不敢逾越禮制。劉邦感嘆說,“今日知為皇帝之貴”[19]。由此可見,新朝對於儒學的接受,經歷了一段相對複雜的變化過程。董仲舒思想的成熟與被重視,正是在此一變化過程中得以發生。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作這樣的概括:從子夏弟子李悝《法經》開始算起,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止,中國思想文化界在這一千多年間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百家爭鳴到法家霸道思想的勝利,《韓非子》集法家之大成的學說,成為秦王嬴政統一六國的指導思想,促進了中國大一統局面的形成。但是物極必反,當法家思想走向極端之際,用刑太極,最終迅速導致秦國的滅亡。
第二階段是西漢初年荊楚文化的抬頭,以黃老思想為中心,講究清靜無為。秦代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給漢初的思想家留下了沉重的話題。如何避免重蹈這段歷史的覆轍,不同思想家自有不同的答案。秦漢之際的楚人陸賈,鑑於當時百廢待興的局面,提出在政治上無為而治,在文化上兼收幷蓄的主張。在兵荒馬亂的年代,這些想法,自然為劉邦所嘲弄,但是他很快就意識到了這些見解的深刻意義,於是要求陸賈著書,闡明秦何以亡、漢何以興的歷史根源。故陸賈《新語》專闢《無為》一篇,以為“道莫大於無為”,“故無為者乃無不為也”[20]。這是對三晉文化的一種否定,也是對荊楚文化的張揚。
第三階段是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界百川歸一。如前所述,戰國時代,人們苦於諸侯割據混戰,漸漸地產生了統一的要求。這種思想在產生於春秋末的《左傳》中已有萌芽,而在戰國中期的《孟子》中逐步明確,到戰國後期更趨強烈。《公羊傳》中的“大一統”思想正反映了當時人們普遍的要求。
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漢初年所倡導的《春秋》“大一統”觀,雖以儒家思想為主幹,實際上融匯了諸子百家學說,其中道家和法家思想,更是佔據了重要的位置,形成了一個外儒內霸的思想體系。
二、《春秋》“大一統”觀的歷史內涵
《禮記·禮運》將遠古歷史的執行,分為“天下為公”與“天下為家”兩種形態。天下為公,是說天下乃天下人共有之天下,是謂大同。當歷史進入到私有制社會以後,以血緣為紐帶,天下為家,公天下變成了家天下,這是國家的雛形。
在《元光元年舉賢良對策》中,董仲舒說: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21]
董仲舒認為,孔子作《春秋》就是要總結由公到私、禮崩樂壞的歷史教訓。他說:“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22]《春秋繁露·俞序》也說:“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23]那麼,“後聖”是誰呢?《元光元年舉賢良對策》繼續寫到:“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24]董仲舒認為,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法先王,成“後聖”,這是董仲舒的最大願望。他從《公羊春秋》中推衍大義,精心構築起天、地、人三位一體的“三統”,又以子正、醜正、寅正為“三正”,以夏、商、週三代為正統,並努力將這種理論賦予實踐品格,為“後聖”服務。
董仲舒少治《公羊春秋》,景帝時為博士,下幃講誦,有三年不窺園之傳說,他的主要成果集中儲存在《春秋繁露》中。他說:
《詩》無達詁,《易》無達佔,《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27](《精華》)
《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28](《竹林》)
《春秋》無常辭,唯德是親。[29](《觀德》)
所謂無達辭,無通辭,無常辭,其義一也,即“從變而移”,“一以奉人”,即在符合時勢與天意的變化中闡釋君權的合法性,實現國家的大一統。這是董仲舒的初衷,也是他倡導《春秋》大義的根本所繫。
從大的方面說,這一主張至少有如下歷史內涵。
第一,從“大一統”到正統觀念。
《禮記·喪服四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也。”[30]《漢書·王吉傳》載王吉上疏:“《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31]此即公羊學“大一統”之義。董仲舒師承此說,注重法先王,更強調“以《春秋》當新王”[32],“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33]。為此,他積極融匯法家、道家、陰陽家及黃老思想,極大地拓寬了這個命題的內涵和外延。如《春秋繁露·立神元》就有道家思想成分。他說:“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失之豪釐,駟不及追。故為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寞無為,休形無見影,掩聲無出響。”[34]又如《身之養重於義》《觀德》《深察名號》等篇,強調義與利,禍與福,心與身,天與地之名號等觀念,大約也出自古道家。《保位權》:“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35]又近於陰陽五行及法家思想。
《公羊傳》強調法先王,更強調了“正”的重要性,用“正”來衡量事件。如《哀公十四年》載:
《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36]
這段話出於《公羊傳》最末處,“所見”“所聞”“所傳聞”都是以孔子為主體,指《春秋》十二公事有的為孔子親見,有的是孔子直接聽得,有的則是孔子聽到的傳聞。《春秋繁露》以此為基礎,強調“《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37]因為這三者來源不同,所以孔子作《春秋》用辭有異,目的在於“制義”,即撥亂世反諸正,以此等待後世的聖王。《賢良對策》釋“正”曰:“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38]這是《春秋》“正”之大“義”,涵義至廣,但核心只有一個,即《公羊傳》所強調的“尊君”,透過“制義”確定王權等級的絕對權威。《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明確說: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性非繼仁,通以己受之於天也。[39]
“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董仲舒透過對《春秋》的闡釋,將《春秋》大義推向極致,強化了“正統”觀念。所謂“正統”,就是要用“正”來“統”天下,由“統”來確保“正”,為王朝的上下授受有據、統治的合法性提供根據。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春秋繁露·深察名號》說:“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40]“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41]由此看來,正統的實質就是“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又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42]歐陽修說:“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43]梁啟超也講到:“統字之名詞何自起乎?殆濫觴於《春秋》。”[44]其實,《春秋》字面並無大義與正統的敘述,這些觀念的形成與董仲舒的闡釋有莫大關係。
“正統觀”成為中國文化中極為重要的觀念範疇,作為古代政權確立自身合法性的重要言說,是宗教、文化等意識形態與現實政治運作的紐結點。正統是政權存在合法的依據和基礎。王朝建立的“正”與“不正”,合法與不合法成為史家判別一朝一代歷史地位和社會價值的主要尺度。歷史上各個政權為了標榜自身為正統,無不自立標準,例如魏晉南北朝時代,南北割裂,南朝稱北朝為“索虜”,北朝稱南朝為“島夷”。北宋前期最重要的《春秋》學家孫復著《春秋尊王發微》,透過闡釋《春秋》的“尊王”大義來維護中央集權制,強化皇權,用世之意很明顯。南宋的正統論更偏向空間上的正統訴求,故強調“攘夷”,胡安國的《春秋傳》就是歷史見證。每到改朝換代之際,這種正統觀總會成為討論的焦點問題。
第二,從正統觀念到天人合一。
正統觀念確定之後,如何維護正統,便成為董仲舒思想的焦點。他認為,天、地、人是萬物之本,依據《春秋》就可以知天意,接地情,通人事。因此,《春秋》之道,至大至高;至大可以王天下,至高可以稱霸王。他特別強調王道、霸道並用的重要性,甚至斷獄、選官,也要借用《春秋》之義。《春秋繁露·精華》說:“《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45]誅首惡,志善者,維護政權的嚴肅性。在《俞序》中,董仲舒甚至認為,治理國家,沒有不學《春秋》的,如果不學《春秋》,則不能預見前後旁側之危。《元光元年舉賢良對策》也說: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46]
董氏將“天”視作萬物之祖,並把天的節律和呈現與聖人所為完全對應起來。為此他不惜加進大量災異祥瑞之類的內容,與君王德政進一步聯絡起來。比如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的傳說,董仲舒就認為是“受命之符”,是上天“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47]這是董仲舒利用對《春秋》的闡釋來建構漢家政治權威的重要法寶。
第三,從天人合一到君權神授。
《公羊傳》從“元年春王正月”闡釋出“大一統”,卻並未對“元”過多闡釋,僅認為就是每一個君主的第一年都稱為元年。從董仲舒開始,強調以“始”來解釋“元”:
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48](《元光元年舉賢良對策》)
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49](《春秋繁露·重政》)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50](《春秋繁露·二端》)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51](《春秋繁露·王道》)
他首先注重發揮公羊學所強調的“神—人”關係,構建出一套在宇宙秩序與人倫法則之間能相互對應的“天—人”結構關係。東漢何休在《公羊解詁》中進一步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義為“五始”。其中,“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時之始,文王乃周受命之始,正月為政教之始,公即位表示一國之始。這“五始”表示著天經地義的統治秩序。帝王登基,實乃天意。《春秋繁露·玉杯》:“《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52]漢代的思想家、政治家無不秉持這樣的理念,來為當時政治服務。《漢書·路溫舒傳》載路溫舒上疏宣帝說:“《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53]這已成為當時的共識。
第四,從君權神授到天下觀念。
董仲舒的思想不僅有為王朝立“正”溯“統”的宗旨,同時也希望借之規誡王權,對可能恣意妄為和無限氾濫的君權進行更形上層面的監督和控制。《元光元年舉賢良對策》說: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強勉而已矣。[54]
《廟殿火災對》《雨雹對》等,都用《春秋》來解說種種災異現象。《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55]這樣,作者把自己擺在了一個特殊的地位,即可以透過對《春秋》的解說,起到對君王勸善懲惡的作用。
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災異呢?他在《春秋繁露·王道》中提出,要順民心:“《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幷見。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56]他在《為人者天》中又說,五帝三王時代所以“不敢有君民之心”,就是不敢自謂君民,要對天有敬畏之心,“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57]
董仲舒倡導的《春秋》大義,不僅是君對臣民的“統”,還強調君對天、對民的敬畏。《春秋》大義對天、君、臣、民,以及中國—夷狄的雙向制約強調,影響了後世的大一統思想,以致成為一種“法”。《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講:“(孔子)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58]司馬遷對《春秋》“義法”的理解上承董仲舒的《舉賢良對策》,在漢代四百多年中具有代表性,後世闡發《春秋》大多不離這一基調。在武帝希望建立統一強大政權的時代,董仲舒既提供了“君權神授”的理論依據,還提供了監督君權的“正義”依據。
第五,從天下觀念到統一實踐。
孔子作《春秋》,時值禮崩樂壞之際。他要尊王攘夷、恢復正統。《公羊傳·僖公四年》用“中國不絕若線”[59]概括其大義,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文化認同,影響極為久遠。當然,在春秋末葉,這還只是一種理想。戰國時代,諸侯紛爭,是非混淆。《孟子·萬章》引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60],表達了重新恢復秩序的時代心聲。如何恢復這種禮樂文明呢?《管子》說:“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鬥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61]《荀子·非十二子》則提出效法舜禹:“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62]呂不韋、李斯提出了同樣的主張,呂不韋說:“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之也。一則治,兩則亂。”[63]又說:“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執一不二,就是要統一。李斯也立志“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64]公元前248年,呂不韋帶兵滅掉東周。又過了二十七年,秦王嬴政橫掃六國,建立了統一的秦王朝,將“大一統”的理念付諸實踐。
不無遺憾的是,“秦世不文”,馬上得天下,亦馬上失天下。這一沉痛的歷史教訓,讓西漢初年的思想家深刻地意識到,強化中央集權,建立禮樂制度,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上策。賈誼《新書》說:“臣為陛下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65]又說:“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車之所至,人跡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哉?”[66]當時內憂外患,無法實現這些理念。
漢帝國建國七十餘年後的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再一次提出這一主張,切合現實的需要,反映了時代的先聲。
三、《春秋》“大一統”觀的政治訴求
漢武帝推崇董仲舒的《春秋》學說,尊王攘夷,強調以王法正天下,試圖透過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手段,積極處理文化多元與政治一統的棘手問題。
先說尊王問題。
春秋時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製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銼以廣地,以強相脅,不能制屬,強奄弱,眾暴寡,富使貧,併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67] (《春秋繁露·王道》)因此,《春秋繁露·十指》明確指出,要強化中央集權,使尊君而卑臣,則“君臣之分明矣。”[68]當時的情形正好相反,是強枝弱幹。西漢初年,地方勢力強大,賈誼、晁錯本《春秋》之義,多次上書請求削藩,“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敢自殺不敢反,知必菹醢耳。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69](《陳政事疏》)。景帝末年,吳楚七國以“清君側”為名發生叛亂。景帝殺了晁錯,並未換來地方勢力的妥協。這個慘痛教訓,讓漢武帝銘刻在心。即位伊始,他就開始強化中央集權,消解地方王侯勢力,迅速改變長期以來困擾朝廷的尾大不掉的被動局面。
《春秋繁露·度制》說:“聖人之道,眾堤防之類也,謂之度制,謂之禮節,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70]度制,就是制度。董仲舒的建議,就是從制度層面入手,整合社會秩序,規範人倫尊卑,遏制地方勢力,使之歸於一統。漢武帝透過一系列的措施,強化制度建設,確保中央集權。在政治方面,武帝取消了地方自行任命官吏的特權,壓縮諸侯王國的疆域和權力,如淮南王所轄地區,一分為三,分而治之。在經濟方面,漢武帝啟用大商人桑弘羊,收回地方鑄錢的權力,實行鹽鐵政府專營的經濟政策。在思想方面,漢武帝希望藉助儒術的力量,迅速消解漢初以來盛行的戰國習氣、黃老之學。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崇尚黃老的竇太后去世,漢武帝親政改元,舉賢良對策,遂接受了董仲舒提出的獨尊儒術的主張,將儒家思想確立為統治思想。
再看攘夷問題。
在鞏固中央集權的同時,漢武帝希望透過軍事手段,儘早解決邊患問題。畢竟,軍事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攘夷是《春秋》大義之一,也是國家“大一統”的政治訴求。更何況,這裡還有君父之仇[71]。
《公羊傳》曰:“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72]這裡說的是春秋時期的情形,而戰國以來的形勢依然如故。《春秋繁露·精華》說:“《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73]從當時情形看,關中地區依然有南北夾擊之虞,必須有所應變。南是指大庾、騎田、都龐、萌渚、越城嶺等五嶺以南的廣大地區,大致包括今天廣東、廣西、海南等地,地方割據勢力仍在。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嶺南地區劃入中國版圖,始於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不久。他曾動用數十萬兵力,征戰數載,最後在始皇三十三年(前214)攻取嶺南,建立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首次將嶺南地區納入中華統一的版圖之中。
秦末漢初,趁中原戰亂,趙佗建立了南越國,實行郡縣制和分封制。漢初經陸賈遊說,稱藩於漢朝,在文化上與中原保持著頻繁的接觸。但是他們對於中原的威脅無時不在。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武帝分五路大軍滅南越國,將嶺南地區分為蒼梧、鬱林、合浦、交址、九真、南海、日南、儋耳、珠崖等九個郡,歸交州刺史部所監察。南越國從建立到滅亡,前後不過九十三年。秦末收復之戰及這次戰爭,前後有大批中原人士南遷,“與越雜處”,將中原先進文化帶到嶺南地區[74]。
至於北部,問題更為複雜。六國以來,這裡長期為匈奴所佔據,在獲取豐富給養的同時,又與西羌聯手,不斷地騷擾中原。秦始皇曾派蒙恬統帥三十萬大軍設防戍邊,還將原來秦、趙、燕北方邊境的長城連線起來,西起臨洮(今甘肅岷縣),東至遼東(今遼寧丹東),綿延萬里。儘管如此興師動眾,卻並沒有遏制住匈奴向內地擴張的野心和實力。
楚漢相爭格局逐漸明朗的情況下,劉邦曾想在平定內地的同時,也能解決秦始皇以來一直困擾中原的邊患問題,但在平城陷入險境,幾乎喪命。這讓劉邦意識到邊患問題的解決絕非一蹴而就。他不得不接受婁敬的建議,確定了與匈奴的和親政策。高帝八年、惠帝三年、文帝前六年,景帝前五年,四次以宗室女為公主嫁予單于。《史記》《漢書》都記載,劉邦死後,冒頓派遣使者送給呂后一封書信,頗多侮辱之詞。而當時的國力依然不強,呂后只能繼續執行和親政策,別無選擇。文帝劉恆起於代王,戍邊多年,深知匈奴問題的複雜尖銳。匈奴憑藉著強大的騎兵優勢,轉戰遊移,靈活多變。而漢朝軍隊的每一次調防,動輒數萬,大兵深入,除了兵源問題而外,最大的困難還在於補給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帝也只能被動防禦,無法解決根本問題。
景帝劉啟初年也曾派遣陶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在解決了吳楚七國之亂以後,他開始認真地考慮如何從根本上解決邊患問題。中元四年(前146),御史大夫衛綰上奏,禁止戰馬出關。這一建議得到景帝高度重視。《漢書·晁錯傳》載,晁錯反思與匈奴的交戰中屢戰屢敗的教訓,在車、馬、人方面,匈奴有其天然優勢。為彌補自己短處,景帝開始處心積慮,充實兵馬。從近年發掘的景帝陽陵陪葬坑所發現的數以萬計的車馬俑來看,雖然只是實物的三分之一,與秦始皇陵兵馬俑有著較大的尺寸差異,但是這裡透露出強烈的資訊,即漢景帝已經把兵馬問題擺在了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在當時,決定戰爭勝負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兵馬。顯然,景帝已為此作了積極準備。
《春秋繁露·王道》:“《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75]漢武帝對於匈奴的關注早在即位之初就開始了。根據《資治通鑑》卷一七的記載,漢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就曾詔問公卿是討伐匈奴,還是執行和親政策。當時,王恢力主討伐,而韓安國則倡言和親。鑑於當時國力,武帝還是聽從了韓安國的建議,但翌年又改變主意,轉從王恢之議,使馬邑人聶壹亡入匈奴,牛刀小試。在他即位的最初六年,這個問題始終困擾著漢武帝。據《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建元中,“漢方欲事滅胡”[76],但是,如何“滅胡”,武帝心裡並沒有底,馬邑之戰,無異於玩火。
從前面的論述知道,漢高祖七年確定的和親政策,確保了邊境七十餘年無大事。馬邑之戰雖然沒有直接交火,但是漢與匈奴的關係卻嚴重惡化,漢武帝當然要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就在這一年,大月氏來使求援,說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顱作為飲器。大月氏憤怒異常,懇請漢朝共擊匈奴。漢武帝正在考慮如何“滅胡”,聞知此訊,乃招募使者前往西域探聽虛實。張騫以郎應命前往,一去十三年,直到元朔三年(前126)才回到京城,帶回來大量的西域資訊。在這期間,漢朝與匈奴的戰爭已經打響。公元前133年六月,漢武帝派遣韓安國、王恢等五將軍率兵三十萬出塞,從此開啟與匈奴長達四十年的戰爭。
從當時戰略形勢看,決定戰爭的勝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雙方對河西走廊的掌控。這是一條集戰略、貿易、通道為一體的通道,直接關係國運的興衰。《春秋繁露·楚莊王》說:“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77]元狩元年(前122),漢武帝開始議置河西諸郡,至後元元年(前88)敦煌郡的設立,河西四郡的建置,前後歷經三十四年[78],成功地斬斷了匈奴的左膀右臂,有效地控制了四周局勢。
河西的穩定,確保了絲綢之路的順暢,有了強大的經濟基礎和軍事實力,這時再“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79],整個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文化上的交流意義也顯而易見。河西四郡設立後,自然有移民計劃隨之而來,提高了當地的文化水準。這些移民中,很多是貧民和罪人。就軍事意義上說,他們的到來,主要是起到了屯兵的作用。此外,還有大量的文人為躲避戰亂,也逃往西北地區。所有這些,都在客觀上促進了當地文化的發展和交流。
《漢書·匈奴傳》載,太初四年(前101),漢武帝下詔伐匈奴說:“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後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80]武帝的拓邊攘夷行動,不僅是“列四郡,據兩關”,還包括開發西南,平定百越、征服朝鮮等戰役。這些政策的制定,有充分的法理依據,這就是“《春秋》大之”。
四、《春秋》“大一統”觀的文化呈現
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第六編《〈公羊〉古義輯》彙總相關資料,說明《春秋》公羊學思想在戰國秦漢時期有廣泛的傳播和重要的影響。其實,不僅僅是公羊學,孔子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褒善黜惡,勒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81]所謂“異言”,即《漢書·藝文志》所說:“《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82]賈誼、司馬相如、王褒、揚雄等人的辭賦,司馬遷、班固等人的史傳,谷永、路溫舒等人的奏記,還有劉向、劉歆父子的雜傳疏議,桓寬、桓譚的著述等,都會引用到《春秋》,儘管師承不同,但都提出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始的主張,多聚焦君臣遇合主題,希望在那樣一個可以大有作為的時代,能夠脫穎而出,建功立業,這是秦漢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可以說,他們的創作與《春秋》大一統觀息息相關,更與秦漢時代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緊密相連。
我們知道,戰國以來養士之風盛行,戰國四大公子自不必說。那個時候的文人,朝秦暮楚,並無一定之規。到了戰國後期,情形發生了變化。呂不韋來自中原,對於戰國以來各家學術應當多所瞭解。他並沒有像戰國四大公子那樣為謀一己之私或一國之利而各有主張。恰恰相反,他充分注意到稷下學宮各派的紛爭與融合,對於各種思想,兼收幷蓄。因此,《呂氏春秋》在學術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對先秦各家學說的彙總。在融匯百家之說的同時,他特別強調了“士”的品行的重要性。他要求的“士”,要講究精神境界,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這表明,經過長時間的戰國紛爭,人們已經厭倦了那種缺乏是非觀念的紛爭,而傾向於對國家一統、萬眾一心的強烈訴求。
西漢初年,劉邦吸取了秦代大權旁落外姓的教訓,分封子弟,與大臣共盟:非劉姓而王者,天下共誅之。地方勢力如吳、楚、梁、淮南等諸國,也由此擴充勢力,並招納文士,擴大影響,又逐漸形成戰國時期的風氣。高祖劉邦之子中,吳王劉濞、楚王劉交、齊王劉肥、淮南王劉長;文帝劉恆之子中,太子劉啟、梁孝王劉武;景帝之子中,河間獻王劉德、魯恭王劉餘等,無不開館延士,為世人矚目。上有所好,下必從之。大臣也隆禮敬士,如平津侯公孫弘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西漢前期重要文人如鄒陽、枚乘、枚皋、司馬相如、羊勝、公孫詭、路喬如、丁寬、韓安國等人,無不在地方割據勢力中擔任幕僚,天下有變,號為“智囊”;承平時期,不過就是文學弄臣。
漢武帝對此心知肚明。他不僅僅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也是傑出的文學家。他深知政權的鞏固需要文化來固本聚魂。因此,他對文人學者,採取恩威並施的政策。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安車蒲輪,徵召枚乘進京。可惜枚乘年老多病,死於道中。但無論如何,枚乘之死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它實際上標誌著盤根錯節的王侯文化逐漸走向終結,標誌著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逐漸走向終結,標誌著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逐漸走向終結,也標誌著漢帝國進入一個思想文化高度統一的全新時期。
在《春秋》“大一統”觀的統領下,秦漢思想家和文學家順應時代要求,積極有為,創造了屬於他們那個時代的文化成果。
在《難蜀父老》《封禪文》等文中,司馬相如多次談到《春秋》,深刻地領悟到《春秋》“大一統”的核心價值。他的《子虛上林賦》比較了諸侯與天子的異同,最終歸結到天子,歸結到一統。史書記載,司馬相如死後,夫人對朝廷派來的人說:“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83]這卷書就是《封禪文》,提出封禪泰山的問題。
嚴助是漢武帝時期一位著名的文學家,來自會稽。武帝即位之初,為吸引優秀人才,特設文學賢良。嚴助藉此機會進入高層,得到漢武的關注。閩越的軍隊攻打東甌,東甌求情。有人主張放棄,認為那是閩越與東甌的問題,與中央朝廷無關。而嚴助別具眼光,認為一定要支援東甌,解決邊地的安穩問題。司馬相如和嚴助來自邊地,在事關國家完整的重大事件面前,表現出鮮明的政治態度,因而得到武帝的重視。
與司馬相如和嚴助相比,董仲舒在政治上並不得志,作《士不遇賦》(《藝文類聚》三十),認為小人當道,“隨世而輪轉”。作者自嘆進退維谷,無所適從。他想到了伯夷、叔齊的高蹈避世,想到了伍子胥和屈原的斃命江心,一心向善,不願向世俗妥協。唐代元結《自箴》《汸泉銘》《淔泉銘》《惡圓》《惡曲》等名文無不源於此。儘管如此,他依然順應了歷史的潮流,提出了一系列維護國家統一的主張。
司馬遷也志存高遠,對戰國以來的縱橫風氣頗為欣賞,而在現實生活中,頗感壓抑,也寫作一篇《悲士不遇賦》,感嘆生不逢時,顧影獨存,屈而不伸,美惡難分[84]。儘管如此,他也“聞之董生”,以《春秋》為本,稱:“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然後“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85],忍辱負重地編纂出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記》,全面系統地勾畫出中華文明自五帝以來“不絕若線”的譜系。《春秋》大義,一覽無餘。所以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下》說:“遷、固本紀,本為《春秋》家學”[86],實為有得之見。
董仲舒和司馬遷在政治生涯上的“不遇”大約是真實的。他們的官位都不高,事蹟也不顯,甚至連生卒年都不詳,但是他們生逢國力蒸蒸日上之時,這種“遇”又是千載難逢的。在這樣一個奮發有為的時代,董仲舒著《春秋繁露》,為漢帝國強化中央集權出謀劃策。司馬遷著《太史公書》,歷史地證明了中華民族是一個同源共生的文明載體[87]。
在漢帝國走向強盛的歷史程序中,以董仲舒、司馬相如、嚴助、司馬遷等為代表的一代文豪,在文化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一是進一步規範文字,為中國的文化一統奠定基礎。
漢高祖劉邦起自布衣,其臣下亦多亡命無賴之徒。他們多不喜歡儒生,甚至見到戴儒冠的,還把他們的帽子摘下來便溺其中。即皇帝位後,群臣爭功,鬧得不亦樂乎,劉邦只能叫叔孫通出來制定禮儀,這才知道皇帝之貴,也由此知道知識的重要性。《古文苑》卷一○載漢高祖《手敕太子》,對自己學無術頗多悔意。作為丞相,蕭何在漢帝國創業之初,就制定了識字書寫制度,多少也反映出劉邦渴求文化的心理。蕭何規定: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試以六體[88],成績優秀者才能為尚書、御史等。官吏上書,字或不正,要被彈劾。《漢書》記載,石奮上書,寫“馬”字少一筆,驚恐萬狀,甚至以為要“獲譴死”[89]。由此可見當時法律的威懾力量。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文字並不統一。即便是距離很近的諸侯國,文字也不盡相同,譬如山東萊陽發現的萊陽陶壺就與鄒、魯不同;甚至鄒魯之間,近在咫尺,其陶文與傳世魯器彝銘文字也有差別。秦以小篆為統一字型,丞相李斯的《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的《爰歷篇》和太史令胡母敬的《博學篇》等文字學著作均以小篆為標準,對於當時文化一統以及漢代文化的發展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
從《漢書·藝文志》序中知道,《蒼頡篇》《爰歷篇》《博學篇》三書在西漢初年多有流傳,有人還將三書合成一書,加以改造,成為兩漢讀書人的基本教材之一。東漢許慎乃會通前代字書,總結了戰國以來解釋文字的“六書”理論,集其大成而著《說文解字》。全書十四篇,敘目一篇,依據文字形體和偏旁結構分列540部,每部以一共同的字作部首,儲存了大部分先秦字型和漢以前的文字訓詁,使原本雜亂無類可歸的文字有了歸類的方式。這是秦漢文人為中華一統所做的最重要的貢獻。最近一百年,在西北邊陲發現的漢簡中,時常有《蒼頡篇》《急就章》等字書,說明童蒙讀物在當地非常流行。
第二是整理圖書,迎接文化高潮的到來。
秦漢以來,朝廷政府對圖書收集十分重視,漢高祖劉邦初攻咸陽時,丞相蕭何率先收藏秦朝的律令圖書。漢武帝時,下令徵集全國圖書。到了漢成帝河平三年(前26),又命謁者陳農前往地方收求遺書。國家藏書日益增多,出現了“書積如丘山”的局面,但也給保藏、流通、閱讀帶來了不便,亟須進行分類整理。於是,漢成帝命劉向在皇家圖書館天祿閣領導了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的圖書整理工作。劉向每校完一書,都附上敘錄一篇,最後又把各敘錄另抄一份集在一起,稱為《別錄》,凡二十卷。《別錄》是中國第一部詳細的書目提要,系統地總結了先秦以來的學術發展情況,對後世目錄學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劉向《別錄》基礎上,劉歆編寫《七略》,將當時的書籍分為六大類,即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略”本是界域的意思,這裡指類別。六藝略包括《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及“小學”等九目;諸子略包括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等十目;兵書略包括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等四目;數術略包括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佔、形法等六目;方技略包括醫經、經方、神仙、房中等四目;詩賦略包括歌詩、屈原賦、陸賈賦、孫卿賦、雜賦等。這種分類著錄,成為中國古籍目錄整理與研究的基本正規化[90]。
第三是創作辭賦,使其成為一種最具大家氣象的文體。
漢代流傳的一些文字學著作,多采用韻文方式,如《凡將篇》《急就章》等,多是七言句式,可能是便於記誦的緣故。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辭賦創作,在描寫物象時,多以類相從,近似一部《爾雅》。還有的辭賦,兼有地理教科書的作用,虛中有實。漢賦的這種特色,貶之者認為這是“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91],揚之者則認為這是一種傳播文獻知識的獨特方式。明代古文家盛稱“文必秦漢”,秦漢文章,特別是應用文章的最大特點就是字字斟酌,句句推敲,可能與此實用功能有關。
不僅如此,司馬相如在前人創作的基礎上,進一步確立了大賦的基本品格,一是內容龐雜,包羅永珍,帶有博物色彩;二是東南西北,古往今來,可謂時空無邊;三是辭藻艱深,華彩飛揚,具有磅礴氣象。在古代文人心目中,辭賦已不僅是案頭文學,也不單純是娛賓遣興的文字,它可以充分展現個人的才學、國家的意志,還有時代的特色。因此,漢唐時期,辭賦創作的好壞是衡量一個文人才學高低的重要標誌。歷代文學總集、文學選本,乃至個人文集,通常要把辭賦擺在第一位,這也成為一種慣例。
第四是建立樂府,透過禮樂制度渲染帝國的權威與執政的合法。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巡視天下,並讓李斯撰寫七篇頌詞,刻在石上,希望流傳久遠。此外,秦始皇還設立樂府,以禮樂演奏的方式,強化歷史的敘述[92]。從唐代杜佑《通典》的記載中知道,在秦漢時代,
掌管音樂的官職有兩個,一是太樂,一是樂府,各有分工,太樂掌管傳統的祭祀雅樂,歸奉常主管;樂府掌管當世民間俗樂,歸少府主管。
《春秋繁露·郊義》說:“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93]在這樣的背景下,郊廟歌就更加重要,成為國家禮儀範疇。《春秋繁露·天道施》說:“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94]司馬相如參與創作了《郊祀歌》十九章,也是體情之作[95]。這些詩歌雖非一時之作,作者也非一人,多是文人創造。還有一部分“歌詩”採自民間,也被演唱,藉此瞭解時政,體察民情。秦漢樂府制度的建立,為維護中央集權起到重要作用。
元狩六年(前117),司馬相如死,漢武帝從其家中獲取《封禪文》。六年後,始祭后土,用雅樂。爾後,武帝發兵平定南越之亂,遂置九郡;又派李息等平定西羌之亂,初置河西四郡,確保中西方經貿文化交流的順暢。西南方面,建立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五郡。武帝以為功高蓋天,遂詢問部下,決定實施司馬相如封禪之議[96]。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即位三十年之際,自制禮儀,正式封禪泰山。同時,漢武帝又大興天地諸祠,命群臣作詩頌,李延年為新聲,郊祀始用樂舞,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從此,漢帝國進入鼎盛時期。
[1]《後漢書·和帝紀》注:“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初開其議,詔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後漢書》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80頁)各郡國察舉人數見《通典》卷一三。《資治通鑑》卷一七謂“從董仲舒之言也”(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576-577頁)。《北堂書鈔》引《漢官儀》:“孝廉,古之貢士,耆儒甲科之謂也。”“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箋奏,初上試之以事,非試之意誦也。”(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七九,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4頁)
[2]《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523頁。
[3]《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第2523頁。
[4]《春秋公羊傳註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196頁。
[5]陳徽:《〈尚書·洪範〉與公羊“大一統”思想》,《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
[6]《春秋公羊傳註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第2196頁。
[7]蘇秉琦:《談“晉文化”考古》,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三晉考古》第1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頁。
[8]《史記》卷六七,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203頁。
[9]《漢書·藝文志》著錄《李子》三十二篇,已經亡佚。《晉書·刑法志》稱作《法經》六篇。秦漢以後的法律都是以《法經》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
[10]《史記》卷七○,第2304頁。
[11]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卷二,《新編諸子整合》,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95-96頁。
[12]《史記》卷四七,第1910頁。
[13]《史記》卷七《項羽本紀》,第300頁。
[14]詳見劉躍進:《釋“齊氣”》,《文獻》2008年第1期。
[15]詳見劉躍進:《賈誼所見書蠡測》,《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
[16]《漢書》卷三九《蕭何曹參傳》,第2019頁。
[17]朱一新《無邪堂答問》:“老氏書作用最多,乃示人若無所能,使人入其牢籠而不自覺,開後世權謀變詐之習,故為異端。”(朱一新著,呂鴻儒、張長法點校:《無邪堂答問》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81頁)
[18]參見劉躍進:《“魯學”解》,《齊魯學刊》2008年第1期。
[19]《史記》卷九九《劉敬叔孫通列傳》,第2723頁。
[20]陸賈著,王利器校注:《新語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9頁。
[21]《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第2504頁。
[22]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3頁。
[23]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第35頁。
[24]《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第2505頁。
[25]《春秋公羊傳註疏》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第2190頁。
[26]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第一編《導言》第一章:“按《公羊傳》之著於竹帛在景帝時之說,其證則哀三年經‘季孫師、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左氏春秋》開陽作啟陽,《公羊》作開,正為景帝諱之也。”(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9頁)
[2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第24頁。
[28]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二,第15頁。
[29]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九,第56-57頁。
[30]《禮記正義》卷六三,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第1695頁。
[31]《漢書》卷七二《王吉傳》,第3063頁。
[32]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七,第42頁。
[33]《春秋公羊傳註疏》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第2196頁。
[34]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第42頁。
[35]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第39頁。
[36]《春秋公羊傳註疏》卷二八,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第2353-2354頁。
[3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第10頁。
[38]《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第2501-2502頁。
[39]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七,第41頁。
[40]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第59頁。
[41]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第19頁。
[42]歐陽修:《原正統論》,《歐陽修全集》卷一六,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276頁。
[43]歐陽修:《原正統論》,《歐陽修全集》卷一六,第276頁。
[44]梁啟超:《論正統》,《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上海:上海中華書局,1932年,第20頁。
[45]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第23頁。
[46]《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第2515頁。
[4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第35頁。
[48]《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第2502頁。
[49]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五,第33頁。
[50]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第35頁。
[51]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四,第25頁。
[52]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第12頁。
[53]《漢書》卷五一《路溫舒傳》,第2369頁。
[54]《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第2498頁。
[55]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八,第54頁。(《漢書·孔光傳》:“臣聞師曰,天左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兇罰加焉,其至可必。”《谷永傳》:“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八一、卷八五,第33-59頁、第3450頁)
[56]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四,第25頁。
[5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一,第65頁。
[58]《史記》卷一四《十二諸侯年表序》,第509頁。
[59]《春秋公羊傳註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第2249頁。
[60]《孟子註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7-35頁。
[61]房玄齡注:《管子》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2-103頁。
[62]楊倞注:《荀子》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9頁。
[63]呂不韋:《呂氏春秋》卷一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1頁。
[64]《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第2540頁。
[65]賈誼:《賈誼新書》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0頁。
[66]賈誼:《賈誼新書》卷四,第33頁。
[6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四,第25頁。
[68]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五,第33頁。
[69]賈誼:《賈誼新書》卷二,第17頁。
[70]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八,第48頁。
[71]胡安國《春秋傳》三十卷就強調“復仇”之義,顯然有感於南宋初年政局而發,所以清人尤侗說此書是“宋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這是後人解釋《春秋》的常用手法。
[72]《春秋公羊傳註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第2249頁。
[73]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第23頁。
[74]1980年代發掘的南越王墓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參看李林娜主編:《南越寶藏》,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75]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四,第27頁。
[76]《漢書》卷六一《張騫李廣利傳》,第2687頁。
[7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第9頁。
[78]參看劉躍進:《河西四郡的建置與西北文學的繁榮》,《文學評論》2008年第5期。
[79]《漢書》卷六四下《賈捐之傳》,第2832頁。
[80]《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第3776頁。
[81]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卷一○,長春:吉林出版社,2017年,第167頁。
[82]《漢書》卷三○《藝文志》,第1701頁。
[83]《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傳》,第3063頁。另參看劉躍進:《〈子虛賦〉〈上林賦〉的分篇、創作時間及其意義》,《文史》2008年第2期。
[84]五百年後,陶淵明亦有《感士不遇賦》,序說自己讀董仲舒、司馬遷之作,慨然惆悵,感嘆真風告逝,大偽斯興,正道清操之士,一籌莫展,抒發的依然是同樣的感慨。
[85]《史記》卷一三○《太史公書自序》,第3297、3319-3320頁。
[86]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31頁。
[87]關於司馬遷的生平事蹟,參見劉躍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司馬遷及其〈史記〉綜論》,《學術交流》2020年第5期。
[88]所謂六體,指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
[89]《漢書》卷四六《石奮傳》,第2196頁。
[90]參看劉躍進:《試論劉向、劉歆父子的文學業績與學術貢獻》,《江蘇師範大學學報》2020年第3期。另見劉躍進:《目錄學與當代中國學術研究》,《資料與文獻學報》2020年第4期。
[91]蘇軾評楊雄《法言》《太玄》語,吳伯雄編:《四庫全書總目選》卷九一,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第256頁。
[92]1976年陝西臨潼縣秦始皇墓附近出土秦代編鐘,上面刻有秦篆“樂府”二字。參見寇效信《秦漢樂府考略———由秦始皇陵出土的秦樂府編鐘談起》(《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1期),袁仲一《秦代金文、陶文雜考三則》(《考古與文物》
1982年第4期)等文。
[93]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五,第82頁。
[94]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七,第99頁。
[95]《史記·樂書》:“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暤,冬歌玄冥。”(《史記》卷二四,第1167-1168頁)這四首詩即見十九章中。唯《西暤》有異文,作《西顯》。詳見《樂府詩集》卷一“郊廟歌辭·漢郊祀歌二十首”題解(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3頁)。
[96]《漢書·藝文志》著錄《封禪議對》十九篇,注:“武帝時也。”(《漢書》卷三○,第1709頁)
來源: 《文史哲》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