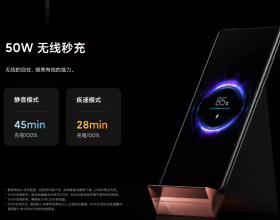1921年7月,當一群平均年齡28歲的年輕人聚集在當時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那幢石庫門建築客廳中時,他們中的大多數一定不會意識到自己正在開啟一項徹底改變中國現代歷史發展軌跡乃至重塑世界政治版圖的驚天偉業。
今天看來,將這件開天闢地的大事搬上銀幕是一件難乎其難的事情。一百年前那樁大事的客觀過程是年輕人相聚幾天,通過幾個決議。憑這段故事,要轉換成兩個多小時時長的無數個鏡頭畫面,要可看耐看,並需面對前人就此題材已有過的多方嘗試,難乎其難。
面對這樣的“開天闢地”和“難乎其難”,電影《1921》贏得一片喝彩,究其原因,固然有電影作為綜合藝術所需方方面面的協同發力,但更在於創作者緊緊扣住了一個核心: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這個大主題。
《1921》中有兩個令人難忘的場景:楊開慧望著天上的煙火,向毛澤東發問,“人生好短,短到可能看不到勝利的曙光,今天的付出還有意義嗎?”毛澤東堅定地回答,“當然,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國家,無法選擇自己的家庭,但我們可以選擇自己的理想。為理想奮鬥,為真理獻身,即便是一無所獲,也值得”;在中共一大結束前晚,劉仁靜不無擔心地問毛澤東,“分歧那麼大,明天還能不能透過?”毛澤東的回答同樣鏗鏘,“能!因為我們的起點一樣,誓死推翻舊世界。僅此嗎?還因為我們的理想也一樣,盼望著建立新中國,大家想要的人民做主的新中國!”
“理想”——在中共一大舉行的首尾,從毛澤東口中兩次堅定吐出的這兩個字是《1921》的關鍵所在。影片之所以凸顯這一點,並非出於“烏托邦”式的浪漫主義,而是建立在歷史真實基礎之上。出席會議的大部分代表家境並不差,僅從物質層面並不存在“窮則思變”的理由與衝動。他們願意放棄安逸優越的生活,乃至承擔在今後遭遇酷刑或殺戮的風險,如果沒有堅定而強烈的理想信念支撐,這一切就無從解釋。也正是因為有這樣一群志同道合者走在一起,這個在當時全國僅有50多名黨員的新型政黨,方能做到僅用28年的時間就改變了中國。
當然,電影如果僅僅只是緊扣理想這一核心而缺乏相應合情合理合史的藝術表現支撐,則會導致空泛乃至虛浮。為了避免這種情況,《1921》又精心建構起了堅實的兩翼,即緊緊圍繞1921這個時間軸,向前向後、向內向外進行時空延伸,描繪出席會議的代表們那些豐富而生動的細節。
在《1921》的首尾,各有一段蒙太奇式的多時空混剪。大幕開啟,觀眾跟隨陳獨秀的視角,回顧中國近現代史上積貧積弱、民智未啟的混沌日子,感受即將影響全球的風雲變幻。而到了嘉興紅船出現時,銀幕上出現了一串快速的時空切換剪輯:楊開慧犧牲、鄧恩銘犧牲、何叔衡犧牲……從1921年到1949年,既有無數懷揣理想的生命消失在追逐理想的歲月中,亦有動搖者、變節者混跡其中。這種以1921年的上海為軸心,向前向後、向內向外的時空拓展,充分調動了鏡頭語言,紮實而形象地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這個關鍵問題。
如果說《1921》的主情節是中共一大的召開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那麼圍繞著會場內的主場景,更多會議前與會場外與會代表的種種活動細節則栩栩如生、耐人尋味。比如劉仁靜、鄧恩銘和王盡美三個20歲左右的年輕黨代表,到上海駐地剛安頓下來便跑去大世界看哈哈鏡。比如毛澤東受李達、王會悟夫婦之邀共進晚餐後返回途中,巧遇法國人在法租界為國慶狂歡,而中國人卻被攔在外面。毛澤東憤然擠出圍觀人群,奔跑起來,速度越來越快,步幅越來越大。諸如此類生動鮮活又充滿寓意的生活細節在影片中比比皆是。正是這些豐富細節的支撐,影片中那些人物才得以活起來、立起來。
作為一部圍繞重大主題創作的文藝作品,《1921》成功的原因有兩條。首先是對錶現物件有著深入而科學的認知與理解。建黨百年這件大事有兩個客觀事實,一是建黨之初只有50餘名黨員的政黨何以只用28年的時間就“換了人間”,後來這個政治組織何以只用幾十年的時間就讓長期積貧積弱且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擺脫了貧困,還成功坐穩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對這兩個問題的回覆,就是如何科學評價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更是保證作品基調不走樣的原則問題。其次則是對藝術規律充分而有個性的尊重。確有個別作品,題材重大,主題積極,但就是不好看。出現這種問題的根本原因不是功夫不到就是能力不足。相比之下,電影《1921》以青春化表達讓不同時代的年輕人進行對話——銀幕中的年輕人探索未來,銀幕外的年輕人重訪歷史。這些努力為重大主題文藝作品的創作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成功範例。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原副總裁)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