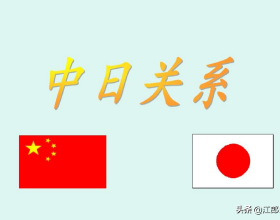“國籍”和“國界”是極其近代化的產物。在“國境”這一概念固定下來以前,東亞世界裡確實存在一種根據統治者的需要而變化的領土意識。
政邦藏書架
今天推薦的好書是
《中世日本的內與外》
現代的日本人是如何認識日本的內與外的?
也許人們腦海中浮現出來的是國際機場的出入境手續、侵犯領海的“國籍不明船隻”或難民船,或者在街角和店鋪見到的外國人。
或許也有人會想到“北方四島”等領土糾紛。有獨自去外國旅遊經驗的人或許會想到踏入“日本”以外空間時的孤獨和緊張,或者也會有自由與解放的感覺。
不管怎麼說,無論是空間(即領土或領海)還是人(即國籍或居住權),都屬於某一個“主權國家”,因此,現代的內與外是明確地區分開來的。
譬如福建人乘坐的偷渡船在五島一帶被發現,遭當局逮捕。聽到這個新聞,有的人認為他們是犯罪者而加以指責,有的人則對他們的境遇表示同情。
但無論哪種情況,他們是與“內部”的日本人不同的“外部”人,這一點是一樣的。
那麼像這樣,日本的內與外存在明晰的界限,這種感覺是從很久以前就有的嗎?
說起來,“國籍”或“國界”的概念成為世界通行的標準,並非多麼古老的事。
超越各國疆域普遍適用的“國際法”,是在17世紀上半葉由荷蘭法學家胡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理論化的。
日本是在討論如何接受由“黑船”帶來的條約體制時,也就是從開國到明治維新的時期,即19世紀下半葉開始接受國際法的各種概念的。
在此,我想提一個可作為思考線索的問題:北海道除函館和松前周邊以外大部分地區,在江戶時代是哪個國家的領土?可能有人會認為,當然是日本了。然而,在18世紀末俄國船從北方來到北海道近海之前,江戶幕府將北海道大部分地區視作“無主之地”。
在江戶時代,北海道唯一存在的藩是以渡島半島西南端的松前為城下町以領主居住的城堡為中心形成的規劃性城市,通常由武家地、工商業地、寺社地等構成,是江戶時代城市的基本形態。
松前藩的將軍換代時,新將軍會交付給各藩主再次確認其統治權的書面檔案“領知判物”。檔案內一般會記載“石高”。所謂石高,就是將藩領的生產力按照大米產量換算的總計數值,是確定租稅數量的基準,也顯示了藩的地位。但是,交付給松前藩主的領知判物裡沒有關於石高的記載。
記載在領知判物上的石高,意味著幕府從數量上掌握了該藩領地的多少,並將此範圍內的統治權委任給該藩。因此,松前藩並沒有被幕府委任北海道的空間統治權。那麼,松前藩在北海道實行的統治究竟是什麼樣的?
日本“內地”各藩大名給家臣發放的俸祿是由藩領租稅的一部分充當的。松前藩則是把在北海道河川河口地點設立的與阿依努人進行交易的場所(即“商場”)分給家臣,將“商場”的收益充作俸祿。這叫作“商場知行制”。
這一制度到了江戶時代後期變為“商場承包制”,即藩外的商人承包與阿依努人的交易,藩士收取其所獲利潤的一部分。
在這兩種情況下,阿依努人都與“內地”藩領的農民完全不同,沒有被納入幕府和松前藩的空間統治物件。當時的人們稱其為“化外之民”。松前藩的統治空間只不過是以松前為中心的北海道南部的一部分。幕府及松前藩將這一區域稱作“和人地”,除和人地以外的北海道大部分地區與南千島群島、庫頁島一起被稱作“蝦夷地”。
當然在經濟上,松前藩士和商人等和人殘酷壓榨阿依努人,後者的從屬程度加深了。此外在政治上,依慣例阿依努首領要對松前藩的官員行一種叫作“Uymam”阿依努語,相當於“御目見得”,指有謁見將軍資格的旗本武士的臣服儀式。倒不如說,“化外之民”這一地位使幕府和13松前藩從統治者應盡的保護義務中解放出來。
但若將觀察點轉移到阿依努人一方,“蝦夷地”無非是“我們的大地”(ainu mosir阿依努語),居住在這裡的阿依努人是一個獨立的民族,他們以貿易為生,與和人、吉利亞克人(Gilyak)等北方民族,甚至明、清或俄國等都有貿易往來。
作為一個民族,阿依努人雖沒有建立自己的國家,但內部有北海道西部阿依努、東部阿依努、千島阿依努、庫頁(樺太)島阿依努等從屬集團存在,由首領們進行政治統治。在此背景下,發生了1669年的沙牟奢允之戰、1789年的國後目梨起義等對和人壓迫的事件。
蝦夷地的以上狀況在俄國人穿過西伯利亞到達東方海域,出現在日本近海之時,發生了很大變化。
從1779年,以俄國船駛抵厚岸、要求與日本通商為契機,一直到1810年代,其間相繼發生了俄國人到蝦夷地殖民,以及千島與庫頁島上日俄兩國勢力的衝突。
幕府與俄國對抗後 ,痛感蝦夷地的軍事重要性,一方面派遣最上德內、間宮林藏、近藤重藏等探索千島、庫頁島地區,另一方面於1802年設箱館奉行越過鬆前藩開始積極管轄蝦夷地。
此外,1799年,東蝦夷地(北海道太平洋一側)以七年為限由幕府直轄,1802年改為無限期,1807年西蝦夷地(北海道日本海一側)也由幕府直轄了。失去居所的松前氏被轉封到陸奧梁川。
此後,北方的緊張局勢稍微緩解,1821年蝦夷地被歸還松前氏,《日美親善條約》簽訂的1854年,幕府再度直轄蝦夷,設定箱館奉行。最終到明治維新時,北海道開拓使繼承了原箱館奉行的職責。
就這樣,日本中央政府不斷加強對蝦夷地的控制,同時在國際法上,也需要與俄國明確領土關係。1855年的《日俄和親通好條約》(《下田條約》)規定,千島群島中烏魯普(得撫)島及其北為俄國領土,伊圖魯普(擇捉)島及其南為日本領土,但庫頁島保留了兩國人雜居的狀況。設定北海道開拓使後,依1875年的《樺太與千島群島北部互換條約》,庫頁島確定為俄國領土,日俄之間的領土問題暫時得到了解決。
庫頁島曾為中國直接或間接統治。1689年9月7日,中俄兩國簽訂《尼布楚條約》,確定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屬於中國領土。1858年和1860年,俄國和清政府分別簽訂《璦琿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清政府被迫割讓庫頁島給俄國。
然而,如果從阿依努人的視角來看,這一“解決”方案只是透過主權國家間的交涉徹底剝奪了阿依努人“我們的大地”所擁有的權利。
明治維新以後,在“近代的”土地法律制度下,“化外之民”阿依努人對其狩獵或捕撈場所的土地所有權不被承認,很多人被驅離了世代生活的土地。
1899年明治政府制定《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一方面強調保護阿依努人的權利,另一方面卻讓阿依努人被固定為“二等國民”。順便說一下,這一法律隨“阿依努新法”即《阿依努文化振興法》的生效而廢止,這是在1997年的事情,希望大家牢記這一點。
如上所述,我們感到理所當然的國界、國籍等概念嚴格來說是近代的產物。
在前近代,國家疆域的外圍地區與中心地區具有不同的特徵,前者的居民作為“化外之民”,基本上不屬於政治統治物件。並且同一空間也是鄰國的外圍地區。我把這樣的空間叫作國家疆域之間的“境界”。
這裡所說的“境界”,與現代地圖上用線條表示的、沒有面積的國界不同。如蝦夷地的事例所見的那樣,“境界”本身範圍很廣。並且正如阿依努人這樣,很多人便生活在這寬廣的地域內。“境界”的經濟基礎是連線多個國家空間的貿易活動,阿依努人這樣的人——可以將其概念化為“境界人”——正是此種貿易中的核心人物。
換言之,前近代的內與外並不能區分為兩個特徵迥異的空間。兩者間隔著“境界”,從內向外、從外向內都是連續的空間。我想以日本的中世一般日本史分為古代(11世紀末以前)、中世(11世紀末至16世紀末)、近世(16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近現代(19世紀中葉至現在)。作者立足於東亞海域史的視角,將中世的上限提前到9世紀。——此處所指比通說更寬泛一些,為9世紀到17世紀上半葉——為範圍來考察這種獨特的內外關係。這是貫穿本書的第一個視角。
再者,思考內與外的歷史時,還有一個有效的視角——“比較史”視角,即沿某個中軸比較“內”和“外”,由此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內”的本質。
若看先前所舉的江戶時代的蝦夷地的例子,日本與俄國都想把“境界”納入自己的版圖,但其方法很不一樣:日本採取的是以幕府或和人的“德”,招攬阿依努人到貿易場所的方法;俄國人則採取了自己到阿依努社會當中“殖民”以確保據點的方法。這種差異源於中華文明圈與歐洲文明圈如何接觸“外部”世界的傳統差異。
本書試圖透過日本與朝鮮等亞洲其他地區的比較,來探究中世日本的發展歷程所具有的意義。
本文為《中世日本的內與外》的引言,原標題為《混合的內與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