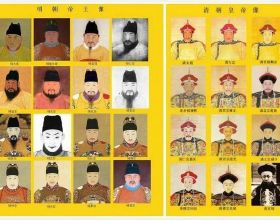楊濯/文 明史專家卜正民在《掙扎的帝國:元與明》中說:“瓷器是中國人的發明,但是青花卻不是……對白底藍紋的偏好最早起源於波斯。”其實燒製“青花”所用的顏料鈷藍在中國本土也並不出產,在歷史上被稱為“回青”,顯然來自伊斯蘭世界。典籍中也有稱鈷藍為“蘇麻離青”“蘇渤泥青”,從譯名看“回青”是從蘇門答臘轉運而來。“穆斯林商人提供鈷藍原料,進行造型設計,下達採購訂單,預付定金包攬生意;而景德鎮民窯接單燒製,中國海商負責突破海禁、遠途運輸,完成貨物接駁後,穆斯林商人再將這些青花瓷轉運歐洲市場銷售”。
在《天下1:明清對外戰略史事》一書中,中國政法大學歷史研究所鄧文初教授指出,即使在大明帝國最為嚴苛的海禁時期和此後葡萄牙人控制南中國海-印度洋貿易時,“回青-青花瓷”這條大明帝國與伊斯蘭世界的物流線並未中斷。在15至18世紀,“一個覆蓋歐亞大陸的全球市場已經悄然形成”,而且中華帝國主動參與其中並起到某種龍頭作用。
與世界經濟關係越來越緊密,卻引發了中華帝國在政治、經濟與軍事等方面的巨震,“不僅社會結構被整體改造,社會心理也發生了足以顛覆儒家信念的改變,帝國權威尤其面臨著巨大的威脅”。帝國面臨著調整自己內外戰略的抉擇,而這種戰略調整又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帝國此後的命運。
近代以來中國的外交變局是如何形塑的,這種外交變局導致怎樣的政治變動與文化變遷,國家以何種學理依據來認知、決策和應對這一變局,如果沒有這場中西交往與衝突,依然長存的歷史程序是否無法給中國這個古老的機體注入新的生命,正如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判定東方的歷史是停滯的或者如卡爾·馬克思所批判的“密閉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樣?
從傳統史學角度來看,《天下》一書要處理的這一連串“老大難”問題,近似於探究“西方的崛起”與“中國的衰落”的東西分流說。就像彭慕蘭(KennethPomeranz)在《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中提出的那樣,東西方在18世紀以前似乎走在一條大致相同的發展道路上,任何一方均沒有任何明顯的、獨有的內生優勢;但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東西方開始逐漸背離、分道揚鑣。
王國斌和羅森塔爾近年出版的《大分流之外》,也只是挑戰了“人口-資源決定論”和“市場制度決定論”,認為促成歐洲和中國經濟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大分流”的真正原因,其實是各自草蛇灰線般掩藏在公元11至13世紀的歷史之中的政治程序、政治制度和政權規模等政治性因素,將“大分流”時間節點推至忽必烈統一中國,並認為由蒙古人開創的“大國”式的超大規模政治體帶來的廣闊的國內市場、成熟的勞動分工以及政府對於社會的弱干預模式,是中華帝國早在西方之前就已經進入“斯密型增長”的原因。王國斌和羅森塔爾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模式或中國道路遠遠先行於歐洲,導致中西分流的工業化路徑很可能是歷史的偶然。
鄧文初指出,上述論斷在方法論上可能存在巨大失誤。其一、作為研究物件的東亞實體並非同質體,內部市場並非完整統一,多種文明並存甚至對峙,中央集權式的治理模式與等級化的官僚體系的覆蓋面侷限於漢文化區域,周邊還並存著諸多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其二、這一東亞實體也會隨著歷史程序而變換面孔,“它既是一個國家、一個帝國,也是一個世界,一個華夷體系與多文明的互動系統”;其三、研究不應過早提出一套宏觀性的結論,而應當關注經濟活動背後的“人的主題”和權力的性質,包括人的意志、慾望、理想與行為,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相互比較與等級構造、群體塑造,以及由人之關係所代表的國與國之間關係和主體意識建構、利益訴求、區域組合與霸權爭奪,等等;其四、在強化分析規模優勢時,也不應忽視超大規模的困境所在,如“超大規模政治體與皇帝個人之治之間的矛盾,帝國對資源的集權配置與市場自身法則之間的衝突,華夷秩序內部的等級與平等訴求之間的緊張,天下主義對於外部世界的封閉造成的貿易梗阻與戰爭頻發等引致帝國政治衰敗的問題”。
可以說,“加州學派與其所批判的世界體系理論一樣存在著方法論困境”,採用“中心-邊緣”時,卻忽視了無論是中心還是邊緣,其內部仍存在著數個層級的、巢狀的“中心-邊緣”結構,而且在這種層級結構中,“邊界並非固定、清晰,而是始終處在變遷與替代之中,建構中的關係與關係的建構也許更應該是歷史學關注的重心”。
正因如此,鄧文初認為,如果歷史研究要抓住真確的“中國問題”,並以真正的“本土化”話語展開闡述,首先要解決的並非西方中心主義遮蔽,而是要直面和修正某種現代人的以自我中心主義為基礎的認知建構。
更重要的是,這種認知偏差無所謂西方或東方,“沒有比較,甚至連自我認知都不可能,遑論歷史反思與文化重建”。當我們糾結於“歐洲中心論”的“東方主義”究竟是偏見還是事實時,或許也需要追問新的全球史與“中國中心觀”是否又是一種顛倒了的“西方中心主義”。
正確的發問方式:“忽必烈的未竟事業”如何完成?
那麼,應該如何以“本土化”話語提出真確的“中國問題”?鄧文初在其個人學術生涯中一直持續關注某個獨特的現象:在世界歷史的巨大變遷中,中國似乎是唯一一個保持著帝國規模的統一國家,甚至在近代以來幾乎所有其他帝國崩潰的同時,“仍舊維持著一定程度的規模與統一”。鄧文初試圖在明清帝國的歷史程序中對此梳理起源、廓清歷史慣性並提供初步回答,努力透過正確的發問方式,讓“舊問題”獲得“新生命”:如何在制度上消化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的政治實體,以實現一體化程序?
對此,鄧文初教授借用了日本學者檀上寬在《永樂帝:華夷秩序的完成》一書中引入的“忽必烈的未竟事業”的概念:忽必烈的龐大帝國所開啟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波全球化歷史程序,並不因為元末反抗力量的衝擊而分崩離析,“反而隨著以漢族為主體的大明帝國的興起,大一統記憶被啟用並得到強化”,成為明清帝國乃至近代中國的“歷史使命”。但是,由於元朝統治時間過短,未能完成中華一體化的制度與知識建構,未能完成帝國的政治整合任務,給後繼者留下了一個巨大而複雜的難題:即“如何整合一個由元代遺留下來的超大規模的政治實體,以實現天下一體化、華夷秩序一體化,或者說實現帝國的南北大一統”。
可以說,中華帝國“先於西方世界且在幾無知識準備的情況下過早進入全球化議題,從而造成‘消化不良’”。當明清帝國所面對的巨大政治困境無法從制度上“消化”這個“忽必烈的遺產”時,帝國的政治整合或者“天下的建構”也就難以完成,明清兩代政治的重心也就註定要糾結於如何完成這個“忽必烈的未竟事業”,帝國也就有可能在向民族國家轉型的近代化過程中,引發巨大的“政治-社會”震盪。
更進一步來看,超大規模政治實體的一體化整合難題,也並非僅僅是中華帝國的內生困境,更是全球化過程中人類必然面對的共同困境。在鄧文初教授的觀察中,第一波全球化的標誌,就是知識擴張的時代和帝國的全球擴張模式開啟了人類的近代歷史程序。人類歷史因地理隔絕而曾有過相對獨立的發展空間,但歷史在全球化開始後已經相互纏繞在一起,“每個帝國都是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獲得自己的發展空間與歷史意識的”,而對此“共時性”現象的意識,可以為我們重新認知原來各自獨立書寫的“國家歷史”提供一個全球性框架。事實上,人類至今也不敢妄稱已經找到了可以妥善推進“忽必烈的未竟事業”的理想制度,“歷史並未終結,而是仍在探索之中”。
鄧文初認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文化相對主義與本位自信所能存在的唯一前提條件,是彼此間的孤懸隔絕和老死不相往來。“帝國時代的降臨,早已將這種道家烏托邦的存在基礎摧毀殆盡”,終將透過比較的過程導向重建“一套共識、一套規則、一套交流與理解的語法、一套國家間戰爭與和平的倫常,為人類社會之共存奠定基礎”。
現代國際關係的確立以主權為核心,而“從根本上說,主權概念是一種相互承認的結果”。這一原則適應傳統的帝國政治,也適應現代國際關係,“這也是大明取代元朝之後,朱元璋需要派出各路‘行者’向周邊國家宣示的原因,也是大清能夠與俄羅斯達成條約關係的原因”。
弔詭的是,中華帝國“天下主義”的世界秩序在理論上可以無限擴張,因此也就不需要“對外關係”這一現代國際政治事務及理論。“當這種自我中心主義獲得了系統的理論建構與強大的帝國力量的支援時,它就會成為一種霸權”,無論是以道德的、禮儀的、宗教的或文化的,還是以赤裸裸的暴力方式表現出來,根子裡其實都是“征服”。但這種內外不分的現實也必將導致國際衝突的內化、國內戰爭的外化,從而使得天下秩序永久性地處在動盪之中並因此失去控制,繼而錯失了平等人格和國格的相互尊重與確認,錯失了人類整體感和自由意志的發現與張揚。
“雙重身份”與知識體系停滯:“天下主義”的挫折
鄧文初認為,“雙重三角關係”是制約大明帝國戰略決策的結構性力量,其中“外三角”關係指的是大明帝國將戰略重心鎖定在與北部元帝國殘餘勢力的角鬥中,與此同時伊斯蘭世界的崛起並向印度洋與中亞的擴張;而兩個平行的“內三角”關係,則分別是“南中國海-印度洋”區域內大明帝國、伊斯蘭帝國與東來的西方勢力的相互糾纏和博弈,以及東亞地緣格局中大明帝國與日本、朝鮮的複雜互動。大清帝國前期所面對的最大的地緣政治格局變化,是俄羅斯帝國的東進形成了“俄羅斯-蒙古-大清”這一框架性的“外三角”,並演化出“準噶爾-東南部蒙古-大清”和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西方勢力以及崛起中的日本與大清帝國這兩個新的平行“內三角”。
地緣政治中的“雙重三角關係”,表面看是對抗性的、多邊的博弈關係,但在鄧文初看來卻是利益互生關係和相互依賴關係,有望由多邊關係構成一種區域性的共同體,“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脫離整體而獨存,也沒有一個民族可以真正做到閉關自守、自給自足”。無論從地緣政治、戰略縱深還是制度構架上看,帝國都並非天然具有強固的結構。特別地,對超大規模的政治體而言,“必然意味著超大規模的接觸頻率、幅度與超大規模的地緣政治複雜性的存在”,除非實行全方位的封閉,否則帝國的穩固就必須直面外力干擾。
正是因為意識到這一點,明清帝國不以直接統治來維持天下秩序,而訴諸於“天下主義”的意識形態構想、文化宣示與話語表達,將帝國的內部統治結構在國際秩序中自我複製為華夷秩序的等級結構:天下夷狄是平等的,“中國”——作為天下共主的中原帝國——是立法者、監視者與仲裁者,天子和作為天子存身之所的“中國”都必須是高高在上的超然存在。這就要求“中國”必須脫離實體概念,不能以一個帝國的國家身份形式出現,而只能以一種建立在象徵符號基礎上的權威的功能出現,帝國所能動用的力量只能是道義的與象徵的,而這正是明清帝國處理海外華僑事件時的姿態。
朝貢體制的形成,歸根結底正是武力征服與威懾的結果。正如拉鐵摩爾的邊疆理論所分析的那樣,大清的內藩處於行政控制線之內,而所謂的朝貢體制實質就是處在大清軍事打擊半徑範圍之內的帝國體制,“大清對治朝貢諸國的政策,是建立在軍事佔有之效益成本估算基礎上的,所謂的道德文教,只不過是其邊際效用遞減的替代罷了”。
不過,帝國一旦啟用硬實力,選擇純粹軍事征服的方式,就會引發對其天下共主的合法性身份的質疑與挑戰,因此帝國往往以道德反思與自我審判的面目出現,以補救道義的喪失,這又與具有自我實質性利益的“帝國”實體產生矛盾,因為事實上“帝國”擴張本身是其維持天下共主身份的現實基礎。
於是,帝國不得不在天下秩序之內、在“雙重身份”之間搖擺,難以獲得真正的平衡。無論是壬辰之戰(又稱萬曆朝鮮戰爭)中明帝國打擊日本試圖模仿華夷秩序建立由自己領導的小型“天下”的朝貢體系的野望,還是在平定準噶爾部戰爭中康熙“由自詡的天下共主、各部族的仲裁者轉變為一方勢力的保護者,再進一步轉變為整個蒙古地區的統治者”,概莫能外。“天下主義的國際秩序,就成為一種囚禁帝國自身的道德牢籠,在這種自我束縛下,帝國反而失去了處理國際事務的主動與能力”。最為遺憾的是,明清帝國的戰略重心既受控於多邊國際關係所構造的客觀形勢,又被帝國意識形態與知識體系所制約。
由於並不存在超然性的知識共同體或獨立的決策階層,“因此無法發展出一整套基於政治實踐的新的理論體系來,新的政治實踐也就無法納入新的認知之中”。制度與知識的雙重缺失,使政治運作成為沒有監控與評價體制的絕對權力,變成權力集團內部的迴圈。保守主義式的不作為或許是最安全同時也是最經濟的態度,“決策者及官僚個人的理性成本考量,卻由帝國付出的沉重代價來買單”。“對外的封鎖在禁錮外來影響的同時,也禁錮了自我強大的機會”。鄧文初敏銳地指出,帝國的知識體系這種根本性缺失,導致“沒有面向事實的勇氣,沒有突破制約的勇氣,沒有對世界相互依存的承認”,從而無法從帝國困境中脫身而出、創造性地改變帝國的政治實踐與格局,無法真正理解“相互依存”“有無相易”的國際關係事實,也錯失了“在確認自己的同時也確認他者,主張自己利益的同時也尊重他者的利益”的互動過程。可以說,東西方的興衰、全球史上的“大分流”,其實在這樣的知識分流中早已決出勝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