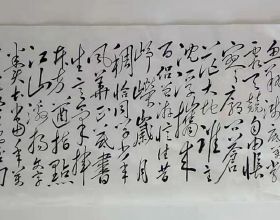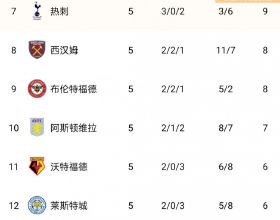誰會留存自己十幾歲寫的作文呢?感謝恩師董文浩先生,將他珍藏多年的豐南一中《稻地》文學社的油印刊物,全部贈予了我。這讓我如獲至寶!因為,其中有很多我在上學時留下的,從體裁上分,可以叫做詩歌、散文、小小說之類的非常稚嫩和拙樸的文字。今天選取的這篇《二十年後再相會》,是我 17 歲那年寫的。30 年前的一個小毛孩子會寫個啥呀?所以,今天發出來,絕不是為了賺取大家的眼球兒,只想給自己留下一份青澀的印跡,或者說叫作心路歷程的見證吧!
附文:
公元一九八七年的最後一天,最後一分鐘的最後一秒,隨著新年之鐘的鳴響終於同我們分別了。
霎時,同學們歡呼起來,在《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的歌聲旋律中,我們手挽起了手,跳起了歡快的“拉拉舞”,共尋昨日十七歲的我。
啊,我們這一群同學、朋友,再過二十年,就都已是三十七八歲的父親、母親,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已奮鬥十多載了。
多麼美好的時刻!
我幸福地閉上眼,想著二十年後的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日:這天早晨,我剛剛洗漱完畢,妻子就進了屋。她溫柔地望著我,遞過一張大紅請柬:
DHT 先生:
您好!我以今天豐南一中校長,二十年前老同學和同鄉的身份,邀請您在本月三十一日前能按時到故校共聚。見面詳敘。
老同學 侯玉敏
2008 年 12 月 29 日
“我一定要去,馬上動身!”看後,我很激動,沒來得及多想,便急著催促妻子說:“快,快幫我收拾東西!”
我一邊整理剛剛脫稿的“考古”論文,一邊找出了因考掘出了西漢的劉徹帝墓而授予我的“一等功”證書,裝進了我的老同學香港九龍皮革公司經理趙建送給我的那個從未用過的檔案包。
收拾停當,已是十點來鍾,“不行,乘火車來不及了。”於是,我坐“伏爾加”來到了考古研究院,向院長請示坐“三叉戟”去。院長欣然同意,並祝我旅途愉快。
下午五點多鐘,我們的飛機到達了豐南一中的上空——
我俯視這塊古老而熟悉的土地,然而一切都變得是那樣嶄新而陌生,唯有那面鮮豔的紅旗,還在迎風颯抖……
飛機降落了,老同學蜂擁而至,就在我剛出機艙的一剎那,眼前晃過刺眼的鎂光。我打量著那位胸掛相機的中年婦女,在努力地尋找著她昔日的影子。
“老同學!”中年婦女先打了招呼。
“你是?”一時沒有記起。
“新聞記者董麗豔!”語氣中帶著一絲不滿。
“啊?是你呀!我們的同氏小妹。恕罪恕罪!”
人群中發出一陣笑聲……
“老鄉!”這時,侯玉敏扶著一位老者蹣跚而來,倒不是侯玉敏腿腳不靈便,而是她與老人的步伐踩在一個點兒上了。
“哎!侯校長。”我像同她見過幾回面似的答應著,並開始凝視她身旁那位兩鬢已霜白的老者……
“啊!董老師,文浩先生,是您?您還如此康健,太好了,太好了!”我很激動。
“是啊是啊,都二十年了,如今我也不中用了!”董老師老淚溢滿雙眼,不住地連連點頭……
望著這位當年我們最崇拜、最敬仰的文浩先生,我不知該說什麼,於是,把手中的鮮花雙手呈給了他老人家。
侯校長開始給大家一一介紹,看來,真不愧是搞教育工作的,說起話來乾淨利索。
“這位是我們當年的班長,呂東光先生,不,還是稱同志吧。他現任財經學院副院長。”
“祝賀你!”我伸過了手。
“這位是省委宣傳部部長王雪漫。這二位是《詩地》主編田小靜、任寶春。”我向他們一一致意。
“這位,省作協副主席王純。”
“啊,王純,不錯,是王純。我還記得你高中時最喜歡老鼠,尤其米老鼠!”
“哈哈哈!”同學們開心大笑。
侯校長顯然也很動情,她的嗓音中還夾帶一股笑的顫音。
“這位,這位就是我們班的佼佼者,大名鼎鼎的地質學家崔文靜。”
“哎呀!崔文靜,沒想到,你搞起了地質。怎麼樣?很辛苦吧?”文靜一樂,道:“老同學,你們考古的也不容易呀!”
“考古?你怎麼知道我考古?”
“誰不知道啊?你帶領的考古小組又有了新的發現,還上了電視呢!”
“微不足道,微不足道!”
我們一路歡歡笑笑地走進客廳,室內溫度很高,同學們都脫下了大衣,掛在了衣帽架上。然後各就其座,開始了熱烈的茶話。
侯玉敏是這兒的主人,當然由她先說了,“各位老同學,時間一晃過了二十年,今天我們才得以在母校相聚……”
一陣掌聲,熱烈的經久不息的掌聲……
董老師的眼中投下了我們每個人的身影。他在逐一地看著他的每一個學生,臉上掛著笑容……
“今天,到會的是四十四位老同學,其餘的,有三位出國留學,兩位因公出差……”
“啊,留學了,真好啊!”有人讚歎著。
“唉?大家還記得嗎?當時咱們班誰的歌唱得最好?”侯校長有些神秘地說著。
“是劉——,對!是劉冉霞。”
“對,就是這位劉大姐,她已成了當今灌製磁帶最多的歌唱家……”
“歡迎 Mrs.劉來一個 !”四十來歲的人們還像當年十六七歲開週末晚會時點她唱歌一樣。
她也挺痛快,呷口咖啡就唱上了:
“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麼美……”
一歌唱畢,真是嗓驚四座。
我身旁的小A更是激動,他說:“當時,只有我和小B不好好學,最後連個中專都沒考上……”
“唉,老同學別自卑,你們幹得蠻不錯嘛!”王雪漫一邊安慰小 A,一邊轉過身說:
“去年,我們去農村外調,就去了小 A 家,如今,他們那裡的農莊已全部實現了機械化,小 A 還自己買了一架飛機,準備噴灑農藥用!”
“是嘛?”我驚問。
“嗯!”小 A 點著頭。
侯玉敏環顧一下四周,問:“大家誰還記得一九八二年我國人口普查時的數字?”
“十億三千一百八十八萬兩千五百一十一人。”一位戴著金絲眼鏡,風度翩翩的中年學者站起來不緊不慢地說。
“啊!是‘滑稽’!”我同他握了手。
“人家現在成了省計劃生育辦公室的主任了!”侯玉敏補充道。
“不敢不敢!不過有一點,本人需要抗議一下,我女兒都上初中了,‘滑稽’這一綽號是不是該取消了?大家叫我老王吧!”他還是那樣滑稽。
可了不得,西京啤酒廠廠長麼曉玲竟笑彎了腰……
“啪”的一聲,董麗豔不愧為記者,鏡頭抓得真及時,這一下麼廠長的光輝形象就已載入了“史冊”。
“哎,王兄,繼續說說你的名堂吧!”律師李金廷點上一支菸說。
“好,那我就吹吹!”他咳了咳嗓子。
“八二年的人口剛才已經說了。那麼二十年後的今天人口又是多少呢?據不完全統計,可能是十三億多一點,按年均增長率來看,人口增長是不快的。……”
“王兄,你怎麼選擇了這項工作呢?”
“一言難盡啊!當時我們學高二地理時,我看到美國地多人少,人民生活水平很高,而我們中國土地比美國多得多,可人口更比美國多,到頭來,人民還是不能得到更多的實惠。所以我立志,將來一定得從事計劃生育工作。……”
“下面,還是請王部長談談吧!……”王玉東主任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說。
王雪漫很客氣,“其實,這主要是咱們主任老同學的功勞,他們用相聲、快板、西河大鼓這些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宣傳人口氾濫的危害性,開始讓人們有了新的認識。我們宣傳部並沒做什麼工作……”
“別謙虛了,要沒你們宣傳部,恐怕我們連飯碗都丟了呢!”
大家都笑……
“哎哎,下面該我了。”記者同志毫不客氣地站起來,響脆地說道:“就說去年在巴西的那場‘和平杯’足球賽吧,當時新聞局派我去採訪。真沒想到,坐在我前面的那位足球副教練竟是咱們老同學馬士軍。嗬,真棒!他的隊員每得漂亮的一分,場上都是爆發出一片雨點般的掌聲。”
這時,身穿運動服的馬教練,手捧一枚金質獎章,來到了坐在首位的文浩先生跟前。
“老師,謝謝您!”馬教練深深地鞠了一躬,而後把獎章掛在了恩師的胸前。
文浩先生嘴角哆嗦著,用顫抖的雙手握住了老馬。
“孩子,謝謝你。是你訓練出了一支強隊,使中國足球翻了身。我們作為炎黃子孫都要謝謝你呀!”文浩先生努力地點著頭,控制著自己的感情,“孩子們,作為你們的老師,我感到自豪,如今你們一個個都有所作為,我從心裡高興啊!我祝福你們!”
望著這位古稀的恩師,我們大家一同走出座位,來到了他的身旁。大家共同伸出手,一隻只地扣在了老師那讓粉筆灰染白了爆著青筋的手上。大家的血都在流淌,都在向一處流淌……
“啪”記者的閃光燈又閃了一下。她給大家留下了這永恆的、美好的瞬間……
“孩子們,今天你們的幾位老師都未到,因為他們有的去‘南戴河教師療養院’療養了。你們的耿邊老師,還有唐老師,他們去了新疆,不久才回來……在此,我代表這些老師再次祝福你們……”
“祝老師身體健康!”
“祝您貴體平安!”
“再過二十年我們還要聚會!”
四十來歲的爸爸、媽媽們還像孩子似的在向老師傾訴著心聲。
文浩老先生頻頻點著頭,他的目光中有我們每一個同學的身影。
這時,錄音機打開了,大廳裡又響起了熟悉的歌聲:
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麼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惹人醉,神州大地處處添光輝……
再過二十年,我們重相會,但願到那時,一切都變得更美……
多麼美好的二十年後啊!我幸福地睜開眼,想著,我們將怎樣做,才能擁有這樣的二十年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