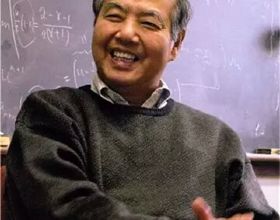《道德經》開篇即說: “道可道,非常道。”既然道不能用語言來表達,那麼人們是否只能對道保持沉默呢? 事實並非如此。從老子、莊子到歷代哲人,都對不可說的道作了許多言說。
因而,有人提出疑問:
“大家都說《老子》是講 ‘道’的,而大家又都說老子認為 ‘永恆的道’是說不出來的。那麼,《老子》一書究竟是在講什麼? 是在講 ‘不永恆的道’,還是在講 ‘說不出來的道’? 如果是前者,又何必去講它? 如果是後者,《老子》 怎麼又能把 ‘說不出來的道’給說出來了呢?”
這是一種鑽牛角尖式的 “直線思維”。其實,古人早就認識到 “說不可說之道”自相矛盾,但是他們並不想去消解這一矛盾。因為,在古人看來,“說不可說之道”是人們在認識道的過程中必須面對的一個悖論。北宋學者蘇轍即指出: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章安也說: “道固不可以言傳也,道固不可以旨喻也, 求夫言跡之間,固非所以得道。然舍夫言跡,則道又不可得而形容。”
可見,對於道與言的關係必須作辯證的理解。一方面,道不是任何具體的存在物,因此任何語言都只是對道的一種有限的陳述,而無法表達道的無限的意義,正如王雱所說的那樣: “雖聖人之言,常在其一曲。”這樣,語言對道就有一種遮蔽的作用,即以對道的某一方面的闡述,遮蔽了道的其他方面。為了防止對道的片面理解,必須強調道不可說。另一方面,“道非言無以致顯”。領悟了道的人,如果想要表達出他所領悟的道,就必須用語言來象徵性地對道進行描述。言說雖然不能完全表達道的意義,但終歸對道有所指示,聽此言說的人,也可能透過此言說對道有所領悟。
因此:
“問題不在於要不要言說,問題在於言說道的人是否對道真有所悟;
問題也不在於言說不可說的道,問題在於聽此言說的人能否得道忘言,由有限的言說去領悟那無限的道意”。
當然,對道的認知主要還是靠體悟,而不能指望別人來告訴自己。
《莊子·知北遊》中早就指出過: “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