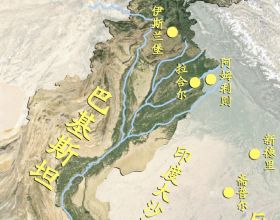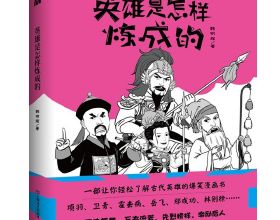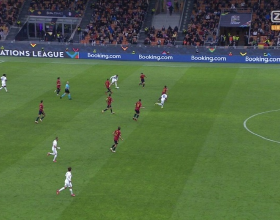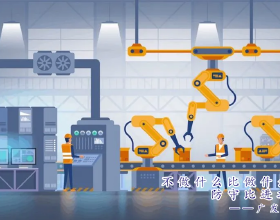技藝的習得
一位老街坊的口述:街北街南學藝的差別 學藝一天的生活
天橋街頭藝人的技藝習得,對說唱藝人而言,當然同樣以“口傳心授”為主,因為他們都出身窮苦,基本上沒有條件讀書,就是讀了點書,文化程度也都很低,三、四十年代,京津兩地眾多的相聲藝人中,僅有馬三立有高中學歷。而雜技藝人就是苦練二字。總體上,他們技藝習得不象街北科班那樣正規,尤其對小孩子,師父高興了就說一兩句,不高興了就一言不發,讓你天天干活。
老街坊劉景嵐是這樣回敘街北、街南孩子學藝的:
真正有一點生活出路的是不會上天橋學藝。去了的也是落魄,實在沒有出路的,有的藝人這時也會可憐他,收他為徒,給他一碗飯吃。街北與街南的藝人收徒在條件上、生活習慣上都有很大的不同。科班有組織、有紀律,一出門都是排著隊,打著旗子,穿著灰布大褂。街南的就沒有這套,什麼都沒有。在街北學藝的孩子條件要相對好一點,而且還籤的有合同條約之類的,去了都得立字據。科班中師父打徒弟的有,受不了跑了的,是一種違約關係,家長要給班裡賠錢的。街南學藝的孩子具體怎麼個拜師法不是很清楚,但肯定有。
從一位普通的老街坊、老天橋迷的追述中可看出在民國期間,上戲班學戲,已不是很恥辱的事情,而在天橋學藝則屬於真正的窮途末路;在街北科班學戲較正規,有統一的衣著服飾和管理,在天橋學藝的具體情形則較為封閉,很少被外人所知。當回顧藝人的自述時,我們可以對天橋的街頭藝人技藝的習得的具體情況略窺一二。
侯寶林1929年拜顏澤甫學藝時才11歲,在師父家的一天學藝生活如下:早上天不亮就起來將煤球火爐收拾乾淨、點著,等濃煙冒過,坐上一大壺水,然後就去壇根喊嗓子,估計水快開了,就回來掃院子、倒垃圾。早飯後學戲兩小時,然後去買東西做午飯。午飯後揹著大羅鍋師兄與師父一起去雲裡飛場子搭班賣藝。吃過晚飯後,他又揹著大羅鍋師兄串天橋附近的下等妓院賣唱,至午夜回家。在這期間,師孃嫌他吃得多,就給他很少的錢,讓他單獨做飯吃,其實根本吃不飽,穿的衣服是師兄剩下的衣服,他因受不了,曾逃跑過。④
高鳳山在7歲時,“幸運”地被曹德魁收為徒後,開始了他的學藝生活:一大早起來,先揹著小筐撿煤核兒,回來就生爐子、燒水、伺候師父起床,然後買早點、熱菜。吃罷早飯,給師父背上牛胯骨等道具去“上早兒”(借別人的場子在別人演出之前先演),下午還有一場叫“上晚兒”或“上板凳頭兒”,晚上再串妓院賣唱。對他學藝,師父並不放在心上,只是讓他幹活。他自己有心眼,用心記師父所唱的段子,在撿煤核兒時練習打板、背詞,還趁餘暇時串場子觀摩偷學藝。⑤
朱國良8、9歲時經張連書介紹拜山東人孫佔奎為師。學藝練功時,不但經常被挖苦,也沒少捱打。早上起來得很早,練功地點隱蔽,不讓別人看見到街上有人時,就不練了,回家再在院子裡練。朱國良的兒子朱有成在臨近解放時,跟他父親的拜把兄弟宋家茶館的宋老五學藝時,和幾個師兄弟/妹就在宋家一間專門用做練功的小屋子裡誰也不可能看見。
從這幾位街頭藝人的習藝自述可看出:1、在天橋學藝是與師父及其一家人的生活緊密相連的;2、學藝僅是徒弟學藝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學藝的同時也要上場演出或做演出相關的事並要替師父家做大量的閒雜瑣事;3、師父雖也指點但大都有所保留;4、技藝的習得主要靠徒弟自己的聰穎與吃苦耐勞。
學藝的內容
實際上,從拜師儀式開始,徒弟就正式學習該行當的知識了,如行業的起源、祖師爺、師承來源、學習態度等,這些內容在具體學習表演內容和技巧時,會被進一步強化。同時,為了讓徒弟出師後能順利地謀生,師父還得傳授行規、行話等。本文主要關注街頭藝人的祖師爺、行規、禁忌、職業道德這些與日常生活緊密相聯的內容。
祖師爺
天橋的各個行當都有自己的祖師爺。在我的調查中,流傳最多的是周莊王的傳說,包括說評書藝人在內的大多數說唱藝人都傳說著周莊王是他們的祖師爺。因先 後有評書研究會,北京長春會(民初建立),北京鼓曲長春職業公會(1940建立),北平市曲藝公會(1946建立)等組織的成立,尤其是後三種組織每年農曆四月十八日,都集中北京鼓曲界藝人在紅橋東小市藥王廟舉行祭祀活動,這樣就強化了周莊王的傳說。舊時,包括天橋各茶館在內的雜耍園子裡表演說唱,後臺都 設有周莊王的牌位,有的園子有佛龕、香爐、蠟扦兒,有的園子就只有一神碼,上寫“周莊王祖師之牌位”。
據關學曾老人回憶,在他拜師時,祖師爺的神碼是這樣的:貼在一塊木板上的紅紙正中寫有“周莊王之神位”,左邊寫的是“清音童子”,右邊寫的是“鼓板郎君”,下邊還有“四大門”(梅青胡趙),木板掛在牆上,下面再放一個香爐或者碗也行。而且,徒弟在拜師後,自己的家裡就做的有這樣的神碼,但一般只是在周莊王的生日或其他節日時才燒香磕頭。
按杜三寶的回憶,周莊王的神碼一般是木製的,大約有15公分寬,兩尺半高。他自己在1948年與其他人結拜把兄弟時, 供桌中央的神位就是周莊王的牌位。
有關周莊王的傳說較通行的是曾在清宮裡給慈禧說書,後流落到天橋說書的張福魁的說法。
我在宮裡聽一個老太監說,周朝的第十五代王是周莊王姬佗,他特別孝順母親,是個大孝子。母親有病時,為了解除一些母親的病痛,周莊王在母親病床前給老人講故事。母親聽了很高興,病也見輕了。時間一長,周莊王的故事都講完了,可母親還想聽,周莊王就讓梅、清、胡、趙四位大臣輪流給母親講故事。後來周莊王去世了,換了新君,認為這些大臣就會講故事,對朝廷沒什麼功勞,要去掉他們的俸祿,哄出朝廷。
四位大臣說老王有旨,讓他們給民間講故事,並且拿出了證據。後來這梅、清、胡、趙四大臣就成為曲藝界四大門戶的祖師爺。據說說書人的扇子是代表周莊王的令箭,醒木代表官印。起初,國家給說書人俸祿,說書的怎能是下九流?⑥
這個傳說除說明了說唱的起源,說唱不同門戶的起源成因,說唱用的道具原型之外,還傳達出最早從事說唱的人身份--或大臣--高貴之人,說唱人的品行--孝 --完全符合傳統的儒家倫理觀念,和被統治者--新君承認等三條潛在的重要資訊。因為這三條潛在的資訊,歷代的說唱藝人自己講述慷慨激昂、振振有辭,有一種極大的自豪感、安慰感。也因為宣揚的是孝道,說的是先王的仁政(新君的寬容),主流社會對其表示了預設,因此這則傳說得以存身和流傳。對徒子徒孫的講述 與其說是要徒子徒孫明白祖師爺是誰,行當怎麼來的而知恩報恩,不如說是藉此要徒子徒孫在殘酷卑微的實在的生存境況中獲得生存的信心和勇氣。
除拜師儀式時、公祭時講述周莊王的傳說,更多的追憶與講述就是在說唱藝人過度遭人欺侮歧視時,同行內部的講述。張福魁就是在竹板書藝人宋來亭因二伯父痛恨他賣藝為生,丟盡了宋家的臉面,打得他無法在天津、塘沽賣藝,逃到天橋後,張福魁給他講了這段故事的。
北京天橋街頭藝人中的說書藝人也有拜敬孔夫子、文昌帝君、明末清初的大說書家柳敬亭、北派說書發軔者王鴻興,相聲藝人也有尊奉朱少文、張三祿的。但與周莊王相比,後者更多的是僅視為同類的俗世的凡人相待,周莊王則列入神靈之列,在廟宇和雜耍園子中供奉。出身於窮家門的數來寶藝人,供奉範聃或朱元璋。王學智 因範聃更古而信奉範聃老祖。拉洋片藝人則以唐朝護國軍師袁天罡、李淳風為始祖,該說法始於天橋有名的拉洋片藝人“大金牙”焦金池。⑦
雜技藝人的始祖
不少有關雜技的書及研究者指明是呂洞賓,但在筆者的調查中,老藝人朱國良、金業勤都不知有祖師爺一說,他們也沒拜過什麼祖師爺,也未聽祖輩或師父說過。朱國良說的更有意思,“我們賣藝的不拜神,沒什麼祖師爺,掙的錢多就是祖師爺。撂地的有的家裡有‘關公’,但都不怎麼信。”
行規和禁忌
行規和禁忌是一個街頭藝人要能獨立演出謀生所必須熟知的,體現在藝人日常生活及演出生活中,十分龐雜,就目前的調查尚無法對其進行全面的概括和歸納,而且有的因絕不外傳已經失傳,現略舉一、二。
龍鬚凳的講究
撂地的評書場子,須在書桌的正前方擺設一張大桌,桌上有木質香槽(內插鞭杆香,供聽眾點菸用),打錢的小笸籮等物。桌後數十條大板凳一行行排列,桌前左右 各橫一條長凳,即“龍鬚凳”。說書藝人唯有正支正派者才准許擺設兩條龍鬚凳,否則必須撤去一條。同行的生意人來到書場,可白聽不付錢,但只能坐在大桌後面 的板凳上,絕對不許坐桌前龍鬚凳。在此坐龍鬚凳的聽客皆為當地有身份的人物,應多給錢。
戒放快
在藝人聚居處(比如說雞毛小店),每天中午之前,尤其是早上戒說夢、橋、虎、傘、龍、蛇、塔、牙八種辭句,行話稱為“八大快”,其他還有腳與五大門的狐 狸、黃鼠狼、刺蝟、長蟲、耗子等。誰要是不小心說了,即放了快,所有聽到的藝人都不去賣藝了,當天的經濟損失由放快者包賠。藝人如非說不可,只能用行話, 如牙痛說“柴幣”,做夢說“團黃果子”,稱五大門胡黃白柳灰“五仙”或“五大家”。
職業道德
這是街頭藝人在拜師儀式時就開始學習的內容之一,也是貫穿整個學藝過程之中乃至於終生的賣藝生涯中。街頭藝人的職業道德從“律己”的角度可精要的概括為“相不欺相,相不吃相”(同行藝人又稱“相”),不許“蹬”、“扒”、“踹”。“蹬”即輕視踩勾人;“扒”指耍兩面派,吹牛皮說大話;“踹”指欺人太甚。
其次,對師父師兄等長輩和行當內的人,一定要按輩份稱呼,該叫什麼就叫什麼,一定不能叫“老幾”之類的。要是師父師叔在那兒說話,一定不能接下句,否則一 個巴掌準過來。由於街頭藝人經常是結社流動性演出,有時還演堂會,所以從師父收徒弟開始,就一再強調“尤其要忌偷,你是王八(自己的老婆偷漢子)、兔子 (即孌童,比女人還女人)都可以要,因為那是你自己的事,與咱們班社沒關係。如果偷,那樣大夥都會受牽連”。
學藝的過程是十分艱辛的過程,不但要身體力行,還要用眼用心,不但要請教師父,還得表現虛心、勤勞與伶俐。根據拜師時所立字據的時間年限,到師父覺得徒弟德藝雙成時,就可以出師了。
註釋:
④ 侯珍、談寶森:《侯寶林和他的兒女們》第18-20頁、第33頁,大眾文藝出版社。
⑤ 《藝林滄桑》,第7-8頁,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北京出版社。
⑥《北京市曲藝志·人物誌·宋香臣》。
⑦ 黃宗漢:《天橋往事錄》,第212頁,北京出版社。
⑦ 黃宗漢:《天橋往事錄》,第212頁,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