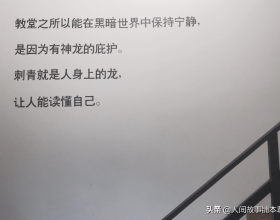這些事發生在輕浮的貴族局德還在全盛的時代,在當時,今日的那種為生存而無情鬥爭仍未為人所知。年輕的貴族哥兒和地主鄉紳的面孔仍未陰雲密佈;在官房裡貴女和名藝妓的唇邊經常都掛著微笑;小丑的職業和職業性茶樓的妙語趣談仍受到人們極端尊敬。生活太平;充滿歡樂。在當時的劇場和在寫作裡,美與權勢被描寫成不可分割的。
肉體的美,當然,是生活的主要目標,為了追求它,人們甚至不惜紋身以求之,在他們的身體上,奪目的線條和豔麗的色彩以一種跳躍的方式展示出來。當一個人要到茶街柳巷去尋歡,會挑選身體紋上花紋的漢子作轎伕,吉原和辰見的藝妓就愛身上有可以自傲的美麗紋身的哥兒。賭窟的常客、救火隊員、商客,甚至武士,全都求助於“刺青藝術”。經常有紋身展覽,在那兒參加者互相指看另一人身上的“刺青”,對某些原作大加讚美,而對另一些的短處提出批評。
有那麼一個才華出眾的紋身大師,他可是個紅人,名聲甚至可以同老一輩的大師匹敵,他的作品在紋身展覽中大受讚賞,大多數這種藝術的讚美者都盼求能成為他的顧客。當時畫家達摩金以其優美的繪畫出名。空草權田乃是硃紅刺青的大師,這個叫清吉的人,則以原畫構圖和其色情的質素而著稱。
最初他是以畫家而成名的,屬於豐國和國貞的畫派,專長於世態畫。雖然他好尊降貴而為刺青師,但仍保持著畫家的真正精神和具有高度敏感,如果誰的面板或身體不合他的要求,他拒絕為他紋身,即使是他接納肯為他紋身的人,紋什麼花紋全得由他作主,而且得同意他提出的價格。還有,他們得忍受長達一個月或兩個月他針刺難以抵受的苦楚。
在這年輕的刺青師的內心隱藏著一種別人料想不到的熱情和快樂,每當他的針刺刺得肌肉腫起,流出鮮紅的血,他的顧客無法忍受痛楚,會發出痛苦的呻吟,他們呻吟得越厲害,藝術家這種古怪的快樂就越大。他特別喜歡作硃紅刺青的設計,這種刺青是紋身中被認為是最痛的。當他的顧客被刺了五六百針後,就作一次燙熱的沐浴。這會令色澤更生動地呈現出來,他們常常會半死不活地倒在清吉的腳下。當他們躺在那兒無法動彈,他就顯出滿意的微笑問道:“它真的這麼痛嗎?”
當他遇到懦怯的顧客,痛得呲牙咧嘴或大聲喊痛,清吉會說:“真的,我還以為你是個京都的本地人,那兒的人被認為是很勇敢的,請你耐心點,我的針法可是不同尋常地痛的呢!”他用眼角望望那受害者的臉、只見他淚痕滿面,他會絕不關心地繼續他的工作。如果相反,碰上一個能咬緊牙關不吭一聲的顧客,他就會說:“哦,你比你表面看來勇敢得多,不過等會兒,很快你就不能再默不出聲忍受它的,你不信就試試看吧。”說說就笑起來,露出他一口雪白的牙齒。
很多年來,清吉最大的奢望就是能找到某個美麗的姑娘光澤的肌膚紋刺,他夢寐以求,極其渴望能為之刺青。這種渴望已成為他椎心刻骨的一種欲求。這個想象中的女性不論肉體和性格上都要達到很多方面的條件,只有一個可愛的面孔和優美的肌膚,並不能使清吉滿足的。他在名妓中搜求一個能合適於他理想的女人,但卻求之不得。她的形象經久不變地存在於他心中。雖然從他開始這種追求至今三年已倏忽而逝,但隨著歲月流逝,他的這種渴望卻只有增無減。
那是一個夏天的傍晚,當他在深川區散步時,突然一隻白得令人目炫的女性的腳吸引了他的注意,它已消失在頂轎子的簾子後面,一隻腳竟能像面孔一般傳達出各種各樣的表情,而這隻雪白的腳對於清吉來說,簡直是稀世奇珍。那些形狀完美的腳趾,那些閃耀光澤的趾甲,渾圓的腳面,那面板光潔得就像曾被無數山澗清泉洗滌多年,所有這一切綜合起來構成了一隻絕對完美的腳,就像專門設計出來騷擾男人的心和踐踏他的靈魂的。清吉立即知道,這就是他這些年來要找尋的那女人的腳了。他興高采烈地追趕那轎子,希望能望上一眼那轎中的美人,但他追趕了幾條街,拐過一個街角就失去了它的蹤影。過去一直以來還只不過是不明確的渴望,現在卻一變而為一股最激烈的熱情了。
一年以後的一個早晨,清吉在深川區的家中接待訪客,那是他朋友託一個年輕姑娘捎信,這朋友是辰見的某個藝妓。
那姑娘羞怯地說:“先生,請原諒,我的女主人派我送這件衣服,親自交給你,請求你賞面在襯袖上畫個花樣。”
她遞了一封信和那件女人衣服給他,那衣服是用一張印有演員巖井登雀的畫像的紙包起來的。在那信中,那藝妓告訴清吉,送信的年輕姑娘是她新近收養的下女,很快就要她在首都的酒帘中以藝妓身份初露頭角了,她懇求他盡他可能地幫忙,為這姑娘進入這行業作個開導。
清吉仔細望了望那姑娘,雖然她還不過十六、七歲,但她的容貌卻奇怪地有著某種成熟。在她的雙目中,反映著生活在這城市所有英俊男子和漂亮女人的夢想,這都市正是整個國家罪惡的淵藪。接著,清吉的目光一直往下望,望到她那雙穿著上街縷了革帶的木屐的嬌嫩的腳。
“難道你就是去年六月坐轎離開平瀨酒家的人嗎?”
“是的,先生,那是我,”她說,對他這古怪的發問不禁笑起來,“那時我爹還活著,他有時帶我到平獺酒家去的。”
“我已等了你五年啦,”清吉說,“現在我才第一次見到你的面,但我早已從你的腳認識你了.....我有些東西要讓你看看,請進內屋去吧,不用害怕。”
他一邊說著,一邊拉住那不知怎麼辦好的姑娘。把她帶到樓上的一個房間,這房間裡出去是條大河。他拿出兩大卷畫卷,把其中一卷在她面前展開。
那是一張古代中國殘暴帝皇紂王著名的公主妹喜的畫像。她嬌弱無力地倚著欄杆,她織金鑲銀的衣袍下幅披散在通向花園的一道石階上。她那嬌小的頭看去幾乎太嫩弱,支撐不起頭上冠冕的重量,那金冠嵌滿了珊瑚和翡翠。她右手拿著一隻杯盞,微微傾側,正在以一種慵懶的表情,觀看著下邊花園中一個正要被砍頭的囚犯。他的手和腳被捆在一根柱子上,站在那兒等待最後的一刻,雙目緊閉,頭低垂下來。這是那類意識傾向粗俗的圖畫,但那畫家卻那樣技巧地畫出了公主的表情和那註定死亡的男人的神態,使這畫卷成為一幅完美無缺的作品。那姑娘有好一陣把目光凝在那幅奇怪的畫上,她不自覺地雙眼開始閃耀,嘴唇哆嗦起來,這樣她的面孔就跟那中國公主的面孔極其相似了。
“你的精神反映在那幅畫裡了,”清吉一邊愉快地望著她一邊說道。
“你為什麼把這樣一張可怖的畫給我看呢?”姑娘問道,把手摸摸自己蒼白的額頭。
“描繪在這兒的那女人就是你,她的血在你的血管裡流著呢。”
清吉又展開另一卷畫,上面的畫題是《受害者》,畫的正中是一個女人,倚著一株櫻樹,望著她腳下躺著的一群男人的屍首,在她蒼白的臉上可以察覺得出充滿了驕傲與滿足;在這堆屍首間,有一群小鳥在跳來跳去,快樂地啼鳴著,根本說不準這幅畫代表的是一片戰場還是一個春光明媚的花園。
“這幅畫象徵著你的未來,”清吉指著畫中美女的臉說道。她出奇的又跟這來訪的姑娘十分相似。“那些倒在地上的男人,就是那些將要為你而喪生的人!”
“啊!我求求你!”她叫起來,“快把那幅畫拿開。”她好比要逃避可怕的幻想,把身子擰開背向畫幅,倒在草蓆上。她躺在那兒,嘴唇發抖,整個身子都在哆嗦。“先生,我會向你懺悔......你猜得一點不錯,我確有著那女人的品性,可憐可憐我,把畫收起來吧。”
“別像個懦夫一樣講話!相反,你應該更細心地去研究這張畫,很快你就不會害怕它的了。”
那姑娘無法抬起頭來,一直用和服的袖子掩住臉,她倒在地上一次又一次地說:”先生,放我回家吧,我怕跟你呆在一起。”
“你還得留下來一陣,”清吉專橫地說,“只有我有權力使你變成一個絕代佳人。”
清吉從他架子上的瓶子和紋身針中,挑出一個裝強烈麻醉藥的小瓶來。太陽光燦燦地照射著大河,河水反射著陽光,在幛子上投下金色波浪顫動的花紋,也照在那睡著的年輕姑娘的臉。清吉將幛子拉攏,坐在她身邊。現在他第一次能夠完全地欣賞她奇異的美了,他心想,他可以在那兒坐上好多年,一動不動地凝視著她那完美而靜止的面孔。
可是用不了多久,那種要完成自已構圖的急切慾望戰勝了他。清吉從架子上把紋身工具取來。脫光了姑娘的衣衫,用筆尖在她背上細細描畫,然後用左手的拇指、無名指和末指掂著筆,用他的右手拿起針。沿著繪畫的線條挑刺,清吉現在熱戀著這年輕姑娘純潔的肌膚,就好像刺青師的心靈注進了那構圖中去,每注進一滴硃砂,就像他自已的一滴血,注進了那姑娘的身體。
他根本忘了時間的消逝。中午過去了,靜寂的春日又到了黃昏,清吉的手堅持不懈地幹著活,也不把那姑娘從沉睡中喚醒。現在月亮已掛在天上,把夢幻似的銀光流注在河的對岸那些屋頂上。刺青還未做完一半呢。清吉停下工作,把燈點亮,又坐下來,伸手去拿他的針了。現在第一挑刺都要花很大力氣,這藝術家會發出一聲嘆息,就像他的心能感覺到每一下挑刺似的。慢慢一點點開始出現了一隻大蜘蛛的輪廓了。當黎明魚肚白的光線透進房中來時,那魔鬼風姿的動物已將它八隻毛腳伸展在姑娘的背上。
春夜要完了,人們早已可以聽得見在大河上下的船隻的搖櫓聲,漁舟的帆上,吃飽了晨風,可以看得見晨霧在飄散。清吉終於將針放下,站到一旁,觀察著那紋在姑娘背上巨型的雌蜘蛛,當他凝視著它時,他明白他一生的心血都貫注進去了。現在它完成了,畫家心中反倒感到空虛得發慌。
清吉喃喃地說:“為了給你以美,我已將整個心靈貫注進這刺青裡了,從今以後,在日本再沒有一個女人是你的敵手啦!你永遠也再不會懂得驚慌,所有男人,所有人都會成為你的犧牲品……”
她聽到了他這番話,唇邊透出一聲呻吟,她的四肢動彈了一下。無疑她開始恢復知覺了,當她躺在地上沉重地喘著氣時,那蜘蛛的毛腳,在她背上張動起來,活像是隻活的動物。
清吉道:“你準是很痛苦了,那是因為那隻蜘蛛把你摟得那樣緊啊。”
她微微睜開雙眼,最初她目光空虛,毫無神氣,跟著瞳子開始閃閃發光,光亮得可以同灑在清吉臉上的月色比美呢。
“大師,讓我看看我背上的刺青啊!如果你真的把心魂都給了我,那我準定已變成很美啦!”
她講話就像夢囈似的,但在她的聲音中,有了一份自信,有了一份權威。“首先,你必須沐浴,使顏色鮮豔,”清吉回答她道,又以一種罕見的焦慮補充說,那會很痛的,痛極了,要有勇氣啊!”
“為了美我能忍受任何事情。”姑娘說。
她隨著清吉走下幾步梯級,走進浴室,當她踏進熱氣騰騰的風呂時,她痛苦得雙眼發光。
“啊,啊!它好痛啊!”她呻吟起來,“大師,別理我,上樓去吧,等我準備好。我會見你的,我不要任何男人在看到我受苦。”
但當她從風呂走出來時,她甚至連抹乾身子的力氣都沒有了。她推開了清古伸過來扶她的手、癱倒在地上。她長長的秀髮披散滿地,痛苦地呻吟起來。背後的鏡子映出她的雙腳腳板,光潔得有如珠母。
清吉走上樓去,在樓上等她,當她上來時,已經細心穿戴好了。他溼潤的黑髮已經梳好,披在肩頭。她嬌嫩的雙唇和彎彎的眉毛,再也不流露曾受過的苦楚。當她凝視著大河,她眸子中射出冷酷的閃光。雖然她年紀很輕,但她已有著多年詭詐和掌握男人心靈的女人的風姿。清吉對於這個一天前還很羞怯的姑娘,現在變成這樣,覺得有趣。他走進另一間房間,把曾給她看過的那兩個畫卷又拿出來。
“我把這些西送給你,”他說,“當然嘍,還有那刺青,它們全是你的,都歸你了,拿走吧。”
“大師,”她答道,“我的心現在什麼也不怕了,而你……你將是我的第一個犧牲品。”
她向他投過一瞥,目光鋒利得如剛磨利的劍刃,那是那中國公主的目光,也是那倚著櫻樹,周圍有嗚咽的鳥兒和死屍的另一個女人的目光。清吉心中湧起了一股稅利的欣喜。
“讓我看看你的刺青吧,”他對她說,“把你的紋身露出來讓我看看。”她一句話沒說,低下頭來,解開了衣衫,早晨的陽光照在這年輕姑娘的背上,它的金光像把那蜘蛛燃燒著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