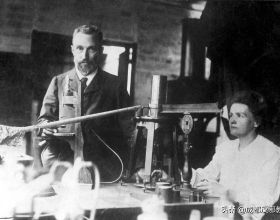曹髦
曹髦,字彥士,魏文帝曹丕之孫、東海定王曹霖之子,曹魏第四位皇帝,史稱“高貴鄉公”。關於曹髦之死,《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只有一句話:“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至於死因,則隻字未提,反而透過郭太后之口,痛斥曹髦“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大將軍以其尚幼,謂當改心為善”,豈料他“既行悖逆不道”,企圖謀害太后,“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云云。
這位痛斥曹髦的郭太后,是魏明帝曹叡的第二任皇后,史稱“明元郭皇后”。《三國志·魏書·后妃傳》載,曹魏黃初年間,河南西平縣出現騷亂,遭到官府殘酷鎮壓,一名當地美女郭氏,在動亂中被捲入曹魏宮掖,至於她如何搭上太子曹叡,並與之定情,史無明載,天曉得也。黃初七年(226)五月,文帝曹丕駕崩,22歲的曹叡即位,是為魏明帝,郭氏時來運轉,“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為夫人”。到了景初三年(239)正月初一,曹叡病危,望著眼前哭得梨花帶雨的郭夫人,深感悲憫,立意給她個名分,“帝疾困,遂立為皇后”。
曹叡在病勢沉重之際,將郭氏封為皇后,她也從此進入曹魏易代之際的亂流之中。曹叡病死,其養子曹芳繼位,郭皇后始稱郭太后。嘉平六年(254),曹芳被司馬師廢黜,扶立高貴鄉公曹髦繼位,甘露五年(260),曹髦被刺殺,司馬昭扶立16歲的曹奐為傀儡皇帝。至此,曹魏末代“三幼主”曹芳、曹髦、曹奐相繼登場,郭太后成了舉足輕重的定鼎之人——“值三幼主弱,宰輔統政,與奪大事,皆先諮啟於太后而後施行”(《三國志·魏書·后妃傳》)。其實,郭太后不過是司馬昭手裡的一枚“橡皮圖章”,一面遮掩自己霸凌嘴臉的炫麗彩旗罷了。郭太后對他畏之如虎、言聽計從,那是絕對必然的。即如曹髦死後,郭太后當即下了一道詔書,不是問責兇手,而是斥責可憐的曹髦。陳壽如此“照本宣科”,照錄譴責之詞,顯然屬於“選擇性”記述,飄漾著幾絲為司馬氏曲筆開脫之疑雲。
關於曹髦的喪儀,大將軍司馬昭與太傅司馬孚、太尉高柔、司徒鄭衝聯名上書太后:“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如此嚴厲斥責,陳壽也是“實錄”,其“扶強凌弱”、為尊者諱之痼疾,霍然在目矣。
南朝史學家裴松之註釋《三國志》,引用《漢晉春秋》之記載,補充還原了這段史實:
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佃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
“文王”,即司馬昭;“佃”,司馬昭之弟、屯騎校尉司馬佃。曹髦召集自己的親信,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等人,發出“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呼號,發誓與司馬氏決一死戰,隨後他徑直入宮稟報郭太后,王沈、王業則一溜煙跑到大將軍府,向司馬昭告密。
此後,曹髦拔劍登車,鼓譟出擊,演繹了一出“雞蛋撞石頭”之悲劇。在東止車門,一干人遭遇屯騎校尉司馬伷及其麾下,盛怒的曹髦厲聲呵斥,左右哇呀呀大聲嚎叫,司馬伷撥馬而走,隨從呼嘯而去;在皇宮南闕門,曹髦與中護軍賈充迎面相撞,皇帝舉劍砍殺,眾人惶遽欲退,太子舍人成濟衝著賈充大喊:局勢危急,咋辦啊?賈充說,司馬公平日養著你們,不正是為了今天嗎,還要問我咋辦?——成濟舉刀向前,直刺皇帝,“刃出於背”!
《漢晉春秋》並記載了曹髦喪儀:“丁卯,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瀍澗”,指瀍河與澗河之間夾峙流域;“旌旐”,即銘旌,導引靈柩的招魂幡。
由陳壽《三國志》蜻蜓點水式簡述,到裴松之引用《漢晉春秋》補記,可以感知魏晉易幟之際波譎雲詭之動盪,略窺史家選擇性書寫造成的歷史“黑洞”,以及司馬昭處事之陰狠酷虐,曹髦後事之草率淒涼。所謂“歷史記載”,不過如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