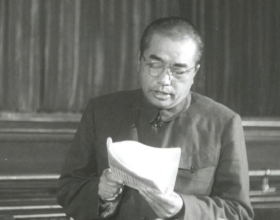皋城是一個守季節規矩的城市,而今卻有點詭異起來,節氣時常越軌,無法與常年對標。前幾天正午居然還會有30多度的高溫,下午三四點出門,陽光依然白花花的逼人。走在街面,所謂秋風蕭瑟,半點影子都抓不到;花木攢集的濃綠和各種色彩,簇擁著深秋的熱鬧,甚或比春天更加騰歡。要不是天色暗得早,晚風有些許涼意,還真的搞不準季節的名堂。
記得郁達夫曾說,“有感覺的動物,有情趣的人類,對於秋,總是一樣的能特別引起深沉、幽遠、嚴厲、蕭索的感觸來的。”他說的這份感秋滄桑,應是湮滅已久。我倒是欣賞達夫的意見,如果在秋時沒有一點動情的感喟或懷想,總覺得有所欠缺。
大概是時勢移心吧。據說當年魯迅在東京,和許壽裳、周作人等五人,租住在曾是夏目漱石的房子裡。那裡庭院既廣,隙地頗多,幾位便墾地種花。寄閒之物中,魯迅尤喜朝顏,朝顏就是牽牛花,那花冠的儀態如同女子輕飄的裙裾,花色婉約清麗,每當曉風如拂,朝顏齊開,雜色的花,綠色的葉,纖細的莖,幽玄靜美。如絲綢般的花冠,在漂泊的遊子眼裡,總會見出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朝顏匍匐在荒地上,順著牆角努力向前爬升,即使在瓦礫和碎石堆裡,也堅忍地向上生長。
暮秋的薄陰夾帶涼風掠過林梢,凜冽侵人。寒風中的朝顏,最是命短,晨昏之間,花朵就到了交付心事的時候。美好的成長憑理智來領會,它是個喜劇;走到凋零時,用感情來品味,它又是個悲劇。弱國的遊子,觀花的情緒和漂泊的自卑,早在《藤野先生》那類文字裡道盡了酸辛。達夫的寒秋滄桑,魯迅的朝顏悲涼,多少帶有一點時代悲情和漂泊的印痕。
如今動盪了去,盛世既來。名利浮蕩的今天,眾生紅塵,忙成了“內卷的囚徒”,匆遽的人群急促地把身體從“這裡”輸送到“那裡”,竭盡全力在此處彼處全力展露豐富得體的現代表情。水泥鋼筋裡,格式化的流程,人們款款抵達每個有形和無形的目的地,用力過猛的人群已來不及賞秋或是悲秋。生活,早超出了生趣之閒和柴米油鹽,人間已不能接受一份遼遠平闊的秋光迤邐了。
每去一次大些的城市,就更覺得皋城是塊福地,淠河是小城的恩人。一條老河緩緩地流淌,在城邊築起了一個灣,箍起一道圍牆,養著古老的一份靜氣,陪你在深秋裡靜默。
走到淠河北岸,尋一處城邊向陽的草坡高地,看著河沿來來往往的閒人,享受著淺淺的細水和柔波;看晚秋的河道,就像天神遺落的古老清寧的卷本。時間凝止,天地安謐,擯除了城央的擁擠,你可在黃綠深厚的中間靜靜嘗秋。
河邊的一切都是鬆弛的,從緊繃的城市氣氛中淡出,陽光澄黃,潔淨無垠地平鋪;老樹閒逸,恬靜直立,沒有一點的顫動;花葉坦蕩,空氣也沒有一絲惶惑和忙亂;草色脆嫩歡娛,清香浮溢,飽和著動人的氣息。一隻只喜鵲在河道的樹梢間鳴啾穿梭,畫著優美的線條。一直以為這些土著的鳥仔已經從城裡銷聲匿跡,沒想到它們從沒走遠。也許跟人類一樣,漸漸不願隨便地開口。
秋在聲音裡是靜的,在人的視聽裡是流動的。它是大地睡眠之前的最後一次盡興的歌唱。
秋聲無禁,輕煙般嫋嫋悠長的蟲聲,在彈奏時令。鳴蟲排行榜最前的,有蟋蟀,蟬和斯螽(蟈蟈)。同為蟲族,玩得最精彩、最有品位當數蟋蟀。它從蟲類混進了人類鑑賞的塔尖,名畫裡,名著裡乃至音樂裡都有它的位置,不能小瞧這個俗名叫蛐蛐的角兒,它甚至混進了古國的大內,皇城宮闈。
蟈蟈形似螞蚱,《詩經》稱之為斯螽,相較蟋蟀,它僅以善鳴聞世;活躍的巔峰期短,也只在夏秋之間。秋至深處,蟈蟈漸次退去。七月,蟋蟀登場,擅長表演的它鳴聲鏗鏘斷續,高低轉換,曲盡其妙,晝夜可聞;那如喜如悲,珠圓玉潤的叮鈴,深得高人們的閒心激賞。蟋蟀善鳴之外,頗能鬥勇,唯蒲松齡的妙手方可盡述風流。
能唱能鬥,善悅人心是其中的雄類,雄蟲孤傲排他,除非是它鐘意的雌類。那驕矜之聲,就是得意的文宣:本公子風流倜儻,家裡有礦,有意者速來,異己者莫入。假如不速之客擅入領地,必是一場生死肉搏。得勝者雙翅高翹,傲然長鳴,鼓呼張揚其功成得意。
而夏秋之蟬,常與寂寞同在。“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蟬鳴像一首經典老歌,能瞬間收束流光,把人送回他年往事。
鳴蟬律己謹嚴,形體端莊,方首長翅,兩翼薄如紗羅。它太看重“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的清譽,哪怕被玩童追捕,從一棵樹飛到另一棵樹,也飛得緩慢從容。儘管一身美名,也逃不脫“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的悲劇。確乎這蟲類的世界,以高潔自居也是那麼不值一錢?
一聲寒蟬,能讓懂蟬的人觸控到布衣之上的冰涼的溼意。恍然驚秋,惆悵出多少匆迫的憂思。
聽秋有得;看秋,亦有其樂。
寒露已降,節入晚秋。寒露與白露,一字之差,其意自在詞中。節令已到陰盛陽衰,轉眼即是“辭青”的重陽,於是,登高思親,看秋山淡泊,看江天寥廓。所以寒露看秋,足見人心向愛,人心眷美之“暖”。
此時,野菊燦爛,銀杏葉黃,寒塘足可照人,幾處深秋的雜花,逆時而生。你若仔細,竟能看出許多樹木會冒出幾片嫩葉,原來花木也會拒絕躺平,精彩之秋,新葉要在萬類霜天中多看一眼大地斑斕。生的精彩,不以一時榮枯作量尺,何必在意“明媚鮮妍能幾時”。
狗尾草彎著身腰,青黃的絨毛在風中搖擺。它有著神性的召喚,“草在結籽”的詩家把它捧上了天。長長的絨毛是它最有天分的構想,這個妙手偶得的創意讓他圈粉無數,蟲子和蝴蝶就是它死忠的迷弟迷妹:遊蟲總想進入絨毛一看究竟,蝴蝶老執念於立在毛尖上兜兜清風。傍晚,天光入鞘,天地濾淨了日色光華,狗尾草還在搖晃著自己的標識。
哦,夏曆的九月來了,終於撞響了清秋的門環,秋老虎立馬熄了火焰逃之夭夭;天空鎖著眉,一副貼了鉛灰的臉堂,幾滴朝雨浥溼輕塵,秋風祭出了鋒刃,開始了對衰老者的屠戮。
突兀的天象,就像這個劇變世界;安常處順的人,總在驚呼順變不暇。河沿的老樹聽出了時間催促:秋風在拆著帳篷,林子的舞臺漸漸稀疏,只剩下矗立的一根根木樁,喧鬧的老秋鑼鼓開始模糊。
靜穆的冷肅,在清點去留,枯藤老樹昏鴉,給人帶來了秋思:葉老歸根,就像河邊的船總有靠岸和離岸。
河岸的村莊,像往古的遺蹟,陳列著不歸的念想。老屋頹敗,秋風卻每年都來看顧,幾個老人還在說著那不知年月的往事。他們在聊著誰和誰還是哪一年見的面,誰和誰是哪一年成的親,誰家的孩子幾年沒回。時光的老繭如同高大堅實的圍牆。人老了,記憶落下的悲喜還那麼光潔如新。
起地皮風了,落葉你追我趕,顧不得嘆息什麼薄命不薄命,被捲過路面落進了溝渠;騎三輪的老者回來了,他躬著腰,車上還掛著一隻編織袋,裡面裝著揀來的塑膠瓶。我料定,他的心是如止水般安逸。滿臉了無牽掛的笑容,匹配他平實安順的心,時間流逝,彷彿給他留下的是更加平靜,更加慈祥。
一列動車由遠而近轟隆而過,我的腦筋被鐵軌拉長:在奔忙的另一端,勞碌的人群在營造不同的世界。馬不停蹄的人間,越來越多的創造著精緻,把世間劃成了“今”和“往”的兩半。但無論你在哪一半,每個人都如同在小心地捧起一個易碎的青花瓷瓶,一邊心生憐愛,一邊又讓你不能無所顧忌地甩步走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