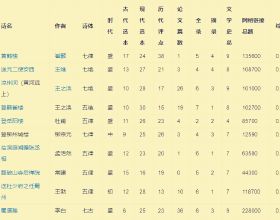唐詩論劍首選之地,竟是這!
公元716年,大唐開元四年,是一個平靜的年頭。
唐詩的江湖版圖上,在湖南嶽陽這一帶,格外地明亮。洞庭湖畔,嶽州刺史張說重修了一座壯觀的大樓。樓的前身為三國東吳將領魯肅的閱兵樓,張說重修後,沒有多想,直接給了個簡單的名字:南樓。
張說當然想不到,他修建的這座樓成了唐詩中最美的風景!因為這座樓以後的名字叫岳陽樓。“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正是這一水一樓聯袂出場,成為唐代詩人論劍的首選之地。
張說得江山之助
作為一位歷經四朝的政壇“老司機”,開元初年,張說因與宰相姚崇不和,被貶為岳陽“市長”。遠離家邦,漂泊天涯,是張說一生政治上的失意期,但也是其詩歌創作的繁盛期。
剛到岳陽,張說滿懷憂傷。羈客的怨思、浪子的酸辛,他把自己說成是“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但當詩人從宮廷走向江山之後,反而遠離了車馬喧囂,有了時間去尋找無言的山水。無限高爽遼闊的山水,給予詩人一種極美的精神愉悅,那些怨思苦情漸漸退卻,他的藝術生命被“開光”了。
原來,當拋開那些名利得失,這個平日看似俗務纏身的自己,居然也能與高山共俯仰,與白雲同翻卷。正是在洞庭湖畔,張說的文字在無垠奔騰的江水中揮灑,他的詩風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一天,老朋友梁知微回長安,途經岳陽。煙水迷濛的洞庭湖邊,張說望著友人的身影,想著自己孑然一身、漂泊他鄉,不禁感慨萬千。於是,一首清新雋永的詩奔湧而出:“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峰水上浮。聞道神仙不可接,心隨湖水共悠悠。”
竊以為,這是唐朝開國百年以來,誕生的最蘊藉的送別詩之一。在後世,任憑是多麼毒舌的批評家,都對這首詩擊節讚歎。明代胡應麟認為這是唐代七絕漸入盛唐的里程碑式作品。更有人認為唐詩就是從張說開始“漸入盛唐”的。
《新唐書》本傳認為張說“既謫嶽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雲”。嶽州的山山水水,助益了張說的詩才,張說也成了唐詩江湖的“帶頭大哥”。
孟詩開萬千氣象
數十年後,另一個詩人站了出來。他叫孟浩然。
嚴格地說,孟浩然到洞庭湖不是來旅遊的,而是來找工作的。作為唐代詩歌史上最偉大的山水詩人,他一生基本上處於待業狀態。
孟浩然曾是李白的精神偶像。他隱居在家鄉的鹿門山,整個青春期都是以隱逸為主的,不是“耕釣方自逸,壺觴趣不空”,就是“垂釣坐磐石,水清心亦閒”,一副歲月靜好的樣子。
在世人眼裡,孟浩然是地道的隱逸詩人。李白常在朋友圈表白:“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聞一多也說:“唐代計程車子都有登第狂,獨浩然超然物外。”
歲月靜好也抵不過柴米油鹽。人到中年的他,開始不淡定起來,拼了命想當官。不少評論家認為孟浩然是“仕隱兩失”,隱居得不徹底,到後來當官不成,連隱居的心境都沒了。
朋友們一個個發達,與其詩文齊名的王維仕途上春風得意,王昌齡也在準備應試,李白到處“走關係”。一個人要想找到好工作,得靠大佬推薦。這次,孟浩然瞄上了宰相張九齡。
詩人說:“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作為干謁詩,關鍵在於要寫得低調而奢華,稱頌對方要有分寸。這首詩在語言上不卑不亢,沒有絲毫寒酸相。重要的是,詩人筆下的洞庭湖浩蕩澎湃,氣象萬千,深深影響了後代文人的感受,宋代滕子京更是在《臨江仙》一詞中不客氣地“致敬(抄襲)”了。
欣賞著這樣的好詩,張九齡十分感動,然後拒絕了他。畢竟張相爺剛剛被貶,就算真心賞識,也是愛莫能助。就這樣,已陷入中年危機的孟浩然,繼續喝酒,繼續寫詩,繼續投“求職信”。張九齡後來到任荊州,把孟浩然招聘到秘書班底裡,這是後話了。
李白但傷知音稀
論劍遠沒結束,李白出手了。
安史之亂中,李白被命運扼住了喉嚨。自從在潯陽登上永王李璘的樓船,他的理想和抱負就被迅速燃盡了。他無數次執筆寫詩申冤和抗辯,一次次還原被權力篡改的真相,但人們只樂意誦讀他喝酒吹牛時寫的詩句,不願意去讀他晚年那些悲苦、泣血、隱晦的詩歌。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公元759年,流放夜郎的李白剛剛遇赦。劫後餘生,他在岳陽偶遇族叔李曄,還有被貶的朋友賈至。這時,安史兵亂的戰火還在熊熊燃燒,他們和盛唐都已青春不再。
一個秋夜,三人共遊洞庭湖。在這次遊湖中,李白寫下五首一組遊洞庭詩,其中一首雲:“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
月華空明,水天一色,多麼清澈明亮的空間!久在痛苦中咀嚼的李白,心胸頓時舒展愉悅。此時,詩人忽發奇想,把“洞庭”和“月色”融為一體,甚至要把洞庭湖上的一葉扁舟行駛到“白雲邊”“買酒”。詩人極具想象力:且讓我們忘記煩惱,共同享受這通體清瑩的月色;且讓我們劃入醉鄉,劃入湖水深處,劃入白雲明月的天空。
最有趣的當數李白的《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三首》之三:“剗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
當李白和友人碧波泛舟,開懷暢飲之際,舉眼望去,兀立在洞庭湖中的君山擋道,湘水不能一瀉千里直奔長江大海,就像人生道路上的坎坷障礙,破壞了他的遠大前程,所以才想要“剗卻(鏟去)君山”。
李白的洞庭詩,充分體現了詩仙的性格:即使在人生困境中,詩人廣闊的胸懷和豪邁的氣魄也展露無遺。
失意者來來往往
到了中唐,來往洞庭湖的是更多的失意者。而在遷謫、行旅、離別之中,新樂府詩派的老大白居易首先亮相了。
他甩出一首《題岳陽樓》,期待以韻味取勝:“岳陽城下水漫漫,獨上危樓倚曲欄。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猿攀樹立啼何苦,雁點湖飛渡亦難。此地唯堪畫圖障,華堂張與貴人看。”
文壇盟主韓愈洋洋灑灑寫了近500字的《岳陽樓別竇司直》:“洞庭九州間,厥大誰與讓。南匯群崖水,北注何奔放……”他的詩奇崛陡峭,骨力遒勁,以長取勝,重新整理了詩壇紀錄。
新樂府詩派的另一位大佬元稹出馬,要為白居易助攻:“岳陽樓上日銜窗,影到深潭赤玉幢。悵望殘春萬般意,滿欞湖水入西江。”全詩琢句煉字,視角獨特,含蘊深沉。末句“滿欞湖水入西江”,不說透過窗子向外眺望洞庭湖水,而說湖水從窗子溢位,流向沒有盡頭的長江,巧妙地融入了詩人的主觀感受。
眼看眾人難解難分,劉禹錫也來湊熱鬧:“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色,白銀盤裡一青螺。”在詩人眼裡,千里洞庭不過是妝樓奩鏡、案上杯盤而已。這首詩舉重若輕,自然湊泊,毫無矜氣作色之態,堪是神來之筆。
在這樣的好詩面前,洞庭湖一下子寂靜了。
傷心人魂斷天涯
一種風流吾最愛,六朝人物晚唐詩。雖然日近西山,但晚唐的詩歌別有一種風流之美。這種美,有別於盛唐。
在盛唐,詩人的目光放得很遠,他們的人生道路鋪展得很廣。即使身處逆境,他們多半不會灑淚悲嘆,他們的步履是放達的;在晚唐,許多詩人空有報國之志卻不斷流轉江湖,詩裡總漂著一些莫名的惆悵,這是一種濃得化不開的悲哀,也是抱負不得施展的抑鬱。
李商隱說:“欲為平生一散愁,洞庭湖上岳陽樓。可憐萬里堪乘興,枉是蛟龍解覆舟。”見慣人生多坎坷,連作快意的想象時,都充滿著悲意。李商隱屬於天性特別醇厚的詩人,所謂深於詩而多於情,憂樂俱過於人。
作為晚唐的神童,鄭谷好詩似是天性,幼年就能成誦。隨父親南下到洞庭湖,竟然“岳陽樓上敢題詩”,那年他才七歲,司空圖“見而奇之,拊其背曰:當為一代風騷主”。但是,他的科舉之路坎坷,連考了十次,直到40多歲才考上進士。
在洞庭湖畔,鄭谷寫道:“穩眠彭蠡浪,好醉岳陽樓。明日逢佳景,為君成白頭。”這首詩頗有杜甫《江南逢李龜年》“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的味道。正是傷心人在天涯。
在唐朝,“挑戰大師”是一種常態。江湖小輩方幹也湊上來:“曾於方外見麻姑,聞說君山自古無。元是崑崙山頂石,海風吹落洞庭湖。”以天馬行空的想象力,虛構了自己“遊仙”的經歷,又透過人仙對話,揭示了君山神話般的“來歷”。全詩運用奇特想象,從題外落筆,間接表現出君山的奇美。這就是“超以象外,得其圜中”。
漸漸地,大唐的落日更加西沉了。韓偓也來到了洞庭湖畔。這位被姨夫李商隱稱為“雛鳳清於老鳳聲”的才子,身處群藩割據、宦官爭權的唐末亂世,再加上忠正剛直的秉性,使得他遭受朱全忠等權奸小人的排擠。
天祐元年(904年)秋,詩人流寓到了湖南:“洞庭湖上清秋月,月皎湖寬萬頃霜。玉碗深沈潭底白,金盃細碎浪頭光。寒驚烏鵲離巢噪,冷射蛟螭換窟藏。更憶瑤臺逢此夜,水晶宮殿挹瓊漿。”
這個秋天的夜晚,洞庭湖裡的月光一瀉千里,天上繁星點點。但如此良夜,詩人輾轉江湖老。“大唐”,後世人心中永遠的盛唐,正如同這洞庭寒潮,一去不返。
盛唐第一傷逝詩
那麼多詩壇大佬路過洞庭,又離開洞庭,而一位詩人卻像一片秋葉一樣,將生命留在這裡。
公元768年,杜甫(712—770年)出荊州,過公安,到岳陽。一路漂泊,目的很單純,就是想活下去。是的,這位擁有“千秋萬歲名”的詩人,一直處於貧寒交加的狀態。
回想746年,杜甫到長安找工作時,“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困守長安十年,政治上一事無成,他的身體卻患上了肺病、痛風和惡性瘧疾。此後,詩人飄蕩成都、夔州,病情加重,又添糖尿病,牙齒也掉了。
這年冬天,詩人來到岳陽城下。南方的冬天,潮溼陰冷。杜甫寫了兩首登樓詩,一首陪友人登臨,一首應該是獨自登臨,這便是《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這是大唐最傑出的苦命詩人,走到了人生的晚景,又偏偏登臨的是自己日夜嚮往的岳陽樓。在這裡,他或許想到了李白,想到了孟浩然。他在哭那些逝去的朋友,哭自己的晚景,更哭國家時局艱危……在詩中,詩人跳出了小我的侷限,個體的小宇宙拓展為整體的大宇宙,個人的“傷心”和“萬方多難”的戰亂結合在一起,使得他的悲痛有了更多的廣度。
可以說,在整個唐朝,沒有一個詩人在岳陽樓上站得比杜甫更高,也沒有一個詩人在岳陽樓上哭得比杜甫更傷心。讀起這首詩,彷彿就能看到蕭瑟冬日裡,詩人痛哭流涕的樣子,也能聽到洞庭湖水的浩蕩之聲。胡應麟曾以此詩為“盛唐第一”。公元770年,杜甫死於往來洞庭湖的一條船上。
(作者為新華社福建分社經濟採訪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