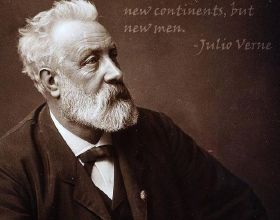去年就聽說尤鳳偉先生身患癌症的訊息,很為他擔心,祈願他戰勝病魔。9月23日下午,我收到了尤老師去世的噩耗。我的作家訪談錄裡,從此缺了一位先生。窗外秋雨淅瀝,思之愴然。
多次接觸尤鳳偉先生,最後一次見面是2015年3月29日晚,在青島松嶺路的一家酒店,尤鳳偉和作家陳若曦為閻真長篇小說《活著之上》頒獎。我請記者同行幫我跟尤老師拍了一張合影,並提出專訪他的請求,他說寫了大半輩子也沒寫出啥名堂,還是採訪別人吧。我記得一個細節,他的一縷頭髮耷拉下來,一仰脖把那縷頭髮頂了上去。
尤鳳偉說寫了大半輩子沒寫出啥名堂,那是謙虛,他的石門系列小說《石門夜話》,《石門囈語》《石門絕唱》及《泱泱水》;他的抗戰系列小說《生命通道》《五月鄉戰》《生存》;他的長篇小說《滄海客》《泥鰍》《色》《衣缽》等,都是有“名堂”的,有的是可以進當代文學史的心血之作。
我想說的是,尤鳳偉先生的清醒和對自己的苛刻。他說過:“我覺得中國作家似乎缺少一種自省的精神,總認為自己已成為文學大師,作品十分優秀,毫無瑕疵。就像一個鐵匠一邊揮錘鍛打一邊唸唸有詞:好刀,好刀。許多作家認為自己打出來的是好刀,認為已經登上了山峰,而真實位置實際上只在半山腰,這是中國作家目前普遍的位置所在。”作家可貴在自省,有自省,則清醒,不浮躁,不自戀。
對於寫作,特別是上了年紀,尤鳳偉考慮的已不是出多大的名,賺多少稿費。而是對得起“中國作家”這個稱謂,希望寫出屬於中國的文學作品。大家一看,會說尤鳳偉寫的是中國地面上發生的真實的社會人生,不離大譜。視自己的職業為神聖,視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為神聖。不苟且、不敷衍,減掉多餘的東西,對得起“中國作家”的稱呼,我想,尤鳳偉做到了。
尤鳳偉在小說自選集《蛇會不會毒死自己》序言裡的一句話:“我是懷著深深的情感來書寫他們的。當我看到背垃圾的民工從豪華飯店自慚形穢像小偷似的匆匆溜走,我的心感到疼痛,我為他們鳴不平。”不在老百姓的苦難面前閉上眼睛,這是尤鳳偉作為一個作家的良知。在牽掛弱勢群體的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短篇小說《為兄弟國瑞善後》,獲評“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最有影響力小說”,小說講的是鄉村小學教師於國祥為死刑犯弟弟善後,到大舅、二姨和大姑父家還錢的故事。入選詞這樣評價:“以悲憫的人文情懷和深刻的生命體驗,細緻入微地描寫並剖解著糾結了親情、倫理、慾望、道德、羞辱、靈魂撕扯和自我質疑等複雜矛盾的人物行為及其背後的隱痛。具有體恤人性、認知命運的沉靜和寬厚。”
不發訃告,不搞告別儀式,不開追思會。尤鳳偉走得乾乾淨淨。青島市作協原主席鄭建華談到一件事,她說:“青島市作協開過不少人的作品研討會,我不止一次問他,給你開個研討會吧?他一笑說,不用,留著那點兒錢給別人開吧。他當作協主席的十五年,我的十三年,建剛(現任青島市作協主席)的四年,一次也沒開過。出叢書時他說,建華,我和你出書都容易,這次就不參與了,讓沒出過書的作者出。”當作協主席,就是為別的作家服務,就應該付出,我覺得尤鳳偉先生做得很對,他完全夠格開作品研討會,但他一次也不開,堅持了32年,這是利他精神的體現。
聞聽尤鳳偉去世,作家劉真驊老師傷心不已,她對我說:“鳳偉是這樣一個朋友——交往,不玩心計;相處,無需防備。迷茫時,能幫你撥開迷霧;傷心時,能給予安慰;困難時,能盡力幫襯,真心真意相處。最願意跟他無拘無束地聊天。”作家趙鶴翔先生髮我微信,悼念文字是:“鳳偉老弟西行走好——你保護住了你心中文學的潔淨度。你實踐了人學的文學靈魂救贖和解剖,注進了愛的美和真。”
跟尤鳳偉的作品一起留下的,是他的自省精神和悲憫情懷。我明白了,作家寫來寫去,寫到最後,其實就是和盤托出完整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