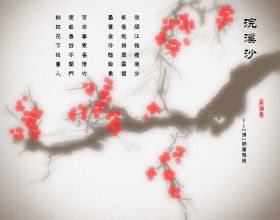去年國慶節期間,我慕名參觀了布達拉宮,被它的神奇的傳說和偉岸的身姿所深深折服。我沿著參觀通道拾階而上,巧奪天工的建築風格,無不讓我敬佩古人的勤勞與智慧。當我穿過迴廊,佇立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金身塑像前時,透過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我彷彿穿越歷史長河,和他來了個時空對話。假如你不經意間推開歷史的大門,徜徉其中,駐足於三百多年前的康熙王朝,你也許會邂逅孤寂而清俊、冷落而優雅的兩個身影-----倉央嘉措與納蘭性德。
倉央嘉措生於1683年,父母親都信奉藏傳佛教寧瑪派紅教。納蘭性德出生於1655年,父親是康熙朝一代權臣納蘭明珠,母親是英親王阿濟格第五女、一品誥命夫人。他們一個是桀驁不馴的六世達賴喇嘛;一個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侯門貴公子;一個是遊走於布達拉宮與拉薩街頭的活佛;一個是身處紫禁城而嚮往布衣生活的詞人;一個是認定的轉世靈童,卻尋覓著不負如來不負卿的雙全之法;一個是註定的廟堂權貴,卻常有遠離侯門,心繫山川魚鳥之思。他們雖然出身懸殊,地位不同,但卻有同樣的情衷,同樣的詩性,同樣的純淨與真實。
納蘭性德說:“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等閒變卻故人心,卻道故人心易變。”這首名句想必大家已經耳熟能詳了。倉央嘉措說:“但曾相見不相知,相見何如不見時。安得與君相決絕,免教生死作相思。”這兩首詩都意在說明人生很多事,許多人,初見時的印象令人難以忘懷,又記憶猶新,彼此都留下許多美好回憶。驀然回首,卻已是物是人非,滄海桑田。
倉央嘉措說:“住進布達拉宮,我是雪域最大的王。流浪在拉薩街頭,我是世間最美的情郎。”納蘭性德說:“迴廊一寸相思地,落月成孤倚。背燈和月就花陰,已是十年蹤跡十年心。”這兩首詩意在表明,睹物思人,卻已是物是人非,不由得發出充滿落寞與孤寂的遺憾。倉央嘉措說:“好多年了,你一直在我傷口中幽居,我放下過天地,卻從未放下過你,我生命中的千山萬水,任你一一告別。世間事,除了生死,哪一件不是閒事。”納蘭性德說:“誰念西風獨自涼?蕭蕭黃葉閉疏窗,沉思往事立殘陽。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疏影浮現於西風之中,倍感秋風淒涼。四周落葉紛飛,不禁讓人黯然傷神而關閉疏窗。詞人將思緒追憶到曾經的點點滴滴,襯托著身後的一抹殘陽,不禁悲從中來。
倉央嘉措說:“我是佛前一朵蓮花,我到人世來,被世人所悟,我不是普度眾生的佛,我來尋我今生的情。”納蘭性德說:“辛苦最憐天上月,一昔如環,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輪終皎潔,不辭冰雪為卿熱。”字裡行間充滿了孤獨與落寞之感,大有無可奈何花落去,春花秋月何時了的怨懟。東坡居士有言:“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就連天上的月亮逢初一、十五也有一次盈缺。即使自己想付出生命溫暖你,卻永遠無法兩眸相視,纏綿悱惻,代之以天各一方。
倉央嘉措說:“那一天,我閉目在經殿香霧中,驀然聽見你誦經中的真言;那一月,我搖動所有的經筒,不為超度,只為觸控你的指尖;那一年,磕長頭匍匐在山路,不為覲見,只為貼著你的溫暖;那一世,轉山轉水轉佛塔,不為修來生,只為途中與你相見。”納蘭性德說:“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孤身在外的日子,又怎麼會一帆風順呢?風雪交加,道路崎嶇,寒氣逼人。詞人被風聲雪聲襲擾著,被惆悵和傷感打亂情思,哪裡還有美夢可言。
時光倒流到三百年前,這是兩位極富詩書情懷、絕世才華的詩人心靈發出的情感共鳴。人雖已故去,但是流傳在人世間雋永、傳情的詩句靜靜流淌著,被那些有緣人一次次的記起,一次次的傳誦,成為名篇佳句。他們各自在寂寞與悲傷中,因那份深情的愛,世間變得溫暖;因這份溫暖,是他們的生命之花不在蒼白。他們在各自的生命中,用最純真的天性,寫著靈魂裡的詩。這些清純而傳情的字元流淌在才子佳人的血液中,成為經久永相傳的佳話。